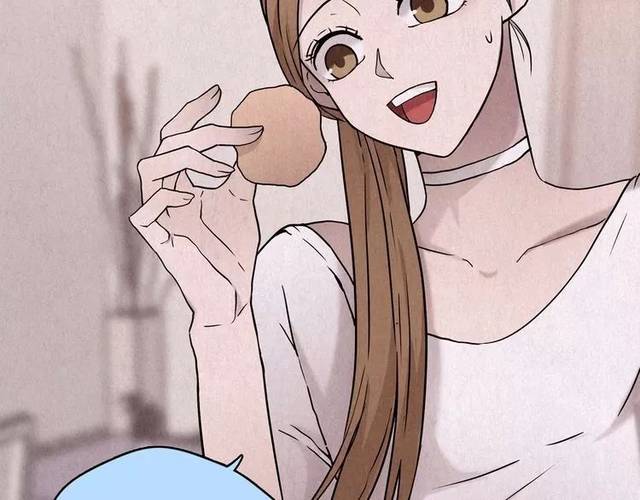入夜,我叫芸儿烧了热水,想拉元春共浴,她却死活不肯,最后只得是各洗各罢。
当芸儿伺候我洗完了澡,元春也已裹着衾被,横躺在榻上了。她见我来,不禁有些羞涩,翻了个身,把那香肩粉背对着我。
我轻笑一声,走过去,也麻利的钻进被子里,一把将她揽入怀中,那可人儿如春天般温暖,瞬间将我融化了。
元春羞怯道:“望王爷垂怜。”
我深情凝视了她片刻,便低头吻在了她雪白的脖颈上……
正是那“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我与元春颠鸾倒凤,几经缠绵,其中自有百般的柔情,千般的蜜意,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上三竿,当我睁开眼时,元春早已不在身边。我只得披了件外套,从里间出来。
“王爷,您醒了?”一个丫鬟见我出来,便起身迎了过来。
“嗯,”我点点头道:“王妃呢?”
“到前边去了,吩咐奴婢伺候王爷梳洗。”她一边说,一边递过来一杯漱口的清茶。
我接过茶来,漱了口,便打量了这丫鬟一眼:十四五岁的年纪,身材娇小,和春兰秋菊一样的打扮。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回王爷,奴婢叫冬梅,往后就在您屋里头了。”
“噗!”我差点没笑喷,“你叫冬梅?什么冬梅?你娘家可姓马吗?”
冬梅一愣道:“奴婢娘家姓崔啊。”
“哦,”我止住笑意道:“不姓马,也不要叫什么冬梅了,我老觉着别扭。你既姓崔,可知《西厢记》里有个崔莺莺,且你说话声音清脆悦耳,如黄莺啼鸣,便叫你作莺歌罢。”
冬梅当即跪下道:“谢王爷赐名,往后奴婢就叫莺歌了。”
我笑道:“莺歌自然配燕舞,往后若有合适的,改个燕舞的名字,正好凑上一对。”
冬梅道:“王爷屋里的,除了奴婢之外,还有个夏荷。”
我道:“那正好了,夏荷这名字也不好,倒让我想起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来,不若改了燕舞,莺歌燕舞,好听,又雅致。”
我让莺歌叫了夏荷来,一并改了名字,这时才见芸儿来传膳。
我见了元春便低声在她耳边道:“昨夜‘芙蓉帐暖度春宵’,你一再说自己初承恩泽,望我垂怜,今天却怎么起得这么早?”
元春没好气道:“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没得叫她们取笑了。”
我把眼睛一瞪道:“哪个敢取笑?古人还道个‘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我本就不早朝,自然是要睡到日高起的。”
元春撅起小嘴气鼓道:“凭你自己怎么睡吧,睡到天黑也没人管你。”
我却大笑道:“这个样子才对嘛,十八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却偏要板起脸来,装什么老成持重。要我说,往后你也别总是什么王爷,妾身的,就以你我相称,似刚才那样,反倒显得亲切了。”
元春道:“只怕外人面前,失了体统。”
我道:“外人面前,自然要庄重些,如今在闺房之内,还要讲什么体统?”
元春点点头道:“倒是这个理。”
吃过早饭,我照例要去园子里看书,昨儿买的足本《金瓶梅》,已被我藏在书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只把“三言二拍”中的《初刻拍案惊奇》拿来,正往园子里走,却被芸儿又叫了回来。原来是翰林院掌院刘统勋刘大人,递了贴子前来,言道有要事相商,如今人已到中堂。我无奈只得随芸儿往前院去。
初见刘统勋,一米八左右的个子,头戴乌纱帽,身着大红圆领衫朝服,花犀束带,胸前绣锦鸡补子。往脸上看,浓眉大眼,不怒自威,八字胡,颔下三绺须髯飘摆,颇有些卓越英姿。
他见了我,当即躬身施礼道:“参见王爷。”
我赶紧上前将他扶起道:“刘大人不必多礼。坐下说,坐下说。”
刘统勋这才与我分宾主落座,我又叫茗烟来,上了茶,才道:“刘大人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刘统勋笑道:“早该来的。前日里,有个吴翰林,说得了王爷墨宝,拿给下官我看时,好一句‘春深浅,一痕摇漾青如翦。’当时我便想着来拜见王爷的,怎奈皇上临时宣招,又怕突然造访唐突,故而拖到今日才来。”
我道:“刘大人可是将这词说与了皇上?”
刘统勋道:“不是下官说与皇上,是皇上忽然问起的,下官便将那首《忆秦娥》抄录了呈皇上御览。”
我恍然大悟道:“难怪了,昨天那人必是皇上无疑。”
刘统勋奇道:“王爷昨天见了皇上吗?”
我道:“也不十分肯定,只是在琉璃厂遇到的人,还央我写了一首诗去。”
刘统勋眼前一亮道:“可是那首《天一阁杂谈论诗》?”
“你也知道?”
刘统勋道:“怕不只下官知道,满朝文武皆知矣。那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皇上在朝上反复念叨多次,当时我等还以为是皇上所做,不想竟也出自王爷之笔。王爷大才,延清佩服。”
我忽然皱眉道:“皇上将我的诗,于朝上反复念叨,怕不是有深意吧。”
刘统勋道:“自然是有深意。”
我道:“有何深意?”
刘统勋刚要说,便见茗烟风急火燎般跑过来道:“王爷,宫里来人了。”
我一愣道:“宫里来人?什么事?”
茗烟道:“小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叫王爷出去呢。”
我转身对刘统勋道:“刘大人且稍候,我去去便回。”
刘统勋拱手道:“王爷自去。”
我随茗烟匆匆来到前院,一个太监,手持拂尘,见了我,便躬身施礼道:“见过王爷。”
我仔细打量这太监,竟是昨天引我上茶楼的那个下人,便笑道:“昨日引我上茶楼,今日不知又要引我去哪里呢?”
那太监也笑道:“传皇上口谕,宣王爷即刻入宫见驾。”
我道:“皇上宣我入宫何事?莫不是又要我写诗?”
太监道:“这老奴就不知了,估么着是好事,王爷赶快随老奴进宫吧。”
我道:“公公稍等,我换身衣服就来。”又让茗烟带这太监到前厅奉茶,我则回到后面,先见了刘统勋。他听说皇上宣我入宫,便也就告辞了。
我叫元春来道:“我可有入宫见皇上穿的朝服?”
元春道:“王爷从没进过宫,连这王府都没出过,哪里有什么朝服?如今现做也来不及。”
我道:“那就算了,你去找一件精致常服来罢。”
我换了衣服,便随那太监乘坐马车,来到午门。她引我从角门进入,一路穿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乾清门西侧的南书房外停驻。
她道:“老奴去通禀一声,王爷且在这里候旨就是了。”说罢她便进去,不大一会儿又出来道:“王爷,皇上叫您进去,且随老奴来。”
我跟着她,进入南书房。南书房不大,里外两个套间。外面的一间中间悬挂太祖李自成金戈铁马图,右边上联:“时乘六龙以御天”;左边下联:“用敷五福而锡极”。
穿过外间,里面就是一个书房,布置得很简单,一排书架,一张桌案,并九龙雕花榻。昨天见过的那年轻人,正坐在榻上看书。
我在那太监的示意下,赶紧上前跪倒在地,三呼万岁。
皇上见了我,笑道:“简亲王平身吧。”
我这才站起身来,皇上又命赐座,太监搬来一把小凳,叫我坐下。
皇上道:“你昨天写的诗,朕已经让人装裱起来,挂去上书房了。如今上书房的那班大学士,都在猜测是出自何人手笔。让他们猜去,朕偏不说。不过有心的,怕是已经猜出来了。毕竟那几个简化字,只你才会写得。朕听说一早下了朝,刘统勋便去了你那,可有这事吗?”
我笑道:“果然还是皇上消息灵通。”
皇上也笑道:“朕若消息不灵通,这皇上也就做不稳当了。简亲王,朕叫你来,可知所为何事?”
我道:“莫不是要臣作诗写字?”
皇上笑道:“你的诗词,朕自然是想要的,但那终归是小事。朕叫你来,是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办。春闱马上就要开始了,依照往年的惯例,主考官两人,翰林院学士中出一个,礼部出一个。这两人,朕早已选定,分别是掌院学士刘统勋以及尚书赵国麟。但今年又有不同,朕想加派一名皇室成员为总裁,原想的是老皇叔睿亲王,但现在不是有了你嘛,朕想还是你最合适。”
我一听便吓一跳,豁然站起道:“皇上,臣虽恢复了心智,但却失忆了,连人都记不得,况春闱乃是为国选才,这么大的事情,臣恐怕难以胜任。”
皇上挥挥手示意我坐下,道:“急什么?朕又不是叫你去做主考,不过是挂个名,充当朕的耳目罢了。前三年春闱大比,曾发生过科场舞弊案,朕当时虽处置了几个,但却终究不得要领,抓不到根源。这次你和刘统勋、赵国麟商议一下,想个万全的法子,不能再搞出什么舞弊案了。”
我嬉笑道:“只要不是审阅试卷,只是监考,那问题不大。要说怎么防止舞弊,臣还真有些心得,回头和刘大人他们说说,再给皇上您上个折子。”
皇上也笑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