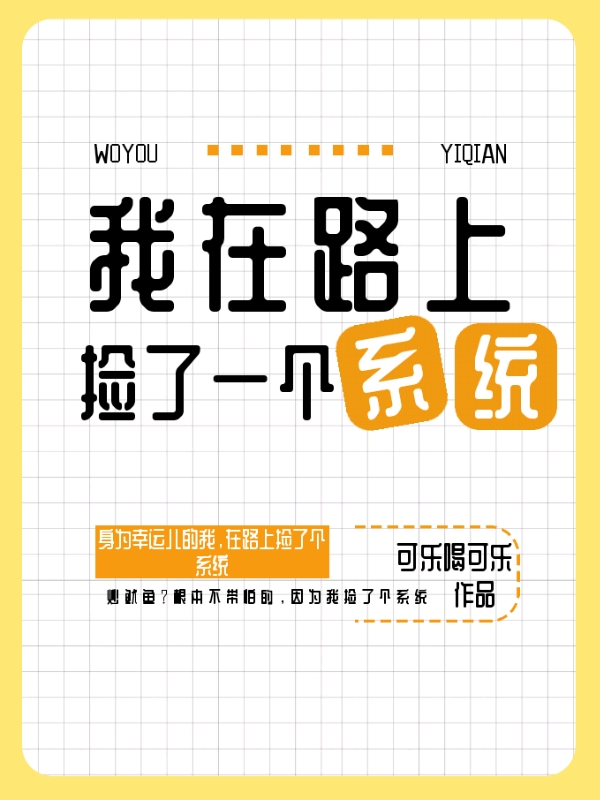每个人对于自己幼儿时期的记忆大多都是很模糊的,我也不例外,我能记得的都是一些片段,零零散散的,还有一些事情,是大人们说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们就先从我最最小的时候说起吧。
我的奶奶因为小时候发烧吃了牛黄,所以被人称为:疯子。虽说是疯子,但是常人很难感觉到她是疯子,因为她的说话办事很利索,就是不那么的讲卫生。
妈妈刚生下哥哥时,因为爸爸在煤矿上班,妈妈要在学校教书,所以产假结束后,就把哥哥交给奶奶照顾,说,孩子饿时就抱到学校来给他喂奶。
但是,奶奶是个“逛山”(陕西当地对喜欢到处乱逛的人的一种称呼),她走到哪里坐到哪里,一坐可以坐一天,谝一天的闲传,就算哥哥饿的哭的不行,她也不会把哥哥带去学校吃奶,就这样照顾几个月后,哥哥得了严重的胃病,是饿下的胃病。
没办法,学校得教书,家里老人又靠不住,所以就在村里找了一个嫲嫲(第一个三声,第二个二声),这是一种称谓,也是一种敬称,村里有这种称谓的人只有这一个,她帮助妈妈照顾哥哥,这样哥哥才慢慢的好了起来。
到了我出生后,因为有了哥哥的前车之鉴,所以妈妈就从学校请假一年,专门在家带我。妈妈是农村代课老师,也就是在照顾我的时候,国家给一定年限、资格的农村代课老师发放“民办教师资格证”,因为妈妈请假在家,所以妈妈的名额就被当时某一个人通过关系顶替了。
听外婆经常唠叨。我刚出生时,她给我洗屎洗尿洗了四十天,那会我能吃能睡还能拉,身体从小就吃的好,吃的壮。
他们说,我在十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走路了,只不过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才开始说话,当然,这些我都没有印象,而我唯一有印象的是,我两岁多的时候已经和村里五岁多的孩子身高不相上下了。
那时候的农村是快乐的,村里面的小孩子有好多好多,大一些的上初中,大部分都是上小学的,还有不少的一些就是我们这些了,没上学的。
还记得那会最好玩的是,有戴帽子的小孩从我家门口过,我悄悄的走到他们的后面,猛的摘掉他们的帽子,然后扬长而去,就这样,他们就哭着嘴里还嘟囔着跑回家,嘴里哭喊着“雷雷把我的帽子抢跑了”,不一会儿,小朋友的奶奶、爸爸、妈妈们结队而来,到我家领自家孩子的帽子。
而我也乐此不疲,原鼓旧锤的继续着。
隔壁家的姑姑和村西头的峰哥谈恋爱,而我就是那个电灯泡,没错,我就是那个最亮的电灯泡,他们每次出去看电影,第一件事先是抱着我,以带小孩的名义领着我出去玩。
农村那会家里有人去世,家里情况好一些的会放电影,放烟火,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只要白天听到哪里有喇叭响,放的戏曲、哀乐,就知道有电影可以看了。听着声音,基本可以判断是哪个村子,等到下午的时候,村里就有信息传出来了,“王家村里老了人,今晚开始放电影,连放三天,晚上放通宵”。
傍晚时分,峰哥就从村西头过来村东头,叫上隔壁家的姑姑,两个人到我家门口,喊:“雷雷,走看电影去。嫂子,我们带雷雷去看电影了哈。”妈妈回应道:好的,你们照顾好雷雷。
就这样峰哥把我往脖子上一架,三人组就这样出发看电影去了,电影放了啥,我不知道,反正就记得,我一会坐在姑姑的怀里,一会躺在峰哥的怀里,没多久我就睡着了,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麦尖子(麦秆堆,陕西话的称呼),在堆子的下面把麦秆掏出一个小洞来,做了一个小窝,把我放进去,用麦秆稍微盖一下,然后他们就扭头,回去继续看电影去了。
等到后半夜他们也困了,就回到麦尖子这里把我刨出来,背到背上一起回家去了。
这样的遭遇我经历过太多次,记忆很模糊,反正电灯泡当的很是荣耀,很是宝贝。
谁知这样的遭遇也被姑姑的弟弟,叔叔如法炮制,继续享受睡麦尖子的待遇。
每个人对于最早的记忆,都有那么一些片段,久久难忘,以上仅仅是我的最早记忆片段的几片,后面还有很多,且听我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