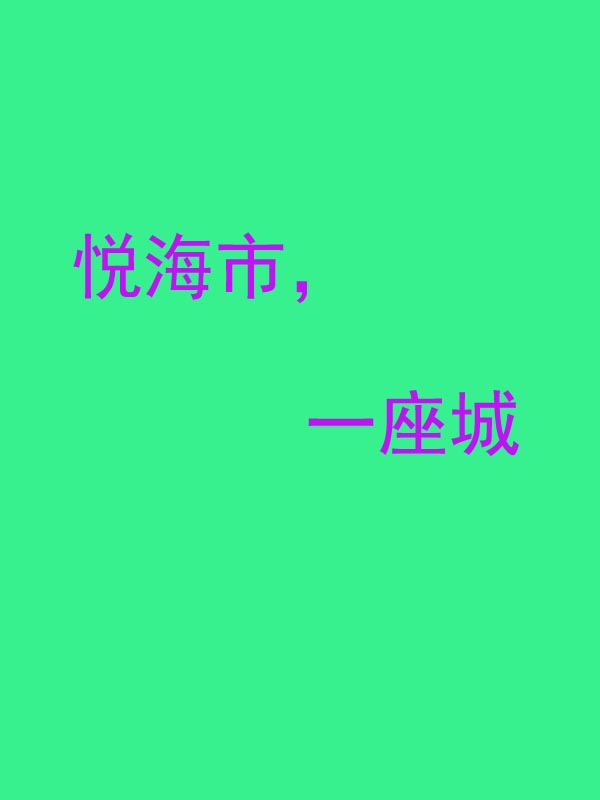9·桃花运
“春华,你今年十七,我表妹二十。女大三,压金砖。今年你们结了婚,明年就可以抱儿子咧。”吉顺嫂子兴趣正浓。
她是慧琳的表姐,她在心里是无论如何都要替自己心爱的表妹玉成这一门亲事。
赵春华的父亲从两里外的大龙河区集市上赶集回来了,他听了吉顺嫂子的介绍,高兴的连连说:
“有这样的好事,天下哪里去找?儿子快快答应啊。”
父亲见赵春华对自己不理不睬不作声,脸阴阴一沉走了出去。
吉顺嫂子又对赵春华说:
“我表妹在屋里挣工分胜过男劳力,这些年她哪年都挣五千多分!这几年她攒钱自己买几床大棉絮,还买几套被褥铺盖。春华,我表妹她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说结婚就马上结婚,不要你花费一分钱,更不要花费你一粒米。”
那年头,靠工分吃饭。能挣工分,就像如今能赚工资一样是硬本领,也就证明了女孩慧琳有结实的身体与充足的体力。
赵春华瞅瞅门外,看见自己的几个同龄小姐妹正探头探脑的在外面充满兴趣偷听。
一想到她们明天准会说,那么好的一床垫棉絮你都不要,赵春华就觉得自己的脸面在发烫。
只要赵春华他点一点头,眼前这位叫做慧琳的漂亮标致的女孩就可以跟他同床共枕,满足他的需求。
可是她即使有冰雪般的肌肤又怎能抚慰赵春华这个读书人那个时代才有的空荡的心灵?
然而赵春华他就是一个字也不能说出来。
青春靓丽的慧琳姑娘站在赵春华的面前,那脸上红是红白是白,于羞红之中越发千姣百媚。她在等待赵春华走过去拉起她的手,向她轻轻而温存地说:
“姐,我们结婚吧。”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走,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
赵春华恨不能拿一把刀子划开自己的难以表白的胸膛。说一句推辞的话语,他深怕自己会深深的伤害这个女孩。要娶她 自己却没有做好起码的心理准备。
母亲抽完一袋旱烟,拿眼神看看赵春华,将铜烟斗在天井的条石上磕磕,说:“婚姻大事,事关你自己一辈子,你自己要拿定主意。我做娘的也不好怎么说。”
赵春华知道,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不敢说二话,但她今天却在明显的支持着自己。
又过了好一会儿,慧琳姑娘自己冷静了下来。她走到母亲面前,拿桌上的旱烟给母亲装上,用一个优雅的动作划一根火柴帮母亲把烟点上了,说:
“婶,要怪就怪我。都是我太性急了,没给弟弟一个心理上准备的时间。”
母亲说:“慧琳,你是个好女孩,好姐姐。弟弟他还太年轻,没有经历过结婚这么大的大事。你大人放个大量,不要计较他。结不结婚,你让他考虑几天。听他给信给你。”
到了夜里,堂叔家小赵春华一岁又早一年半就出去了读高中的堂弟来到了赵春华的家里,对赵春华说:
“哥,我还生怕你头脑一发热就真的要跟这个女孩结婚了呢。听我爸一说,我都好替你着急!哥,我知道你心里是有像雄鹰那样到蓝天中去展翅翱翔的梦的。”
这个堂弟是真正比自己多受了一些教育,说话似乎也有了雄辩的口气:
“哥,现在高中里开的新课本里就有一门课叫《工业基础知识》,是为以后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做准备的,也是为你实现飞上蓝天的梦做准备的。”
火塘里的火光映在堂弟那似乎充满青春热血的脸上,他继续用雄辩的声调劝说:
“哥,如果你现在就结婚,就等于你这一辈子完全固定难以改变了。即使国家以后有了工业化时代,你也可能只能被边缘化了。再说我吧,学校开始办高中那会,我就是做梦也梦不到我现在可以进入县里办的师训班读书,并且半年后就可以出来当老师的呀。”
说完,堂弟果真拿出那么一本小小的封面上印着《工业基础知识》的课本来给赵春华看。
堂弟的一番话语,真真的令赵春华振聋发聩,也脑里热血沸腾。
赵春华拿过堂弟手中的那本书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真的看得很细致也很认真。
别说它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课本,它在赵春华的面前铺展开来的,却是一个让他与同一代人感觉得到的可以进入新生的全新的新天地。
赵春华在心里决定了:第二天他要去一趟毛知春老师的家里,问一问老师和师母,自己是该读书呢还是该娶老婆。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赵春华觉得自己知识与见解都不够,他需要一个比自己站得高也看得远人来教导和指引自己。
在家里,父亲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就连赵春华的终身大事也不例外。
因为在那个大集体几乎没有粮食可分而经常有人饿死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几年,是父亲用他的那双粗糙的大手日以继夜地搓神香,然后挑到集市去卖。靠微薄的一点收入买来昂贵的粮食,让他的全家七口人存活了下来。
父亲跟着他苦命的父亲,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家里一贫如洗。他们家没有土地,也没有一技之长。他的三十多岁的父亲便去给戏班子当挑夫,一年下来才挣得两块大洋。
那一年他父亲的腿上长出两个很大很大的毒瘤,家里没有钱医治,他亲身感受了人体所不能承受的痛,亲眼目睹着自己的父亲因为剧烈疼痛而承受受不了的生命之痛。
他的父亲痛得用牙把木床的床板咬得稀烂,有时痛得在地上滚爬,牙齿咬得地上的石子“咯呲咯呲”响。
在一个夜静人深的冬天寒夜,他的父亲痛得没有办法,用一根长长的布腰带悬上楼莖,结束了自己三十几岁的生命。
从此父亲便失去了他自己的父亲,央求大叔大婶撬下屋里几块破旧的楼板合成一个匣子,就着那件破旧的棉袄,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早晨草草地埋葬了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即使是巧媳妇也做不了没有米的饭,改变不了寡母孤儿饥寒交迫的生活状况,唯一的选择只有出门改嫁。
母亲出门改嫁后,才只有六岁的父亲孤苦无依,实在饿得受不了,就背一把旧锄头去别人挖过了的番薯地里落(la)别人没有挖干净的番薯度日。春夏五荒六月的日子,到山里捋些臭菜叶,用火烤烤,央求伯伯婶婶给几粒盐搓搓充饥。
后来是一位远房叔公看着实在不忍,就叫父亲跟着他生活。那位叔公自己也十分贫困,就靠着搓神香卖勉强度日。
父亲八九岁,就能双手倒立着在村中有着“进士”匾牌的水沟以下的晒谷场上用手“走”几个来回,还跟着那位远房叔公学会了潜入到深深的河水中去捉甲鱼。
从十岁开始父亲就跟着那位远房叔公学搓神香度日。
父亲没有上学,却在后来的日子里能靠自己琢磨着搓出当时唯一一个人的能燃点七七四十九天的寺庙打醮用的盘龙大香,把他的劳动成果打人湘西南以致广西贺州一带的市场。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可是我长到八九岁时还听到他读和唱一大本一大本的故事书如《凤山遇母》《薛仁贵征东》。
不过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文化教育也局限了他。
父亲经常说,以前的时代读书有用,读好了书的人可以考秀才考顶子(指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成为国家的栋梁。
“现在读书没得用了,你看看那些读了大学出来的老师干部,打倒的打倒,下放的下放。邻村有个人读了大学,是有了工作,可老婆孩子被下放回家,管不了老婆也管不了孩子。
老婆孩子是从来没有做过事的,提又不能提,挑也不能挑,多遭罪。”
父亲还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冯丽娟那个生产队分红薯,地在五六里之外,红薯就分在地上。一家人搬了三四天,脚都走红肿了,肩膀也磨出了血,活脱脱像以前的败兵粮子,才把那几百斤红薯弄回了家。
赵春华还记得冯丽娟在全大队开会时唱歌时那美丽俊俏的苹果脸庞和她那嫩脆而又约带沙哑的歌声。
她的唱歌赵春华欣赏,但她的做事赵春华却瞧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