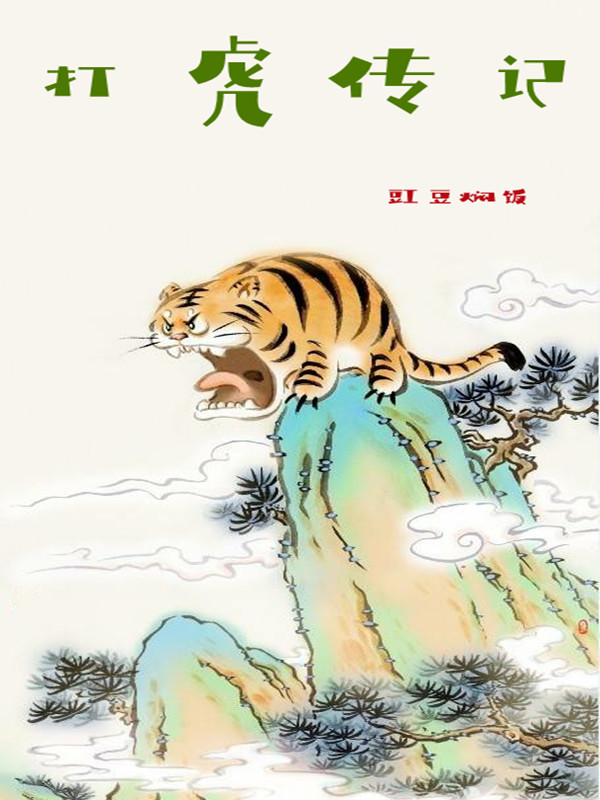二妈道:“多蒙老爷、奶奶看顾,老婆子敢不用心?但今年时年好,小户人家可以度活,都不肯出来。前西门张翰林老爷家,也要雇一个,至今尚无。既蒙老〔爷〕吩咐,且待我去寻问,只恐急切难有。”
岳母道:“这是一项大事,未满月的孩子,可少得乳么?”这几日亏得管家富方的妻子养住,他孩子虽大,幸有些乳,暂令他喂,亦非常久之计,你可以用心去寻,自有重酬。”
二妈道:“既然如此,我就去!”遂辞了出门而去。
次日,只见二妈来了,岳母问道:“可有了么?”二妈道:“我来与老爷奶奶商议,昨日回去,适与隔壁陶四妈说起雇奶妈之事,他也是惯做媒的。
“他说有一个山东人,姓刁,夫妻两口,都有三十一二年纪了。带了一个女儿,也有十四五岁了。到此处投奔亲戚不着,流落在此半年。
“他们有个孩子,未及周岁,才死了四五日,正有乳哩!只是要卖身,不肯单做奶妈。实是一件凑巧的事,只恐老爷嫌他外路人,或者不要,故此特来商议。”
岳母听了,遂令丫鬟到书房中,请出老爷。丫鬟领命,即去请了岳父来。岳母把上项事说知,岳父对张二妈道:“我家人尽多不用买,只是燃眉之急,也说不得了。
“你就去叫他二人来,我看一看,问明他的来历,再议便了。”二妈道:“既如此,我就去唤他来。”起身就去。
不多时,同了那陶四妈,领了一个妇人进来,张二妈指点他,见了岳父、岳母的礼。岳父看那妇人,果然只有三十一二年纪,却是生得美貌风骚。
岳父就问道:“她丈夫在那里?”二妈道:“在大门外,禀过老爷,方叫他进来。”岳父即令陶四妈,唤他进来。陶四妈就去叫他。到了厅上,对岳父磕了头,站旁边。
岳父道:“你叫甚么名字,原籍那里,因何在此?”那人道:“小人姓刁,名仁,妻子邢氏。本贯山东郯城县人。当时扬州府有一个姓胡的乡宦,在山东经过,娶了小人的妹子为妾,一向不来往。
“今年山东遭荒,没奈何挈家到扬州,一则看视妹子,二则原想投奔他家,不意妹子已死。亲人不在,竟不相干。
“守候了一月,每日到他门首,可恨那些管家的需索门包,方肯通报。幸在守候,得做官的出来拜客,小人发急了,只得扯住了轿子,叫唤起来,他方才知道。
“不想见我身上褴褛,甚是薄情,只叫我在寓处等候。次日却差一个〔人〕送了四钱银子,来与我折饭,小人愤恨,不收他的,赶到门上,数落了一场。
“他恼我,叫家人出来打我,幸得两邻舍的劝开了。小人回到寓处,进退无策,不能回乡,只得把几件衣服抵还了饭钱。
“过江来,别图生计,住在西门外饭店中,已经五个月了。没奈何,思量投靠人家,昨日陶四妈说老爷府中要奶妈,小人情愿老婆卖身。小人一生忠厚诚实,倘蒙老爷收用,虽赴汤蹈火,也不敢辞的。”
岳父见他身材长大,说话清楚,就有几分喜他。便说道:“我本意只要雇奶妈,不肯用买,今见你说来,是个异乡之人,流落在此,我且收用你。“你的妻子在内做奶妈,自然另眼看顾你,俟我小相公长成之日,你要回乡,悉听自去,我亦不计较。”
刁仁道:“受恩深处便为家,既蒙老爷抬举,小人粉身难报,即使驱赶也不忍去。”岳父大喜,问他要多少身价。
刁仁答道:“小人该店家叁个月的饭钱,不过十余两的银子,其外亦无使用,总不与老爷较论。”
岳父一发道他忠厚老实,便说道:“你夫妻三口,与你三十两身价,算还饭钱之外,也要做些衣服穿,你且去写了身契来。”
刁仁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起来到外面寻了纸笔。他原也识字,自己就写了一张卖身契,同两个媒婆,俱签了押,同送到富家。
岳父收了,叫管事的兑了三十两银子与他,两个媒婆各人赏了一两,就叫同刁仁前去收拾行李,并领女儿前来。
刁仁即同陶四妈到店中,算还了饭钱,他也没有什么行李,不费工夫,领了女儿前来了。岳父把他女儿一看,年纪虽小,却是生得丰姿秀丽,态度娉婷,不施朱粉,红白自然,袅袅娜娜,有十分标致,竟不像这等人养的。
因对刁仁道:“你女儿生得如此,日后须要择一个好人家匹配他,不可误了他。”遂令张二妈率领进去,拜见岳母、小姐。
岳母、小姐亦爱他,令收拾一间房,与他母子在内宿歇,哺乳公子,打发媒婆起身。那陶四妈又叮咛教导他夫妻一番,作谢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