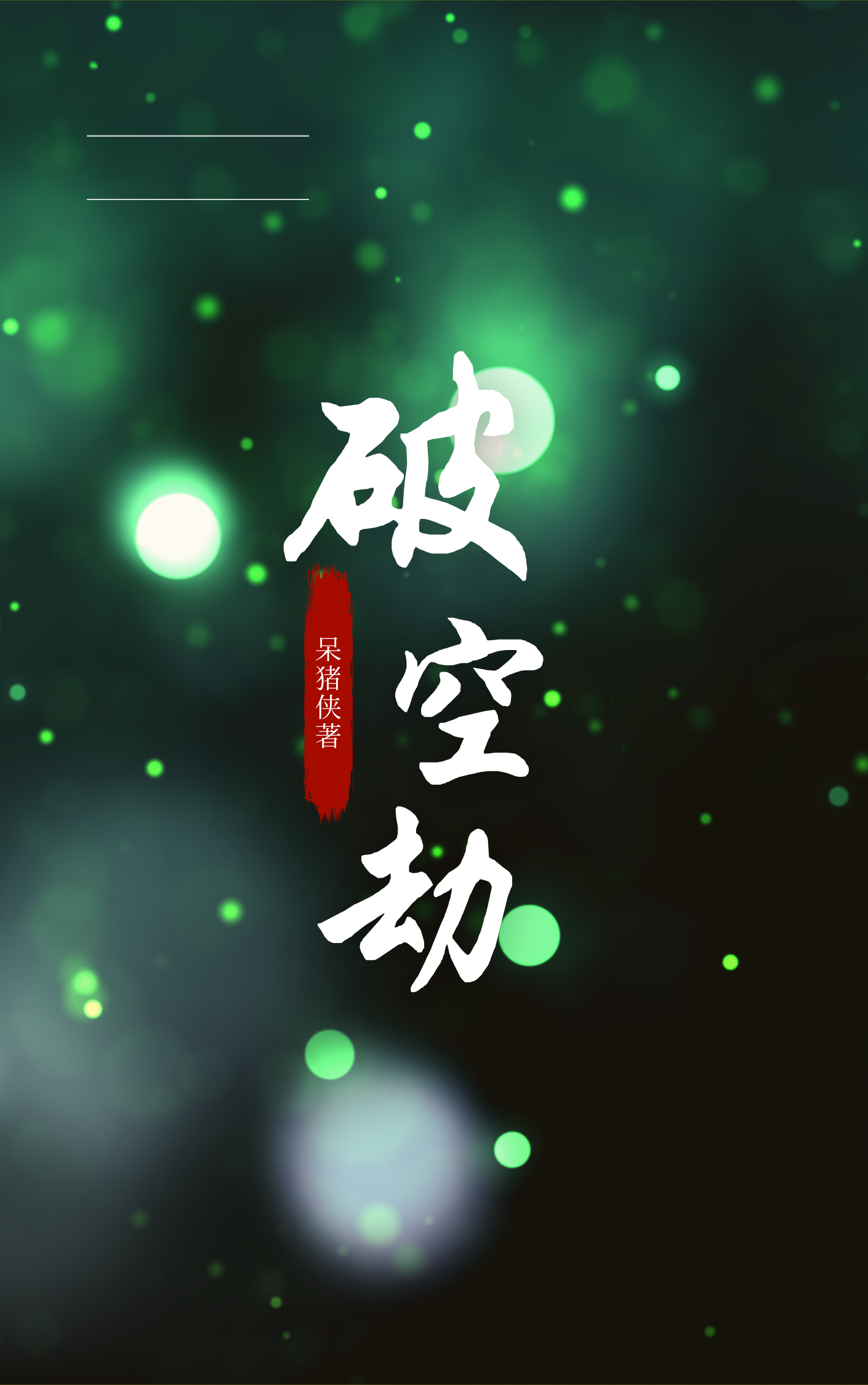我暗喜道:“事有凑巧,看他怎生见我!”遂叫珍儿跟了,望东门外尘远庵,访超凡。不移时便到,见依然疏柳苍松,板桥曲水,想起当年作寓之时,不觉感慨系之!
因口占一绝。诗曰:
青锁横塘杨柳烟,旧时风景尚依然。
当年吟遍残萝目,此际临留未敢前。
到了庵前,只见门儿闭着。敲了两下,里面走出一个老僧来开门,见了我,便举手请进,至佛殿上坐定。我便问道:“超凡师何在?”
老僧道:“超凡是贫僧道友,已回首半载了。今回首后,贫僧即在此。”我大惊道:“他身边并无徒弟,谁与他入龛举火?”
老僧道:“都是本地檀越主持的,如今贫僧立他牌位,朝夕拈香。”我即起身,叫他领至牌位处,倒身拜了四拜,站起来想着他的旧谊,不觉潸然落泪。
老僧道:“超凡是江南人,听相公声音,也是江南,莫非是令亲么?”我说道:“非亲也。小生姓广,超凡虽是同乡,然素昧平生。当年游学至此,承他意气相留,久寓于此。
“一别数年,今日特来看他,不想他已西游,使小生徒抱人琴之感!”
老僧道:“相公可为不忘其旧,难得难得!”我说道:“不枉到此一番,超凡虽逝,幸老师在此,特奉白银二十两,早晚相恳,备些香烛,供奉他,也尽小生一点故人之谊。”
说罢,即令珍儿送上。老僧收了,即要收拾素斋相待,我止住。因索笔砚,书一律于壁间。诗曰:
忆昔曾经借一枝,乾坤意气属吾师。
何当客梦初回日,却是浮生未议期。
荒草未萦三尺墓,寒花犹发百年姿。
也知灵爽应相见,或在更残人寂时。
书毕,叹息一回,又到各处看了一遍,触物伤怀,不禁凄怆。就别了老僧回到店中,与尚义说知,因感念超凡,竟夜不快。
次日就往枣强发进。到了县里,天色将晚,锦石林还有三十里,不得赶到,就在东门外,寻了一店住下。
我又吩咐家人道:“此处县官姓王,是我同年,我不去见他,切不可走了消息!”家人应诺了。
我在房里歇息了片时,即到外面小解,解完了,转来只见对门客房里,一个女子,同着一个人携了手,在那里说说笑笑顽耍。
仔细一看,那女子十分面善,这女子见我看她,也回头端视,似有所思之态。我不好久看,就进了房,细想了一会,暗想;
“这女子好像小凤模样,看他见了我,觉有惊疑之况,若说是他,却是如何在这里?即叫尚义去问店家,那女子姓甚、那里人?”
尚义去问了来,说道:“是本乡的妓者乌媚娘。一个山西客人接来的。”我说:“这等说就不是他了,却为何相像得紧?”
尚义道:“老爷说甚么相像?”我说:“这女子像我一个熟人。”正说间,只见店家拉了张成去讲话。须臾,张成进来道:
“也古怪,那对门的表子,叫店家来问我们姓甚,那里人。小的含糊回了他。”我沉吟道:“一发可疑了,他怎么也来问我?其中必有缘故。
心上好生鹘突,意欲再细认一认,那女子又在里面陪客吃酒,不走出来。欲待叫他过来,觌面端详,又碍着别人叫的表子,不好意思。
即着张成去叫了店家来,问他道:“那对门房里的表子,在那里住?”店家道:“在西门外。相公若爱他,明早送那客人起身了,小人对他鸨儿说了,留下在此,相公顽一日便了。”
我为了弄清情况,就说道:“好!你去与他说罢。”那店家巴不得多住一日,赚几个钱儿,欢喜不尽的去了。
当下吃了晚饭,睡了。我心上狐疑,一夜不睡,到得天明,即起来了。那对门客人果起身,店家即送那表子过来,道:“相公,我送媚姑娘来了。”
我正在洗脸,洗完了,那表子已站在面前。两个大家定睛一看,表子开口问道:“相公,可姓唐么?”我愕然道:“你可是小凤姐?”
那表子,即潸然泪下道:“我正是小凤,这等说果是唐姑爷了!为甚的我央主人家来问,又说姓广?”我见果是小凤,惊喜相集道:“一言难尽,且慢慢与你说!”
此时家人们见小凤,叫我唐姑爷,正不知其中缘故,只是呆看。那店家道:“原来相公与媚娘是旧相知,怪道夜里他叫我来问。”
我说:“当时在此经过,认得的,昨夜一时认不真了。”店家不知缘故,也不管这个闲事,应了一声,自去了。
我便打发了家人出去,独留尚义在内,遂同小凤炕上坐定,说道:“我昨夜偶然见你,因别数年,急切难认,正在孤疑,却好你又托店家来问我,一发疑惑了。
“故今日又多住这一日,要辨了真伪。不想果然是你,你却如何落在此地,可将别后之事,说一说。”
小凤道:“当初老爷犯事,即着我父亲领了公子,躲在山东。后来,我父亲赌钱,废了家,因出外做买卖,不想涉在盗案监,押在故城县监里。
“彼时沈君章只说去救我父亲要使用,与我母亲商议,将我卖了。彼时说那人姓乌,是真定府大财主,娶我为妾。那知道是个忘八,将我哄入娼家,流落此地了。
“当初我父亲,原同沈君章在兖州府住,后因追究公子的信急起来,又同了沈君章迁至高唐州,开了饭店。
“不想你下在店中,我父亲昧心,与沈君章商议害你。我闻之心如刀割,又无法可救,亏你走了,又喜之不胜。今日天赐相逢,我尚有无数言语,一时说不尽。
“只是姑爷一向在何处,可曾到家?当初自从你出门之后,我何时不想,今日也将数年的事,对我说知。”
我听得他说父亲与沈君章谋害的话,方省悟道:“当日我原疑沈姓与我无仇,为何要害我?那知是你父亲的缘故。只是沈家屋里,还有个姓王的,你可知么?”
小凤道:“这就是我父亲了,当时怕公子的事发觉,故此改了姓王。”我立刻恍然大悟,说道:“数年疑惑,今日如梦方觉!”遂将本身的事,也大略说了一遍,只未说出做官的话。
又问她道:“你父亲如今何在?公子可长大了?”小凤道:“我曾央人去打听,说我父亲死于故城县监内,母亲就跟了沈君章,公子与高唐州州官一个乡亲,姓史的过继去了。”
我就问道:“那姓史的,那里人氏?”小凤道:“这却不知,除非问那姓沈的方明白。只是我闻得沈君章,又搬往河南彰德府去了,所以我这里一向音信断绝了。”
我想:“我如今竟要往河南,正好寻他。”小凤道:“当初姑爷若肯收我在身边,岂得落此一番火坑!”
我笑了笑说道:“彼时实因你尚是处子,恐所愿不遂,坏你名节,故不敢领你的高情。总是人生患难机缘,俱有定数,断不可勉强的。”
小凤道:“往事休提,我几年来做了浪里孤舟,可怜受尽烟花之苦,今日万分机缘,得遇姑爷,实我见畔岸之时,你岂能不发一点慈心,提我去?”
我笑道:“你看我身飘四海,那有力量提出你去?”小凤道:“我看你今日车马仆从,意兴勃勃,必不是不得意之时。总与姑爷无缘,见我目下这般行径,尚然心如铁石,绝无苦海慈航之意。况今日一会,后会难期了!”
说罢,泪如雨下,将身子倒在我怀里来。我见他那一种韵致,又非昔比,且见他娇啼婉啭,着实怜闵他,已有收他的意思,恐他知了真情,女人见识,高兴起来走漏消息,故不与说明。
此时也便搂住他,与他拭泪道:“你莫哭,且再商议。”正说话间,只见珍儿走来,问道:“老爷,店家问吃什么饭?”我将眼一睃,珍儿便回过口来叫相公。
小凤是伶俐的,早已看破,便道:“我知你做了官了,你不要瞧着他,叫他改口叫相公。”我说:“做什么官,他不过偶然叫错。”
小凤道:“我也不管你做官不做官,只是坐在你身上,设法救我去便了。且问你当初老爷被劫失印,问了军去,你是个女婿,也该替他伸这冤,查出印来,访出公子来才是!为何痛痒无关?”
我说道:“你这话也说来好笑,除非知道打劫的人,才伸得冤。彼时官府通行严缉,尚无影响,你叫我怎样伸冤,怎样查印,怎样拿盗?”
小凤道:“要印也不难,要盗也不难,可怜我是个女子,见老爷家破人离,久抱不平。今日见你,正要说几句知心的话,不想你反藏头露尾,一味哄我。”
我听他说话有因,便搂定他问道:“你可知些缘故么?”小凤道:“要盗是容易,只是你说救我出去也无力量,岂有力量去拿盗!对你说也无益。”
我立刻笑道:“我实对你说,你且不可则声,我中过进士,现任河南按院。因一路还有些事情,恐怕走漏消息,故尔如此,不是哄你。你且说打劫的是谁?”
小凤听了,方才喜遂开颜,把积年愁恨,一齐散去。便将沈君章等人打劫的,一一说了,然后提醒我:“只消拿住他,可不是冤也伸了,印也有了,公子也有下落了?”
我点点头说道:“你父亲可知情的么?”小凤道:“想是知情的,如今死了,也罢了。”我说:“但不知那姓沈的果在河南否?”
尚义道:“我知道盛二有个哥,在彰德府住,必然在那里是真,只不知在那一县。”我说道:“既在河南,少不得要寻他。”
小凤道:“如今我的事怎样商议?”我说:“这不难,只消如此如此便了。”小凤大喜,说话之间,吃过早饭,又细叙前事。
小凤又问及尚义,我便将他说知救脱高唐之难,并自己改姓的缘由,细说一番。不觉天色已晚,小凤嘻嘻笑道:
“当初你假道学,辜负我一段深情,天幸今日遇于旅店之中。但我已属败柳残花,不知还肯相纳否?”我也笑道:“不敢请耳,固所愿也!”晚饭毕收拾就寝。
我虽是道学的人,却也值少年久旷,小凤又系遇了心上人,把十年的相思一宵发泄。这一夜的绸缪绻缱,娇痴怜惜之状,难以形容。
直到云收雨散之后,相抱而睡。一觉醒来,已是天明。起来梳洗毕,我即叫店家来,说道:
“实不相瞒,那媚娘实是我家的人,被人拐卖在此,幸而昨日遇着,意思要烦你去对他鸨儿说,愿偿原价取赎。若说成了,自有重谢。”
店家道:“说我便替你去说,只恐他不舍这颗摇钱树。况媚娘是本地有名的表子,相知不少,他鸨儿即使依了,众人也未必依。”
我说道:“只烦你去一说,依不依再相议。”店家道:“使得!”应诺而去。去了一会,只见店门外,拥了一伙人进来,嚷道:“那里来的流棍在此,冒认人口,叫他出来认认。”
原来这些人是店家去说了,那鸨儿纠合来的罡棍。知道是过往的客人,可啖之物,一拥而入,先将小凤拉出去,推上牲口打发去了。
为头两个罡棍,把我数落道:“那里走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人来,你有几个浪钱,在此卖弄,阚丧子!睡了一夜,也就便宜了你。怎么捣出这些鬼话来?那一个是你的家人!”
就动手打过来。尚义拦住说道:“打不得的!”那人就把尚义一掌,回手又要打我,亏了从中一个老成些的人,见我一表非俗,不知来历,恐打出祸来,和身劝了出去。
众人又吩咐店家,叫立刻打发媚娘昨夜的房钱,赶他起身。说罢,众人洋洋得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