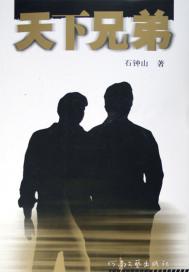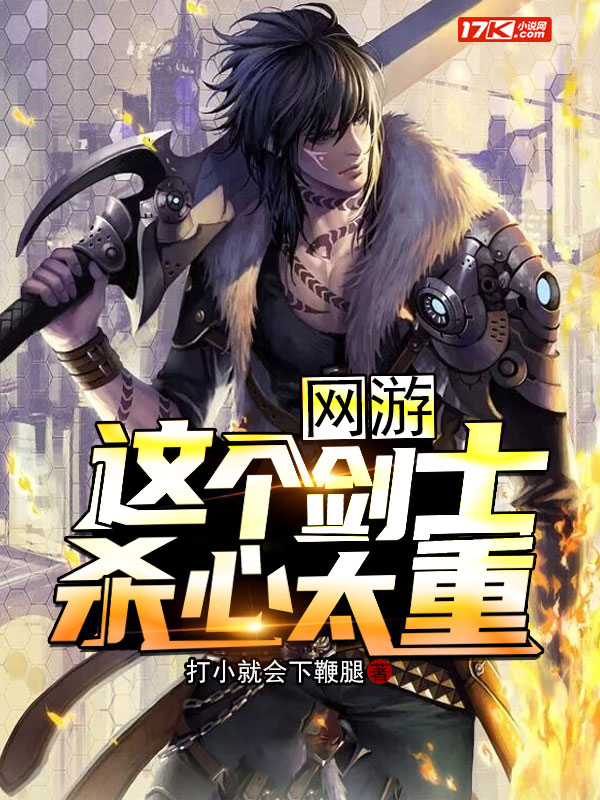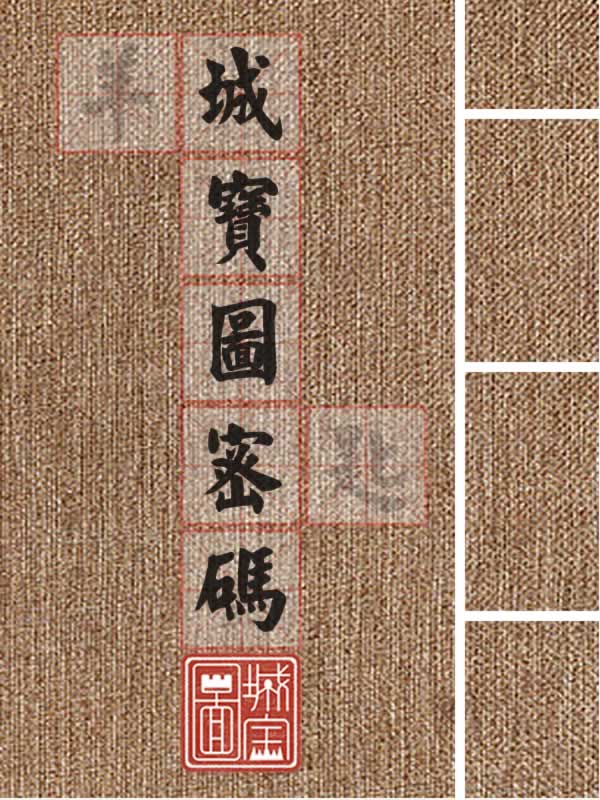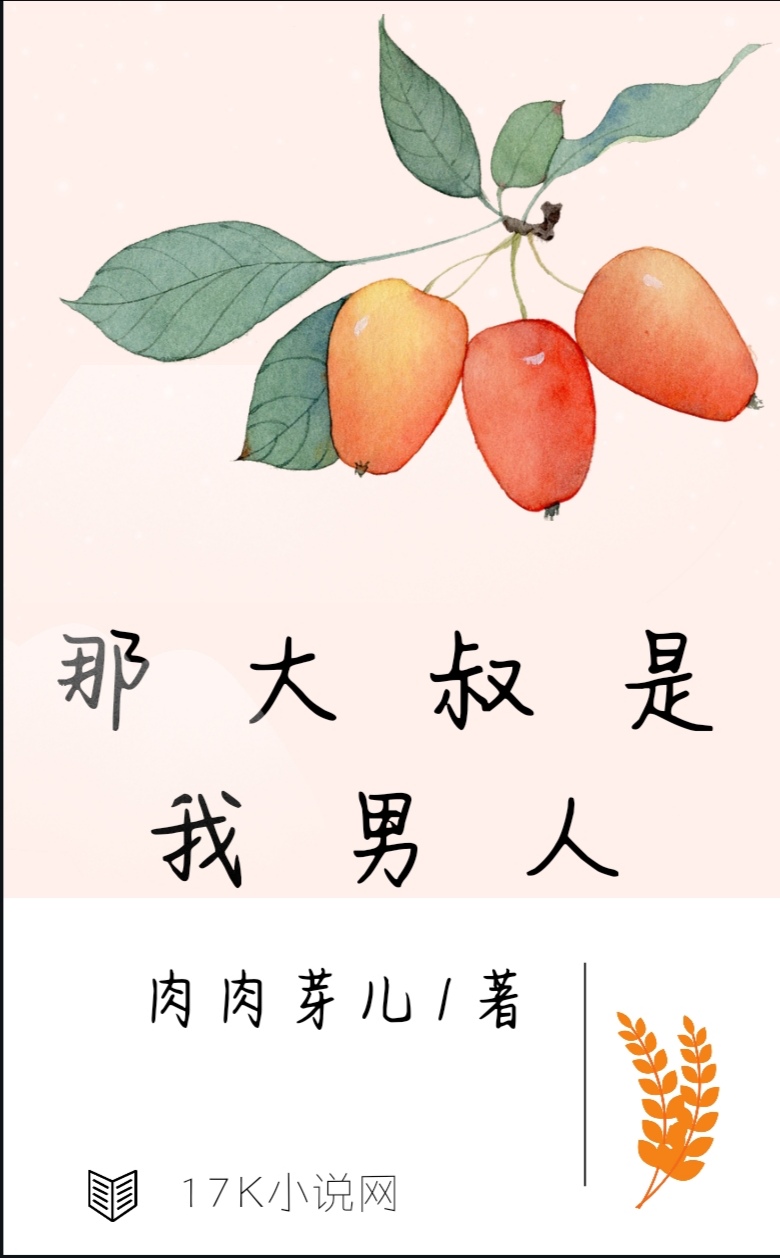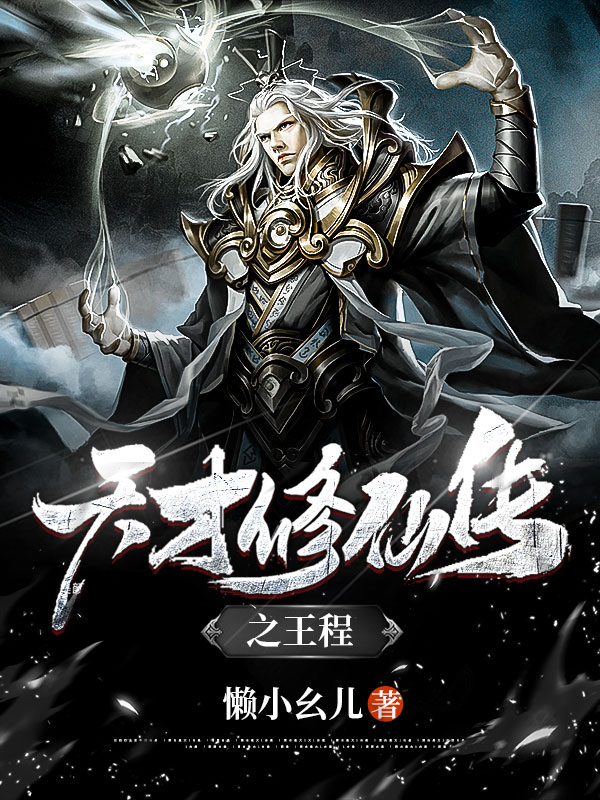原文
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
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
——李世民《帝范》
白话
能容纳一头牛的大鼎,不适合用来煮鸡;狸猫只能捕鼠,不可以让它去与猛兽搏斗;只能放三十斤东西的容器,不能让它去容纳长江和汉水;能装几百石粮食的车,如果你只放几斗几升谷粟,那么它就无法装满。这么说来,大的东西和小的东西容量不一样,将轻的东西当重的东西用,就会不适宜。
有的人智慧多,能力大,有的人智慧少,能力小。对于才能小的人,不能让他担当重任。对于能力不大的人,不能给他大的职务。任用员合适,那么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操劳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国家的治与乱,都在于得人和失人。用人得当还是失当,这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
家训史话
唐太宗登基后,因为开国不久,整个朝廷的结构都在建设与调整之中。那么把手下的有才之人分别放在什么位置上才能够成为一个最合理、最有效的组织结构呢?
房玄龄处理国事总是孜孜不倦,知道了就没有不办的,于是唐太宗任用房玄龄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军令、政令,阐明帝事,调和天人。入宫禀告皇帝,出宫侍奉皇帝,管理万邦,处理百事,辅佐天子而执大政,这正适合房玄龄“孜孜不倦”的特性。
魏征常把谏诤之事放在心中,耻于国君赶不上尧舜,于是唐太宗任用魏征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
李靖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唐太宗就任用李靖为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刑部尚书的职责是:掌管全国刑法和徒隶、勾覆、关禁的政令,这些都正适合李靖才能的发挥。
房玄龄、魏征、李靖共同主持朝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上层组织。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合理地搭配起来。李世民在房玄龄研究安邦安国时,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具体的办法来。但是,房玄龄却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不善于整理。他的许多精辟见解,很难决定颁布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想事,但却善于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做周密分析,精于决断,什么事经他一审视,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律令提到唐太宗面前。于是他们俩搭配起来,密切合作,组成合力,辅佐自己,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房(玄龄)谋杜(如晦)断”的人才结构。
古训今鉴
唐太宗的“房谋杜断”的用人搭配体系是非常高明的。用人不仅表现在人的量的多少, “全才”是极少有的,“偏才”是绝大多数,但“偏才”组合得好,就可以构成更大的“全才”。通过这样合理的组织结构来弥补人才的不足,以求达到人才的最佳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