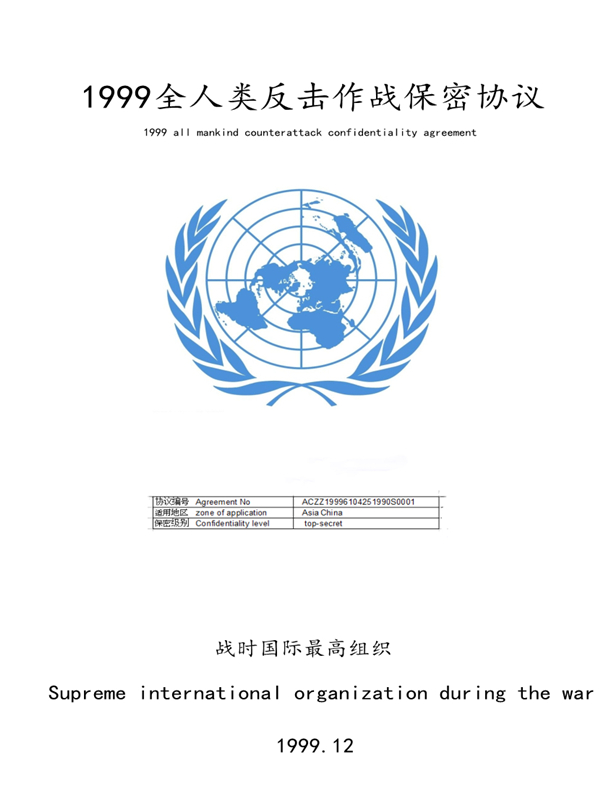阿楚看着冯妙妙带着丫鬟气冲冲的走了,不禁担忧道:“姑娘,要不去……回禀夫人?”
陆泠眼眸低垂,让人看不清神情,端着茶盏,吃了一口,“不用,告诉母亲,也是让母亲烦忧。”
“那……表姑娘若是向老夫人说了什么不利姑娘的话,到时斥责下来,苦的也是姑娘你呀。”阿楚的眉头皱成‘川’字,忧心道。
看着丫鬟如此紧张忧心,抬手把她眉头抚平,冷笑一声:“平日是我太过谦让于她了,真是被惯的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她想要什么,便能要去?呵,祖母对她是比对我好,可我兄长是长孙,以祖母重男轻女的性子,讨不了什么好去。不如借此机会,杀杀她乖张的脾性,让她知晓知晓谁为主,谁为客。”
阿楚却没放下心来,看着自家主子悠闲的吃着茶,劝说道:“那就让她这么走了?姑娘不让人拦着?好歹在她之前到老夫人面前分说分说呀。”
“不着急,也得让人家好好说说心中的委屈。”陆泠老神在在的捧着茶盏,眸光映出茶叶随水沉浮,嘴角上弯,以为唾手可得的东西,快要得到时,发现自己不能沾染分毫,这才更受打击。
随手拿起平日看的话本,翻了十几页,才有小丫鬟来报,老夫人让她前去墨韵堂。
……
老夫人所居的墨韵堂位于府中的中轴线上,与沈氏的正院以一片竹林隔开。
老侯爷十三岁时,跟随太祖皇帝打天下,后太祖皇帝突然崩逝,又遵从太祖遗愿,辅佐高宗皇帝。为巩固朝纲,几次征战,攻打南蛮,终让南蛮退居五十公里,不敢来犯。
如今老侯爷五十有七,身体硬朗,每日清晨必会到竹林练剑。
陆泠带着丫鬟穿过竹林,看见一花墙,老夫人武氏身边的蒋嬷嬷带着几个小丫鬟站在墙下。
“姑娘。”蒋嬷嬷行礼道。
陆泠点头,示意她起身。
几人沿着抄手游廊到了正房外,自有小丫鬟为其掀帘。
陆泠弯膝行礼,道:“祖母。”
眼眸向上看了看。
武氏身着藏青色绣万寿纹样长襟,每个万寿纹样上均有米粒大小的珍珠点缀,头戴抹额,发间插着一赤金金簪。
不苟言笑的坐在榻上,面有怒容。冯妙妙坐在武氏身边,眉梢上挑,很是得意的看着陆泠。
“跪下!”武氏厉声道。
陆泠听话的跪在地上,面露不解,“不知何事,让祖母如此气恼?”
“你说为何?妙妙自幼不在我身边,你们这些锱铢必较之人,真是见不得我好过!看看你,可还有侯府贵女的气量,不过是幅画,我还没死呢,就这么对待你表姐了?和你那母亲一个样!”武氏一个巴掌拍在案几上,眉毛竖起,怒斥道。
屋中的丫鬟仆妇具敛声静气,不敢抬头。
冯妙妙居高临下的看着陆泠,心中舒爽不已,哼!侯府嫡女又如何,还不是老老实实的跪在地上。快意的再添把火,“外祖母,您消消气,表妹是侯府贵女,妙妙不过是一小官之女,如何与其争辉?这些年,父亲多受上司打压,家中境况愈发不好。幸亏有外祖母垂怜,接我进府,才能在外祖母膝下承欢,可……终究妙妙不姓陆……让人轻视至此。”
说完挤了几滴泪来,武氏心疼不已,一把抱住她,拍着后背,直道:“有外祖母在,我看谁敢欺辱你!”
陆泠来时已做好准备,神色不见丝毫慌乱,镇定自若的说道:“祖母为何如此说?您看看表姐身上,哪一样不是母亲置办的?那羽缎可是舅舅千里迢迢送给我的生辰之礼,表姐说喜欢,母亲怜她父母不在身边,说送就送了,我亦没有丝毫不愿。头上戴的赤金钗,本是父亲送给我的,表姐说没有金钗戴,便要了去,孙女可曾拒绝?祖母,不问我是何缘由婉拒了表姐,就给孙女定了罪,孙女实在冤枉呀。”
说着说着,心底的委屈一丝丝燃起,眼泪夺眶而出,更显得情真意切。
流泪而已,谁不会!
不等武氏开口,又哭道:“祖母又言及母亲,不知母亲哪里做的不好,这府中大小事宜均由母亲打理,表姐来侯府小住,更是重新修葺了院子出来,供表姐居住。每日晨昏定省,管家侍夫,究竟是哪里忤逆了祖母,让祖母如此不快。”
美人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亦是我见犹怜。
蒋嬷嬷见惯了冯妙妙的撒泼打滚,今日再见陆泠一番泣语,真是高低立下。想到此处,撇了撇嘴,这云泥之别,又从何而比?
作为侯府唯一嫡女,陆泠自幼便受良好教养,怎么行路,怎么言语,都是极尽优雅,便是受了委屈亦不会失态。武氏何曾见过孙女如此哭泣?本来心里软了几分,但又听陆泠为沈氏分说,不免增了些气性,她最厌的就是这沈氏做什么都面面俱到,滴水不漏,让她这做婆婆的一点错漏都挑不出。
想起沈氏,武氏有些心虚,言语间减了几分戾气,“先不说你母亲,你说冤枉,那你说说是何缘由?”
陆泠眼睛一直觑着冯妙妙,见她嘴巴微张,似是要辩解,自己都到这墨韵堂了,怎可给她机会?立刻泪如雨注,道:“那幅丹青可是兄长所画,虽说是年幼时所作,可那幅画曾挂在兄长院中,外男亦曾见过。若是被表姐要去,也没什么,就怕有心之人谣传,说……”
含泪的双眸看了看冯妙妙,紧攥着手帕,放在嘴边,似有千般委屈:“这些我都与表姐说了,可表姐还是……若是污了表姐和兄长的名声可如何是好。”
眼泪一颗颗自美眸而出,没有擦拭,任其洒在脸上。周围的丫鬟仆妇本就看不上冯妙妙在府中大肆敛财,自持甚高的样子,如今自家主子被欺负成这副模样,更是愤怒不已。
武氏看重家中儿郎,听此事涉及长孙,便蹙了蹙眉,眼眸微转,似是在思虑。
陆泠见祖母有犹豫,心中大定。事到如今,自己已经出手,那就要一击即中!若是想高高抬起,轻轻放下,呵,那得要问她干不干!
猛地起身,冲了出去,大声喊道:“即是惹了祖母不快,孙女这就去家祠跪着,向祖宗忏悔己过,是孙女错了,错在不顺表姐心意,不从祖母之言。”
武氏本意是想说孙女几句不是,连带着再斥责沈氏,耍耍长辈的威风,可自己没说几句,孙女便闹的这般大动静。心中惴惴不安,也气外孙女没说其中缘由,让她以为不过是幅名画。
怎会涉及到长孙,这要是传到老侯爷耳朵里,到时受责骂的就是自己了。忙让人拦下陆泠,小姑娘家受些委屈,哄哄就过去了。
可陆泠怎会轻易放过,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本就是想引起祖父的重视。这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说,不过是表兄妹之间的倾慕之情,可往大了说,确实会污了男子的才名。
毓昌侯府如今在江南立府,江南学子又极重名声,‘风流’二字或许不过是场笑谈,可在世家贵族耳中,却是德行有亏。
祖父又怎会任其发生,亏了兄长的声名。
陆泠向过来要拦住她的丫鬟使了使眼色,沿着小道,跑出了墨韵堂,七拐八拐的,好在平时随着祖父学骑射,家祠离墨韵堂亦不太远,一路小跑着进了祠堂。看到地上的软垫,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理顺气息,丫鬟阿宙才进来,气喘不止:“姑……姑娘,你……”狠狠咽了口气,“阿楚去请夫人了,姑娘又何必跪在这儿。”
“做戏当然要做全套。”陆泠淡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