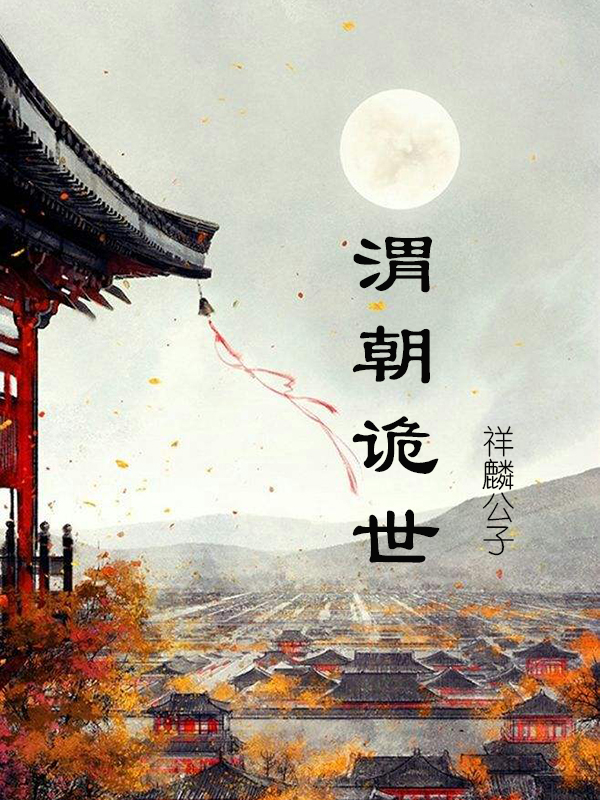樱子问,外面发生什么事?
守门那老者快步走出去看了看,又问了问行人,回话道,“白一凡游街,他们都说,要将白一凡送到秋水城去,曾府众人在江边等着要取他的性命。”
樊威被唬得呼的一声窜出去,忽然又折返回来。
樱子问道,“发生什么事?”
樊威摇头道,“不对──!”他一时又说不出哪儿不对。
樱子问道,“有什么不对?”
樊威又道,“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必定有什么不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脑子飞快转动,樱子吃惊地问道,“你说什么?”她本已很紧张,事情已经最糟糕了,难道还有更糟糕的?
白一凡被人抓住了,难道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樊威道,“他们要送公子到秋水城,这个可能是真的,因为公子得罪了曾府,但不应该这样猖獗,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的,一定──。”樊威的脑子本就不笨,现在因为事关重大,他的脑子忽然变得不够用似的,樱子在旁都听急了,樱子急忙问道:“你想到什么?说吧?”
“他们这样做,必定是故意让我们知道,故意让我们去救人,然后,中间设个埋伏,将我们一网打尽。”
樱子道,“他们为了你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樊威道,“为了抓住我们,花再大的力气他们也愿意的。”
“既然你发现了他们有埋伏,别人会不会没发现?”
樊威不明白她的意思,问道,“别人?别人是谁?”
“白公子有很多朋友,比如他的好朋友高峰。”
樊威道,“高峰比我聪明,他不会轻易上当。”
樱子又问道,“别人呢?还会不会有其他朋友?”
樊威道,“当然有其他朋友,认识他的人不少,公子的朋友也不少。”
樱子道,“就算有埋伏,我们也要去救他,绝不能让他们带白公子走,绝不能让白公子的朋友上他们的当。”
樊威点头道,“对,我们要快,快点识破他们的阴谋,公子的朋友就不会掉进他们设计的陷阱。”
“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就出发。”
樊威抻手阻止道,“不,不能这样走,我们要兵分三路。”
樱子果然是一个好主子,她问道,“怎么分兵?”
樊威说出他的分兵救人办法,樱子认为可行,在地板上划出路线,然后吩咐各人分头行动。
樊威道:“我先潜在人群中,见机行事。”
樱子点点头:“你要靠近他身边护着他。”
樊威点点头,“我会的。”他仍戴着一顶帽子,遮住半边脸面。
蒋金南的行动,正如樊威所想,前头捆绑着白一凡,白一凡满脸是血,显然挨了几顿打,脖子上吊着那把波斯刀,标识为“凶器”。
他被捆在马车的铁笼子里,动弹不得。
那个铁笼不仅坚固而且密实,白一凡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蒋金南认准白一凡的同伙会来救他,所以,前头四条汉子,手持长枪,马车走在中间,马车后又跟着十二人,也是手持长枪,长枪后队就是弓箭队,二十人的弓箭队,大家押着方阵,在街上走过。
这阵势,就象打仗一样,甚至打仗也很少见如此整齐的方阵。
蒋金南毕竟是行伍出身,熟悉列队排阵。
蒋金南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铁笼前后是长枪,如有人来抢白一凡,就会有人用长枪去戳白一凡,那情势,谁都不敢来救,否则,对方就会抢得个死人。
忽然,一条疯牛从街头跑过来,众人一阵骇然,惊呼着四散逃命。
街上不是没有出现过疯牛,阳春三月,春耕夏种,有一二条牛累疯了,跑出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在这个时候出现,就很不正常了。
蒋金南大叫道,“他们来了,这是疯牛阵。”果然,那条牛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低着头喘着粗气冲过来。
前面四人用长枪准备戳它。
后面四人则伸长脖子等着,一旦发生什么意思,他们就拿枪戳白一凡。
忽然,后队二十几人乱了起来,手中的弓箭弦被一条汉子,用一把快刀划断,大家手上拿着一把断弦的弓,不知道如何是好。
铁笼后的长枪队正要准备跟人打斗,却不提防有十几个黑鬼冲上来,他们使的长刀,刀刀要人命,那使枪的何曾看过这阵势?
有三五人慌忙扔下枪逃去。
前队对付疯牛,那疯牛的牛角已经顶到跟前来,大家呼的一声,散开逃命,后队更难挡黑衣人的长刀,纷纷扔枪逃去。
弓箭手也慌忙散开,东躲西藏。
马车上只有铁笼,铁笼里只有白一凡。
蒋金南大叫:“不要慌,大家不要慌。”他自己却慌到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绝没想到败得如此之快。
蒋金南看看铁笼铁锁头,冷笑一声,任你如何乱了场子,也没法打开这把铁锁头。
忽然,蒋金南大叫一声,被人一刀斩下马来,幸好他反应快,及时闪开,这一刀没有斩中他脖子,却唬得他惊叫不已。
蒋金南的人马全乱了套,楼上街边行人指点谈笑。
蒋金南正要重组人马,忽然脖子上架着一把刀。
蒋金南当然认得这个人。
樊威道,“我这把刀要将你的头切下来,也不须多大力气,你说切还是不切?”
蒋金南恐慌地叫道,“不切,不能切,你要人,你就放了他,别伤我性命。”
樊威正要放他,忽然又道,“我放了你,恐怕李东家也不会放过你。”
蒋金南惨笑道,“你竟然还替我着想?”
樊威笑道,“好像是的。”
“今天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你造成的?”
“好像不是。”
“是谁?”
樊威已经押着他走近牢车,道:“是他。”
蒋金南自己又不瞎,当然看得出来,这一切决不是白公子安排的,白公子现在在牢车里,动弹不得,他怎么可能安排这么大的劫车场面?
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李府庄园有大队人马进庄抢劫,庄主吩咐快快回兵救庄。
蒋金南喃喃道,“大队人马?又是你们?一定是你们搞的鬼──!”
樊威道,“快放开他,否则,我立即要你的小命。”
蒋金南从裤腰上取出钥匙,递给樊威,樊威是个精明人,不接钥匙,叫道,“你亲自把门打开。”刀在樊威手上,蒋金南不得不打开锁头。
不一会,黑衣鬼脸人全都将蒋金南的人打倒打散。
樊威也扶着白一凡下了马车。
樊威掉转头对蒋金南说道,“你想立功,就赶快回救李东家,否则,李东家一家全被人杀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白一凡跳上马,朝西街方向跑去。
黑衣人呼的一声,全部散开,不一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蒋金南叫道,“快,不要追白一凡了,赶快回救李府庄园。”
众人捡起长枪断弓,一齐跟在大都头蒋金南身后,去救李府庄园。
街上众人,都亲自目睹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大家都说,天兵天将救走了白一凡,也有人说,这是天上十八罗汉下凡间救人来了。
这边蒋金南正朝李东家庄上跑去,那边高峰也正冲到街口。
街上只有打斗的痕迹,刚刚扶起的烧炉,散落一地的苹果、李子,张二的馒头散落在地,乞丐们争抢着,行人们涌回来,纷纷诉说过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有人指着地上的血迹,重述街头混乱打斗场面。
高峰无心听人们的议论,他走近张二,拍拍张二的肩膀,问道:“张二哥,损失多少?”
张二哥抬起头来,见是高峰,苦笑道,“还好,刚抬上来的两笼算是白费了,你要馒头我回去拿给你,这些多半被人抢去了,只捡了这些。”张二哥指指篮筐的馒头苦笑。
张二哥的馒头铺子在后院,他在前街摆摊买馒头,今天刚出摊不久,两笼馒头都被汹涌的人潮掀翻在地,蒸馒头的炉子也倒了,热水洒满地,几块黑炭散落水沟边。
看见雪白的白面馒头散落街上,在地面打滚,张二哥连声惊呼,心痛不已,四下抢捡。
高峰道,“我不是来要馒头的,我想打听一下──!”
张二哥嘘声道,他已经明白高峰问谁,张二哥道,“你没听说吗?天兵天将救他走了,没事的,好人不会有事的,你快点去找他吧。”
高峰道,“谢谢你,他往哪个方向走的?”
张二高低头捡馒头,在地面画了一下,高峰知道白一凡是朝南街方向走的。
高峰帮他捡了两只馒头,“这些都不能吃了──!”说罢,放了一锭银子在张二哥的菜篮子里。
张二哥慌忙道,“小公子,我没有馒头给你,怎能要你的钱?你给这大钱──。”
高峰已经走远,张二哥笑道,“你也是好人,我捡起来的馒头当然不能再买,但整干净沙子,猪是可以吃的。”
一个小乞丐冲上前来,抢了两只馒头,张二哥叫道,“你看你,你又不是猪?”
张二哥骂完,自己也笑了起来。
紫大夫正在门外张望,只见高峰一人前来,急忙问道,“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公子怎么样了?”
高峰道,“我去到时,人早已经散开了,听人说,他已逃脱,谁人去救他?”
紫大夫道,“这就好,他逃脱了,这就好,谁人救他?樊威?不可能,他伤成那个样子,走路都拐拐的,怎么能救人?”
“樊威受伤了?”
“是的,樊威中箭,带伤来通风报信的──十六呢?”
高峰道,“十六不会有事的,我收到消息,就跑出来了,顾不得别人,白一凡是不是回家了?”
紫大夫道,“樊威不笨,怕人跟踪,绝不会带主子回家的。”
“他们会去哪呢?”
紫大夫也摇摇头,想了想又道,“这是主子的地头,他要去哪,别人是找不着的,或者他去那女人屋里──?”
“女人?”
紫大夫想了想又道,“也不可能啊,他若去找她,就会带危险给她。”
“我问你,她谁啊?”
紫大夫道,“她是主子的相好,最近这段日子,主子天天去找她。”
高峰咦的一声,“这家伙什么时候有个相好的了?”
紫大夫道,“我也没见过。”
“人家的相好怎会给你见?你真是啊,我走了,我兄长可要骂我了。”
紫大夫笑道,“还是高公子重情义,一听说我家主子有难,就拼命出来相救,在下多谢公子了。”说完,拱手作揖。
高峰笑道,“这不能用情义来形容了,他的命就是我的命。”
紫大夫点头道,“公子有兄弟如此,真是天意。”
高峰笑道,“什么天意啊?是我大意了,差点出了大事,我走了,替我谢谢十六,今晚奖他只烧鸡吃。”
紫大夫笑道,“好的,我今晚奖他只烧鸡。”
紫大夫送高峰出屋,然后返回屋去,准备樊威的伤药,如果樊威回来,一定要换药,经过这么激烈的打斗,说不定伤口早裂开了。
这时,只见十六喘着气跑回来了。
十六叫道,“主子走脱了。”
紫大夫道,“我知道,谁人救的?”
“是樊威和很多黑衣人救的──你怎么知道的?”
“高峰前脚走,你后脚进来,你说的黑衣人?谁呀?”
“不知道,我赶到街时,那些人都散开了,像黑云一样,呼的全不见了。”
紫清大夫笑道,“有你说得这么神乎?”
“真的,大家都在议论呢,说是天兵天将下来救白公子的。”
紫大夫道,“这是说书讲的,你见到樊威?”
“我见到他的背影,也看见主子上马走了。”
紫大夫点点头,“你很聪明,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十六道,“我帮不上忙,刀是长刀,枪也是长枪,分分钟会要人的性命,我怕死,就不敢走近看。”
紫大夫道,“有空叫公子教你些功夫,将来也能用得上场。”
十六道,“这样最好,我也很想学。”
既然白一凡走脱了,紫大夫也就放心了,两人又说些闲话,厅前有人叫大夫,紫大夫就走出去了。
紫大夫走了两步,忽然转身道:“你今晚去买只大烧鸡回来吃。”
十六笑道,“有喜事啊?”
“高公子说要奖你的。”
十六乐了,“我现在先吃个馒头垫底。”说完,进到厨房,揭开锅,拿个大馒头吃。
从前十六三天两头吃不上饭,紫清大夫见着可怜,这孩子正在长身体,饭量大,容易饿,所以,锅里总是热着馒头,十六想吃,随时拿来吃,不分时候。
内竹商行。
樊威也愁惨了。
樱子问道:“三天来,他没说什么?”
“一句话也没说。”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三天来,一句话也没说,我进去,他当我是透明的,只喝酒,已经喝了三天三夜,已经喝了十八坛酒。”
樱子叹息道,“他变了。”
“是的,他完全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开解他。”
樊威摇摇头,“很难,他是一个倔强的人,很倔强,明白吗?”
樱子道,暗道瞎:“难道我的柔情也融化不了他?”
樱子轻轻推开门,她鼓足勇气走进去。
白一凡端着酒杯,呆了一下,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樱子,樱子身子微微颤抖一下,她从没想到他会这种冰冷而陌生的目光盯着她,就像盯着一个陌生的动物一样。
樱子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她发现白一凡并不欢迎她,于是,又退出门去,轻轻掩上门。
樊威见樱子退了出来,叹息一声道,“你看见了吧?”
“我看见了,他通红的双目注满怒火,但是,他的目光像是注入了冰,很冷。”
樊威道,“他看我时,也是这种目光。”
樱子道,“我不能改变他,只有他能救他自己,只要他才能逃脱心里的窂。”
“心里的窂?”
“是的,他逃脱蒋金南的窂,却逃不脱心里的窂。”
“他心里的窂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被紧紧地困在窂里,他自己走不出来,谁也救不了他。”
“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樱子摇摇头,“不会,他告诉我们要珍惜生命,他本身也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要喝酒,就让他喝个够,他要喝多少,就送给他多少,酒能醉人,也能醒人。”
“喝酒还能醒人?”
“是的,喝醉酒的人头脑最清醒,说不定现在,他的头脑就非常清醒,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
“哦,他只知道喝酒。”樊威并不完全理解樱子的意思,他终有一天会明白的。
樱子笑了笑,或许他现在不仅能喝酒,还能做些什么,只不过白公子不说而已。
樊威道,“我们无法改变他,或者时间能改变他。”
樱子点头同意,道,“是的,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他。”时间能治疗任何创伤,包括人生失败带来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