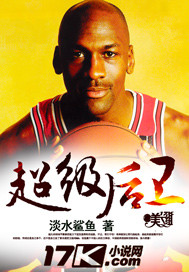不能较真,印宏只好站了起来,躬身给老领导赔不是。敢在老领导面前,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争荣的人,难道是自己?
晚上回到小屋,左思右想,不胜彷徨,对实施计划感到困难颇多,不知从何处下手。他又想起来了那个该死的臭官司,上诉书交了,还没有回音;弄不好,会坐牢的;明明是那个女孩子撞了我,法官偏偏说是我撞了她。天地良心,这到哪里去说理啊?
他走到窗前,望着黑黑的外边,全是森森的树林,障蔽了一切;看不见迤逦的山峰,见不着涓涓的溪流,没有了氤氲的气息,茫然一片,不知就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缝补千佛山这个褴褛衣钵,真比登天还难啊。此刻,整个综合经济体的运行重担,都压在他一个毛头小伙子身上;梦幻难以确定,憧憬难以触及,幸福何以实现,谁能帮自己?如果没有那个该死的臭官司,也许他可以轻身上阵,坦然相搏,没有恐惧。然而,现实冷峻,让他在激愤中失却热情,在思考中丧失能力,在奋进中遭到阻击。万能的上帝啊,我诚何幸福,我又何辜负?
他内心疾呼。
这时,范梅梅轻声推开房门,蹑手蹑脚地来到他的身后,拦腰一抱,猝不及防——是先生犯鬼,还是鬼犯先生——这着实把印宏吓了一大吓,内心怦怦直跳。
“你这干嘛呀?”他责怪道,风快地挣脱。“深更半夜也不睡觉,神经似地跑到我这里,调弄鲁男子,成什么话儿。”
“嗬,美得你了。”范梅梅笑态可掬:“还自称闭门不纳的鲁男子,有那么魁伟,那么英俊,那么高尚吗?”
印宏说:“我当然英俊呀,当然高尚呀。”
范梅梅嗔怪道:“你高尚个鬼,总不来找我,让我来找你,翘什么皮?”
在灯光下,她那娇滴滴的苹果脸儿,显得格外圆韵,格外动感,格外光滑。她挨得很近,娇润,扭捏,就要相贴啦;香喷喷的樱桃小口儿,微微张开,些许上翘,诱惑地朝向他的嘴儿,伸过来了,就要相腆啦。印宏觉得有一股扑鼻的芳香迎面泼来,沐浴全身,好味道啊;不禁心中升腾起春春的欲望,久久迷荡,无法抗之,无法拒矣。
印宏有些吃惊。范梅梅原来不是这样娇柔的呀。过去的范梅梅,哪有这般妩媚,这么诱惑,大方得出奇?怎么突然之间,她会成为半夜弄粉、三更放荡的迷人鬼啦?印宏只好揽住她的腰身往后推移,拉开距离,避免贴近,好让自己压抑的性欲得到减免,狂跳的心脏得到安宁,不安的情绪得到转移。
然而,范梅梅倔强地扭动身体,紧紧地,镶嵌地挨近了他,用双臂向上地勾住他的颈脖,圆圆笑脸仰望地将嘴儿噘了起来,冲动劲儿串上来,有股无名的魅力,任何美男子还真的难以抵御。
印宏勉强贴了贴她的嘴唇,不知是甘是甜还是辛……地位变了,女朋友也会变,印宏瞬间悟出来了这条真谛。
常无理能够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令小腊不可思议。这个纨绔子弟,平日里浮夸虚掷,蛤蟆一般蹦迪,荡涤几个铜板,还以为买下了天上人间,胆大妄为而又无所顾忌。他可以肆意糟蹋宫殿,刻意左右生意,将那万贯家产,耍尽了根须,所剩无几;到头来,怎么样?居然腾腾地绝处逢生,异地升辉,跑到大型国有企业里面来了,摇身一变,捞油水竟然捞到小腊头上,堂堂正正,威风凛凛。这个常无理在外边混惯了码头,回来一出手,瞬间成为大神一般的操盘手,让里面的人大跌眼镜,也让陈奇奇、崔凯之流捧之不及。
小腊啊,你何苦梦寒灯屋,怀昼雨楼,没精打采,伤心不已?
欧阳修怎么突然离职了呢?这完全出乎小腊的意外,太蛊惑人心了。猛一听见,还以为有人故作玄虚,弄一场“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无为”的活报剧,逗逗乐子,发泄情绪。假如真的如此了,那还了得,简直天塌地陷,地球终了。到那时,自己与印宏的事情,欧阳修说话还算不算数?
这是她的心病。
她躺在家里的床上,将绣锦被子放在床头,自己靠上去,盖上鸭绒毛毯,一种柔软而舒适的感觉出来了。她早就想成一个家,梦寐以求,实不为过。她相中的小伙子就是印宏,曾跟欧阳修提了几次,欧阳修也答应了,就是还没成。她早就看出来了欧阳修对印宏不一般地器重和栽培。如果不是冯晓春、蒋存村之流的阻碍,印宏早就上去了,自己的愿望也就顺理成章。但是,能怪冯晓春狡诈无情和蒋存村肆意打压吗?不能。谁愿意昔日的奴才,摇身变成自己顶头的上司,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要伺候一辈子?要怪就怪那个范梅梅,狐媚地活在当下,将印宏捕获,抢占了先机。不能说范梅梅用了什么奇技怪术,很多事情都是自然天成,人为因素在其次。天然去雕饰,无意胜有意,这姻缘啊,最忌讳刻意。自己再怎么追求,也耐不住范梅梅在印宏身边不住地磨蹭,千佛山上一日三呵护,尽情,又尽意。
看样子,得把印宏调离千佛山,安排在自己身边,实为上策。
小腊为自己制定了行动方案,感觉好起来,一个翻身下床,到客厅找东西吃。
刘艳在看电视,见女儿出来,就问道:“咋睡不着?”
小腊说:“我在考虑青湖省的GDP增长率,怎么排名在全国倒数第十名,忙得很,睡不着。”
刘艳说:“我当然信啦,不信宝贝女儿的,信谁呀?不过呀,很多事情由不得你主观努力,客观使然。我劝你还是物归原主,干好本职工作,不要好高骛远。”
“妈,谁好高骛远啦?”小腊撅嘴生气道:“你那张嘴就是不饶人,挖苦人来像刀子锋利,不想我好啦?”
“我怎么不想你好?当然希望你好哇。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常无理管好,别让他在外边糊搞。现在,他正统了,地位高了,追她的女孩子肯定多,一不小心,他跑了,看你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他地位高了?”
“我能不知道这点儿事情?就连你们的欧阳修被离职了,我都知道,你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你是不是以为我就会牌桌上赢天下,整天蹦嗒嗒?告诉你吧,棋盘虽小,维系却大。你不能小看了我们这些年纪大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不要跟上了年纪的人较劲。——这话儿,有一定道理。”
“妈,我哪有心情跟你较劲啊?”小腊被触动了,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是认为你太邋遢,太不注意形象,衣服瞎穿,大红大紫,太显眼,像一个妖精:腰身苗条健康,脸上布满尴尬。”
“哈,”刘艳笑了起来,“你这是在损我呢,还是在表扬我呢?”
“我在损你呢,”小腊说,“如果你平时吃好一点,营养一点,也不会如今这么尴尬。”
“我以为你在表扬我呢。”刘艳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沙发前,躬身拿起一件大红的彩巾,披在肩上,嘴上嘟噜上了《手心里的温柔》,迈开小步,翩翩起舞:
你在我身边把我的手牵,
牵着我手心不变的誓言;
高高的雪山祝福我们,
爱在这一刻永恒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