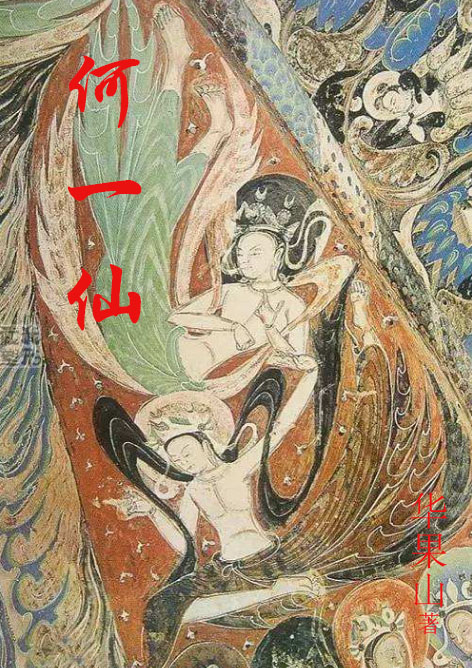秋日明媚,万里无云。
临近晌午。
郝家村。
遇难的村民遗体有十几具,郝财带领勉强能动的人把尸身摆在一起,然后堆起柴,准备火化。
郝瑟受了重伤,本就结巴的嘴更加磕巴,浑身裹满了布,躺草席上喃喃半天,愣是没能说出一句话。
木屋中,周积素利落的身影在伤者之间穿梭,吴佳友虽说医术不高,也没有特地教过,倒是她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而然会了些简单的伤口处理。
此时她蹲下试图给一人包扎,这人浑身是血,伤的很重。
“别碰我。”
他拨开姑娘的手,气若游丝,周积素仔细看看,发现他正是昨夜拿长叉意图偷袭的郝三弟。
郝三弟的亲大哥最先身死,而他化悲愤为力量,拼死逼退了好几名土匪,还叉穿了一个人的头,此时却因伤势过重,奄奄一息。
他哥俩本想靠着这对男女,解村子一时之难,没想到草屋内不知发生什么,激怒了张老二,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恨从心头起,根本不想再看见她一眼。
“我来吧。”
郝财从屋门进来,接过她手中的布条蹲在他面前。
村子空地上,木柴堆已经熊熊燃烧起来,在阳光下有些分不清颜色。
郝三弟回光返照似得,紧紧抓住他的手腕,盯着他的双眼,艰难的说。
“郝……财,不,郝薪桥,你……顾着发善心,可曾……想到过村内这种局面?你奶奶的……”
话刚说到一半,嘴都没合上,他的眼神就已经灰暗下去,瘫软倒地,没了声息。
“……”
郝财,应该说郝薪桥,眼神落寞,默默地把他放平躺好,闭上眼呆了半晌。
“你……”
虽说在医馆见过不少生离死别,但眼下亲身经历,周积素却有点不知该如何安慰,张了张口,没继续说下去。
郝薪桥有些无力,在地上闭目坐了一会,遂又睁开看向她。
“姑娘,你可知我这本名,是怎么来的?”
后者自然不知,摇了摇头。
他苦笑一声低下头,看不出是在笑些什么。
“众人齐抱薪,搭桥渡苦海。廖阿婆给我起名薪桥,而我,却当不起这名字。”
说到一半,他又看向清秀姑娘。
“眼下这局面不能怪你,也不能怪那瘦小子,趁张双寒没反悔,赶快走罢,能走一个是一个。”
哪成想他下起了逐客令,姑娘没有多加思索,又摇了摇脑袋说道。
“七日后那个张什么是冲我而来,既已掺和其中,我自然不能说走就走。倒是你们不必再停留此地,带着村民去别的乡镇找个活计,如何?”
听到她这话,郝薪桥有些振奋,不过很快又泄了气。
“如今我们只剩下些伤者妇孺,就算跑了,不出几天便会被张双寒的快马追上,那时候,就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姑娘自知思虑不周,陈土不在,她又不谙世事,一时也是没什么法子可想。
停滞的气氛很快被吵闹的马蹄声打破。
纷乱的马蹄声,有点像上午的来人,难道那群土匪,竟然去而复返?!
郝薪桥赶紧靠近窗边,偷偷张望,周积素也扒着门缝瞧去。
来人须发尽白,穿着捕快的官服,骑着黑鬃骏马,他身后是数位打扮与他相似,同样纵马驰骋的捕快。
身形一致,眼光锐利。
哪来的官差?
郝薪桥纳闷地嘟囔一句,这郝家村地处偏远,剿匪都是百年难得一回,怎么这会儿来了几位官爷。
而且为首的白须老人,越看越眼熟。
“咦?这人不是昨天的廖老伯吗?”
周积素坐着他的驴车一路搭话,对他样貌熟悉地很,一眼就认了出来。
来人停住马,眼前的景象,如果说昨天来时只是有些破落,那今天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地上,墙上,到处都是大片还没干涸的血迹,围篱和木屋破了许多窟窿,村子空地上还有一个正在燃烧的火堆,里面依稀可见人的遗骸。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村内还有没有人?!”
廖老伯下马跑进村子,语气急切。
“郝财,郝兄弟在吗?周小姑娘?陈小兄弟?!!”
正当他以为村内没有活人的时候,一扇屋门吱呀呀打开,满头都是土和草棍的周积素走了出来,身后跟着浑身沾满血来不及清理的郝薪桥。
“你们这是……?”
仅仅一夜,村内竟然就变成了这样,看两人的模样,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激烈的厮杀。
事实也正如他所想那样。
这老伯全然没有了昨天那乐呵呵农民小老头的模样,官服加身,须发尽白,腰配宝剑,隐隐有股无形之势。
郝薪桥按耐不住,率先发问。
“……廖老伯?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老人一时无言。
“廖伯是我们衙门第一捕头。”
另一位捕快打扮的人下马走到廖老伯身边说到,竟是一英气女子。
“哪个衙门?”
郝薪桥有点诧异,旧京根本没有衙门会管这档子事,而且廖婆婆在世时,也从没听她提起过。
“西棟洲总衙门。”
英气女子继续说。
西棟洲,是毗邻旧京西侧的一大块地界,而郝家村,正好夹在这两地中间,只是这里山峦迭起,从来没人管过。
廖老伯示意女子停下,亲自开口说。
“老夫姓廖,名赴川。郝小兄弟,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郝薪桥立马拱了拱手,言到。
“小民本名郝薪桥。”
然后把上午发生的事尽数说了个遍。
“……竟是如此,可恨老夫迟来一步!”
廖赴川握紧拳头空挥几下,语气忿忿又有些无力。
“陈小兄弟以身犯险,实在是侠义之人,我们如何解围?”
如果贸然出手杀匪,陈土肯定紧随其后就被其祭天。
“入夜后,我们偷偷潜入,把他救回来?”
周积素思索片刻,出了个主意。
“此法可行,不过……老夫还有事要问。”
廖赴川说着话,眼神一变,看向郝薪桥。
“陈土的命,当真要留?你我与他不过一面之缘,如此费尽人力,值吗?”
此话问出,众人皆面生难色。
在场的人,除了周积素,说跟这瘦小子有多大情分,自谈不上,而廖赴川所行所为定要征得郝家村的同意。
郝家村现在,就只有郝薪桥一个主心骨。
“……”
郝薪桥迟疑了。
一边是当朝捕快,实力高深难测,只要他率领一众高手杀上去,不出几个时辰,定能给死去的村民报仇雪恨。
一边是黑黑瘦瘦,说话摸不清路数的独眼小子,如今落入敌手,生死不明。
“弃下一人,则能保众村民平安,郝薪桥,你考虑如何?”
廖老伯与慈祥的影响已经相差甚远,言语间充满危险的诱导。
正当纠结之时,屋内的郝瑟被人误踩了一脚,痛呼出声。
这声惊呼,把郝薪桥的思绪立刻拉了回来。
那瘦小子在危难关头,是为了救村子才被抓走,如果真这般断义决绝,以后定会良心难安。
最终抬起头,正视着廖赴川的双眼。
“不能舍,要救,我自会去救!”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
廖老伯得到答复,满意地捋了捋胡须,这才笑道。
“呵呵,心境颇高,是个好苗子。此事尘埃落定后,与我回西棟洲如何?”
周积素也松了口气,她刚才真有点看不懂这老伯,现在才发觉他原来在试探郝薪桥的决心。
“大仇得报后,小民愿追随大人左右!”
郝薪桥恭敬拱手。
“好、好、好。”
廖赴川连道三声,然后向他的手下招了招手。
“拿药救人。”
众捕快各有所长,医术自不在话下,从马背上取下药品后便进了屋。
几人也找凳子坐下,廖赴川仔细检查了郝薪桥身上伤口,所幸并无大碍,于是捋着胡子开口。
“先把那匪寨详情细细道来,最好不要有半点遗漏。”
后者听闻点了点头,说道。
“此匪窝名为金箔寨,有两百来号人,今日带头的是寨子二当家,我们称呼为张爷,原名张双寒,听说以前是在军中当差,善骑马,耍弯刀,训练手下也有军中那一套。”
他说着话,英气女子拿了些绷带过来,站在一旁静听。
“但他只是二当家,上面还有个大哥,穿着打扮像个和尚,不知道叫什么,也未曾听他说过话,张双寒对他十分敬畏。”
郝薪桥说得有点口干舌燥,一直不住得咽唾沫。
“大概……两年前,他们兄弟二人为躲避官兵逃窜至此,打死了金箔寨的原当家,取而代之,我们村子也是那之后不久,便拜入他们寨下。”
之后事无巨细,悉数讲了出来。
廖赴川听完若有所思,站起身负手来回踱步想了片刻,沉言道。
“两年前……嗯…我倒是有所耳闻,那次旧京的老王爷派兵剿匪,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喽啰打死不少,两个头目却都逃脱了出去。”
说着不免有些惊疑,究竟是怎样的奇人,才能金蝉脱壳,逃离那张包围网。
“不管如何,今夜去探上一探,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