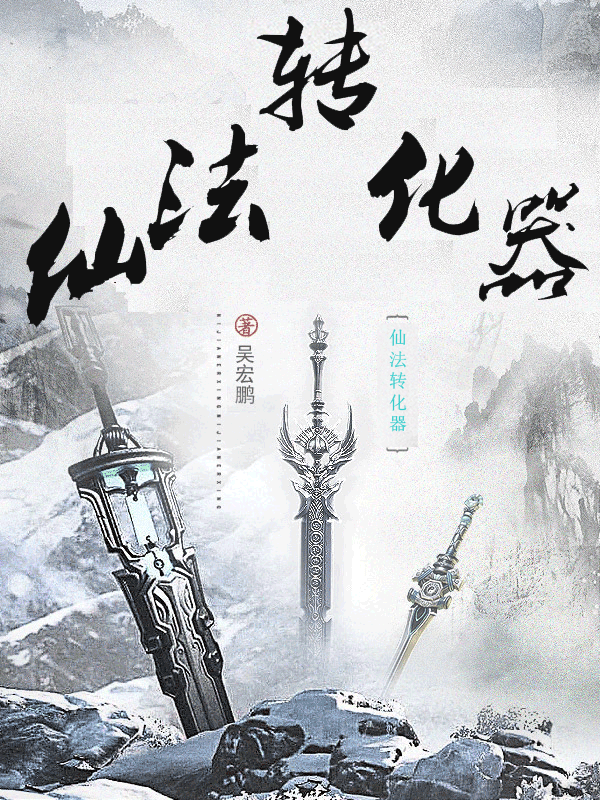遮了半边月亮的云彩缓缓的飘远了,冰凉的月光又悉数洒向昏暗的树林,一片苍白。
一男一女两个身形静立在婆娑的枯枝下,他们的影子与那树的影子缠绕在一起,细分不出彼此。
“我们就一直在这等着,不用去找他们吗?十一真的不会有危险吗?”
絮濡沫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看着身边的男子如苍松般一动不动的背负双手盎然挺立,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她忍不住打破了两人许久的沉默。
“此番十一弟执意要随本王来宁州,任何人都知道凶险莫名,虽然本王不会害他,但是他的母妃文贵妃,又怎么可能放心将她宝贝儿子的生命安全全部置于本王手中,从最开始十一弟单独进城起,再到你们去报名竞仙大赛,都是有文贵妃的人保护在侧,就连上一次长街暗杀,就算你不出手,他们也不会让十一弟丧命。”
絮濡沫恍然,随后嘲讽道:“原来是这样,看来我这为朋友两肋插刀插的有些多余啊。”
男子好笑的瞟了她一眼,片刻后转开目光,“此去京都,你有何打算?”
絮濡沫摊了摊手,无奈一笑,“我下山不就为了那么一件事,还能干什么?”
他思索了片刻,淡声道:“你的身份,十一弟并不知道,但这不代表他身后的隐卫不知道,就算现在不知道,以后肯定也是会得知的,本王本不欲与你同行,但十一弟放不下受伤的你,而且也不排除你娘有在京都的可能,所以到了京都,你万事小心些。”
絮濡沫望着他诚挚的表情,张了张口,想告诉他她并不是真的安羽,可是又想他就算知道了又有何改变?他以为她是安羽却一直都没想过伤害她,而京城那些,就算她说她不是,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她。说与不说,在他面前,毫无差别。
再说了,才认识几天,你今天说你是这个人,没过几天又说你是另外一个人,反复无常的,保不准人家还以为你是因为贪生怕死所以这个时候又想要隐姓埋名。
“到了京都,你最好是隐姓埋名,换个身份。”
嘿,絮濡沫在心里笑了,刚才若是自己说出来,估计他还真就以为自己是贪生怕死吧。
她心里有点别扭,这个本来就不是她的身份,却越说越乱。
尘拜无霁回头看了她一眼,看到她的别扭苦恼,有些好笑的道:“又不是换个名字就不是你这个人了,有什么可别扭的?”
絮濡沫无力的一声长叹,无语问青天,“叫我濡沫吧。”
“濡沫?”男子挑了挑有如刀裁的剑眉,盯着她的眼睛。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絮濡沫转头,对上他的眼睛,从彼此的眼中可以看到,两人的眼睛在此时何其相似。
眉头似蹙非蹙,眸中如墨黑,如渊深,天然一段韵致全在眉梢,世间万种风情悉堆眼角,带了淡淡的渴望却疏离,探究却忍住。
两人此时却都没想到今日的一言,却在不久的将来,一语成谶。
不如相忘,于江湖。
彼时,男子于马上一夜狂奔,却不得女子身影,收缰勒马,衣衫在风中滚滚翻飞,猎猎作响,望着曾与女子一同游览过的熟悉山景,现下再看却是仿若失了所有的颜色生机,苍凉而荒芜,终是落下生平第一滴男儿泪,灼痛了她一双如玉纤手几度拂过的惊世艳容。
此时,絮濡沫败下阵来,率先转开了眼,面对着这样一张妖艳绝对气质风流的俊脸,她不知为何总是缺少一贯的抵抗力,直怕自己再看下去真的会忍不住跑上前去亲两口。
尘拜无霁一笑,“相忘于江湖,听起来多么无奈。”
絮濡沫却摇了摇头,目光悠远而忧伤,“相濡以沫,令人感动;相忘于江湖则是一种境界,需要有坦荡、淡泊的心境,学着看淡,学着不强求,学着深藏,把感情深深埋藏,藏到岁月的烟尘企及不到的地方。”
是絮非泽对白玛的感情。
尘拜无霁背负着双手,如韧竹般挺立风中,微仰着头,唇角是一抹若有所思的笑意,她这样伤感,说的是白玛吧。
对于两个不太熟悉的男女来说,在这样既不是良辰也不是美景的环境下,讨论相濡以沫对于他来说终究有些陌生,他没有接过话题,仔细打量了下眼前的破庙,他轻声道,“进去看看,敢吗?”
也不等她的回答,便迈步小心的靠近,絮濡沫皱眉,“有什么不敢!”
尘拜无霁听了她有些赌气的语气,稍稍停了下脚步,只是一瞬便又继续靠向庙门,停在庙门口了,眼望庙里的漆黑一片,只有破旧的屋顶挤进几缕月光,勉强能看清里边的轮廓,看了一会才淡声道:“既然不怕还等什么!”
絮濡沫极不情愿的噢了一声,缓缓挪着脚步,一双漆黑的大眼看着他极优雅的拂了下长袖,将那门口的浮灰和破旧的蛛网震开许远,退后了一步待那尘埃落定后,他才又迈步走了进去。
絮濡沫跟在他身后,突然好奇的问道:“你不是五王爷吗?为何你的属下都喊你五爷呢?”
尘拜无霁一向淡漠清冽的声音这次竟有些铿锵之音, “成王败寇,既未成,何称王?”
絮濡沫嘟着嘴不以为意的又问:“那你还整天本王本王的喊的起劲。”
男子一直缓缓向前探索的身子停了下来,转过身,在黑暗里看向她,她不知道他是否看得清自己,至少她是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的到他一双晶亮的眼睛闪着比这屋里更黑的墨色深邃,他的声音就像是浮尘一般低弥,“尘国律,皇子十六封王,封后必自称,彰显尊贵。”
“那也不用在每个人面前都这样吧,眼药就从不在我面前这样讲话,朋友之间这样子不是会很有隔阂的吗?”
他眼中的晶亮稍黯,语带回忆的道:“习惯了,本王如此自称已经九年,转眼就要十年了。”话音一转,望着她,眸中闪着莫名的精光,“或许以后,会有一个人,让本王再习惯免去自称。”
絮濡沫四下里观望着,慢慢摸索着向前,也就没注意到他意味深长的目光,她了解一个人十年来的朝夕习惯很难改变,也就没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存了一份芥蒂,“你当年为什么拒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