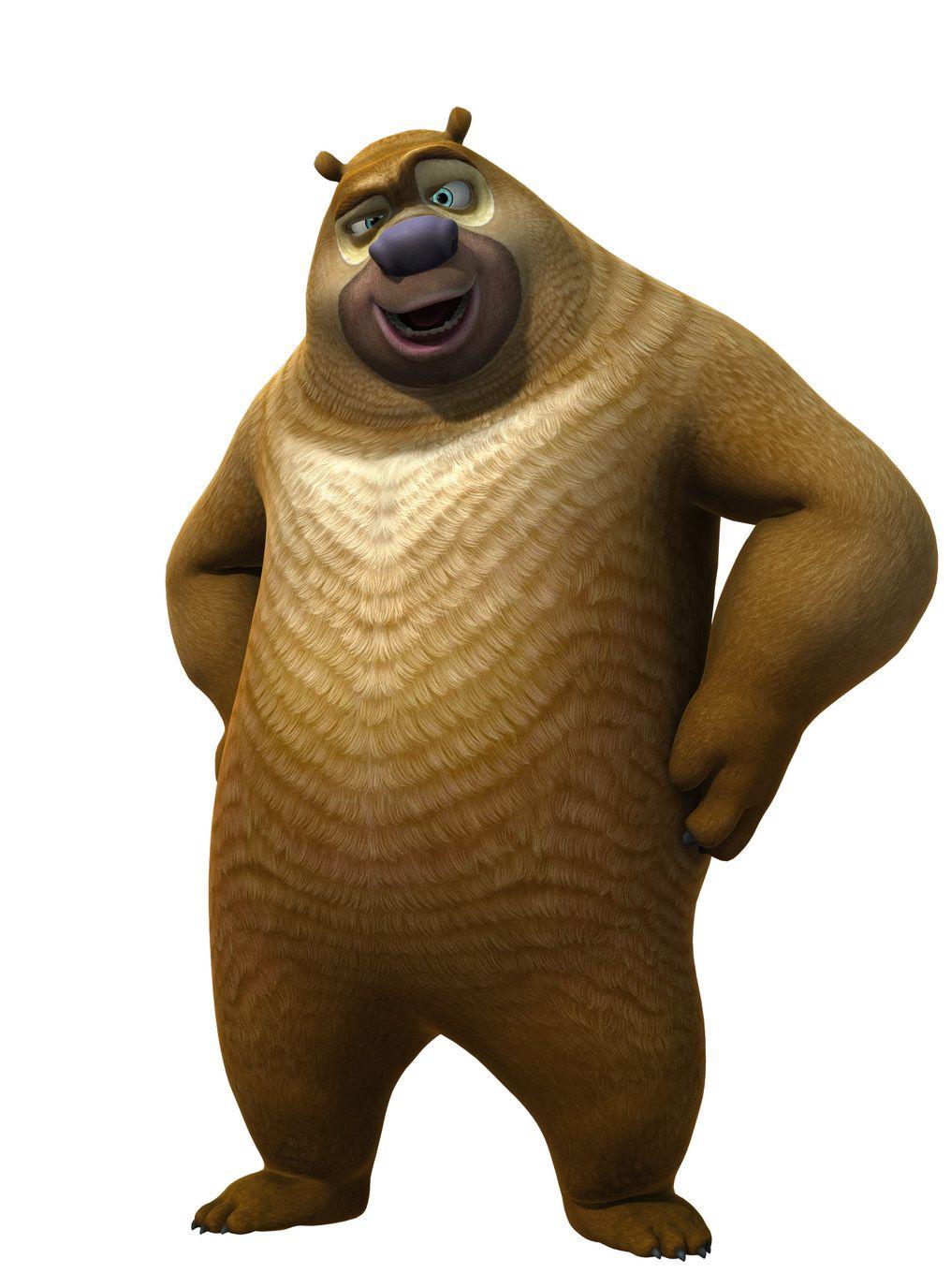腾云回到昆仑山脚,爬山爬到半山腰时已是夜幕低垂。
此时一轮皓月当空,在爬最后一段阶梯时我一直抬头仰望着它。它看起来那么近,清而亮,像一枚圆润莹白的玉团浸在透明的夜色中。我伸出手欲感受它的温度,然每迈上一级石阶它便也跟着升高一级,永远与我隔开一段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
就这么自娱自乐地爬到了山间平地,我一眼便望见润朗的月辉下沐着一个人。
他斜躺在昔日我们总是一同沏茶论道的木案上,一手支着自己的太阳穴,一手拿着细口的青玉酒壶时不时仰脸往嘴里灌上一两口,双眼始终凝视着遥远的夜空,看上去像是已出神良久了。
……瞿墨不是声称自己从不喝酒的吗?那他现在又是在做什么?
突然想起以前玄漓给我讲的关于瞿墨的一则八卦。他说瞿墨不喝酒是因为酒量实在不行,而且酒品也算不上好,一点不像他。
当然我始终不明白他哪儿来的自信说这种话,况且就算他说的是真的那也应该承认这是遗传问题。
我朝对月自饮的瞿墨走去,未料脚下一滑,一个没站稳差点儿就要摔一跤。低头一看,发现原是他随身携带的那支玉箫,此时正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华。
“师傅,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雅兴了,还边赏月边喝酒呢。”我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箫,继而走到瞿墨身前站定。
他斜睨向我,就像在看一道虚无的影子。虽然他身上的酒气挺浓的,但就目前状况看来确然还是平时的那个瞿墨,并未像玄漓所说的那般因大量饮酒而失态。
“师傅?”我俯下身,又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我,在等。”他依旧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边,不过话一出口我竟觉得自己骨头都要酥了——他、他的声音……何时变得如此低柔婉转了?
“……等什么?”
他饮下酒后长舒一口气,接着放下酒壶向我伸出手,脸部轮廓在银光的晕染下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柔和。“坐过来,陪我一起等。”
“……”
我凝神端详了一番此刻的瞿墨,可到底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是顺着他的意狐疑地坐到了木案上。
“师傅,到底是要等什——”正当视线在空中左右游移之际,我蓦地感到腰间一紧!
瞿墨双手攀着我的腰稍微扭了一下身子,接着竟自顾自地又把脑袋搁在了我腿上,双目微合,神情很快陷入一派安详……
“喂……师傅,能不能不要总是把我当成你的抱枕?”见状我简直欲哭无泪,而更为惊悚的是,就在下一刻瞿墨就搂着我的腰分外亲昵地来回蹭了蹭。“最喜欢你了。”轻软的嗓音挠得我打心底都发起痒来……
啊,我想我突然明白了:
他眼下的的确确……是醉了。
“来,”躺在腿上的瞿墨一刻不安分,忽又抓起一旁的酒壶往我怀里塞,“你也喝一杯。”
“呃、谢谢你,我不喝。”身边有个喝酒喝得连人格都碎了的家伙,这要我怎么还下得去口。
“很好喝的,尝尝。”他坚持道。
“不用了。”
“就喝一口。”
“不要,你也别喝了吧。”
“喝嘛……”
“不想喝。”
正当我以为这无意义的推搡要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瞿墨这家伙居然还生气了,我一时不察被他使劲一扑腾给一把扑倒在了木案之上——
“干什么啊师傅!以为喝了酒再耍流氓就不犯法了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胡搅蛮缠我真要被他搞得神经衰弱了!
……然而,他并没有像往日那般得寸进尺,撑在我身上始终与我保持着一段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距离,吐息间溢出的浓醇酒气徐徐喷在脸上,登时为这段明明可以算得上是安全的距离平添了几分暧昧。
我的目光透过氤氲的酒气从他朦胧的双眼一路下移,停在他被烈酒润成一派妖异之色的唇上,期待他能为眼下这莫名其妙的状况说点什么,可是……
“你这个逆徒!”
“……啊、啊?”我懵了。
“你这个逆徒!”瞿墨再一次重重地重复道,连带着腾出一只手揪住了我左边的脸颊。
“啊痛痛痛!”
我当即抓住他的手拼命向旁边扯,可也不知这家伙喝醉了哪儿还来这么大的劲,手指就像是螃蟹的钳子狠狠夹住我脸上的肉怎么拖也拖不开,而且我越是掰它它夹得还越紧。
“师傅,我……我只是不肯喝酒……怎么就惹到你了!”被他揪着脸颊不放,我是拼命咬着牙才把这番话吐字清晰地说出来的。
可未料我话一出口瞿墨眼中竟蓦地就升起一阵若有若无的水汽,在月光下隐约折射出一层薄光。
我吓得当即闭了嘴。
怎么?此刻他被酒生生泡就的一颗玲珑玻璃心一不小心就被我稍重的语气给震碎了?
感觉到颊边的力道在一点点流失,即便我是真的很无语还是尽量抖着嗓子问了他一句:
“师、师傅,你现在……不会是在哭吧?”
——请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拜托!
“逆徒,”然而我分明还是听到了他话里掺杂着的鼻音,“为师当爹又当娘地一点点把你拉扯大……”
“喂!你是擅自把自己代入了什么样的角色啊?”
“……精心料理你的吃喝,倾尽全力传授你法术,亲自教你待人接物的道理——”
“由你亲自教做人那还了得……”
“可你呢?!”
“我、我怎么了师傅?”他能不能不要这样一惊一乍地折腾我?
“你一夕之间就把为师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做出那等、那等……你真是伤透了为师的心!”瞿墨言罢一下趴倒在我怀里掩住自己的脸,双肩一个劲儿地上下直颤……
这、这真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瞿墨吗?他喝醉了原来会变得这么恐怖?……还是说,他是真的很在意我和无弦的事?
“师傅,你没事吧?”我正想伸出手去拍一拍瞿墨的背,孰料他蓦地就从我身上重新撑了起来。
“既然做过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他怔怔出神地呢喃。
“师傅?”
“那今日,就由为师带着你,”他一脸释然地笑了,“同归于尽好了。”
“什、哇啊!”
猛地听到这彻底丧失理智的话,还未及我作出任何反应,瞿墨不由分说地就紧紧抱住我往旁边一滚,我们径直沿着斜坡抱成团状一路滚了下去,而在这斜坡的尽头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我不由眼含热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
滚至半道儿,一片横亘的泥洼地忽然感人至深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它极大地缓冲了我们从上面自由滚落的速度,在接近那突出的崖口时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