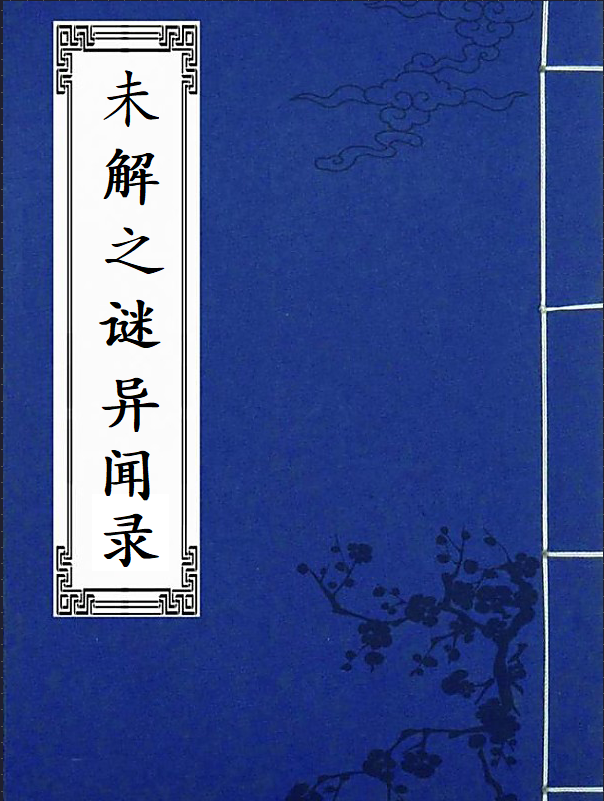新厂,沈恩衣住得惯,吃得惯,行得也惯。
只是,她不再放床头一个闹钟,不再放工台一架收音机。
她吃饭,用大碗,那碗大得很夸张,可以装下三碗米饭。
她喝汤,咕噜噜的,一饮到底,一口而尽。
沒事时,她喜欢去站老板办公室门口出来后转角楼梯空旷的站台,只因那里有块全墙透明的玻璃。
夜晚,那里有星有月,还有街道,行人,路灯。
白天,她有空也去那站。
几分钟,半小时。
像抽烟的人探风一样。
全墙透明的玻璃就那么神奇。
你看它,只要你看,那里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无。
特别是白天,她心中会有一个很大的想法。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为什么退一步?她迷惑,自己可沒什么仇人。
去找工作时,她在招工处认识一个叫邓小飞的人。
邓小飞说,以前他是兵哥哥,刚入伍时,英姿颯爽,年纪轻轻就已经得了班长的高位。
他的女友更是大家闺秀,父亲是军人,母亲开商场,人民路,中和路,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三四百平方米上下两层的开时装。
他小时候,家里就有保姆,日子过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这一切,却因为家里的生意,他把父母的一个同行打了,像杀猪宰羊那样挑了对方的手和脚筋。
那人后来命保住了,可落得终身残疾。
家里因此赔了许多钱,破产,他也从高高在上的公子哥一下沦为万人唾弃的阶下囚。
冰冷的手铐扣着他,沉重的脚链拴着他,女友分手,家人分离,人格破裂,纯粹是一下子的事。
人只有穷了,你才知道,哪个真真正正对你好。那些锦上添花的人,早早消失不见,雪中送炭的呢?还迟迟没有到来。
“事后,我真的很后悔,因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就冲动的把自己的前程,后路,白白葬送,且一分不留全部搭了进去。
我几乎判了无期徒刑。
沈恩衣,之所以现在我能站在这儿,你能看得到我,也是万分缘份,因为我在改造期间,认错态度好,表现佳,连连减刑,到前年,他们就提前把我放了出来,刚开始,他们规定我只能在家附近多少米活动。
后来慢慢的,我沒出错,渐渐获得了自由,再后来,我表现佳,因而解了足禁!我现在沒有梦,只想好好的活着,活着就是梦。
在这个城市,我做的这份工作,无奈,自由。”
沈恩衣说:“给人介绍工作,一人50块钱?”
邓小飞说:“成了以后才有,不成的话,我拿不到钱。你千万别小看这一人50块,这个月,前十五天,我就做了一百多个,虽然真正去的沒有那么多,但也不会少于三四十。我这里都有很明细的登记。四十乖以五十,两千了,只是这工作,地方经常换,且不管吃住,还晒太阳。”
沈恩衣捂着嘴巴咯咯地笑:“小飞,你看我这样,能做和你一样的工作吗?”
“能啊,怎不能。”邓小飞说完,工也不招了,牌子一收,直接带了沈恩衣就去公司。
公司很小,要求也不大。
但沈恩衣最后不做。
因为蓝心诺打了电话给她。
蓝心诺说:“招工有什么前途,每天风吹,日晒,雨淋!我们有手有脚有技术,这活我们不干!人在外面跑,总有不安全!你一个女生,在外面吃,外面住,想想都难!”
邓小飞于是请沈恩衣吃面,恩衣说:“别客气,还是我请你吧,你们工资难接,反正我身上也还有钱。”
邓小飞笑,说:“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穷?”
沈恩衣听了,哑然失笑。
“不是,都不是。只是我想请你!”
邓小飞说:“我明白你的心思,你自强,独立,包括这次,以及许多次出来,也都是希望自己能工作,安定,证明自己能行。”
沈恩衣站在满墙玻璃窗前,海阔天空看世界。
难道是——你退一步是一步,我退一步是无路,等你退到无路,就会明白我的领悟?
蓝心诺耳朵上戴的梅花钉是金的,脖子上戴的桃心坠也是金,手上戴的凤尾戒也是。
厂里面结了婚的人,不管贫困,富贵,都有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
有时出街,怕抢,心诺也脫了凤尾戒,金耳环,金项链的。
2组师傅的老婆,买了一个手镯,带在手上,上班时手镯敲着机台,吭吭筐筐。
“她也不怕摔,不怕碰。”心诺说:“薰衣,你也有,怎么不带?手镯那东西,跟玉一样,都是能消灾避邪的。”
沈恩衣搜肠刮肚,因为林以辰确实没送过她什么首饰,除了那颗结婚戒,两人也都是吵来吵去才得,换句话,她没有!她心慌说:“我刚来时也戴了,干活不习惯,套着手的感觉,也很难受。”
关于手镯,沈恩衣自己给自己买过一个。
箫川舅舅的小儿子玩玩玩,追着跑着,一不小心,镯子碎了。
“现在好了,碎了?”箫川舅舅怒骂!
“沒事,很便宜的货。”她嘴上讲着,心却很疼,但手呢,也开心了,从今往后得自由。
萧川舅妈有一手镯,沈恩衣带宝宝去她家时,那天正下雨,那路正泥泞。也那时,萧川舅舅和萧川舅妈,两人正离婚!
沈恩衣她们穿的鞋,到家早已沾满了泥巴。
沈恩衣安顿好孩子们睡时,听见萧川舅妈在那拍拍拍。
“啊呀!”萧川舅妈大惊!
“怎么了?”沈恩衣慌道!
“我见你们的鞋有泥巴,想拍干净,结果手镯碎了。”
沈恩衣去看时,萧川舅妈正拿手电筒去花园那里找。
“唉呀,不知道找回来还安不安得上。”
“翠玉嘛,安不上去了。”
“好,好,安不上去,你别跟你舅舅讲,那么多钱买来,等会他怪。”
“到底买了多少钱?”沈恩衣问!
“我们去云南旅游时一起买的,八千。”
沈恩衣听了心痛极了。
这就是翠玉,一不小心,八千也就沒了。
“我婆婆想给我一个,我不要。”沈恩衣说。
“为何不要?”心诺问,她给恩衣一个不要白不要的眼神儿。
“那是我老公的奶奶,生前戴,五六十年代,我婆婆在深圳打工,八百块钱给我老公的奶奶买的。”
“五六十年代,八百块已经很值钱了,到现在更值。”
“后来奶奶去世,手镯跟她一起,埋了三年,三年后才从坟墓里挖了出来,别说戴,我看着都怕。”
离别,也就不能再讲首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