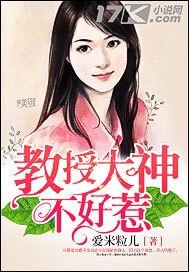数日后得到消息,这金锦夫人的娘家本是浙东一带的商贾望族,原本姻亲兴旺,资产累巨,富甲一方。
但因受周宗建案的牵累,不但本家被抄没,连带得族人也都尽破,人财皆亡,流离道路,惨不可言。
金锦夫人初时也曾归家,但不过十余日便被官府中魏忠贤的走狗爪牙驱逐,被迫离开家乡,如今杳无音讯可查。
林猛听罢黯然摇头,道:“怎地凶狠?竟不肯让人活吗?”
童牛儿从前在御林军里时干尽类似勾当,最知道底细。冷笑一声,道:“其实倒也不是魏忠贤要如此,凭他一人怎能思虑得周详?不过是一人举火,万人添柴罢了。唉,人心本恶,唯利是图,哪个肯放过盘剥别人的机会?便为一文小钱,这天下也必有人愿杀人放火而得之。”
姜楚道:“既是如此,便不寻了吗?”
童牛儿心思却与旁人的不同,沉吟着道:“鸟儿飞过也有个影,何况是人?我偏不信。明日我便赶入浙东查寻,你们且等我消息。”
林猛见他如此奋勇,深受感动,上前握住童牛儿的手道:“浙东距此数千里,路途劳顿,你怕要多吃幸苦。”童牛儿摆手道:“不碍事。”
想着浙东对自己来说是片生疏之地,举头无熟人,怕不好办事。童牛儿以为还需找个冠冕理由,借助东厂的力量行事最方便。
刚巧银若雪接下一项去广东廉州左近剿匪的差事,说与童牛儿知晓。
童牛儿听后大乐,央求着银若雪带自己同往。
银若雪见这个一向贪玩好色的浪荡子如今竟有这等心思,不禁又惊又喜。道:“怎地要去?”
童牛儿想着还需言语里哄她高兴才好,道:“自然是上前杀敌立功,叫皇帝那老儿赏识,封我爵位。你父见了必要高兴,不就肯将你嫁与我了?”
银若雪最欢喜听到如此言语,心里美滋滋地甜蜜。以为童牛儿看着虽然无赖,其实骨子里还有些正经在。
童牛儿却不知此次同行的还有方威的白虎营在。
方威此时已将童牛儿恨入骨髓,常在夜里梦见将他如何,可见意欲之急迫。
今日听说童牛儿要一同前往广东,暗地里高兴。计算着战场上杀敌时刀剑不长眼睛,一不小心叫童牛儿怎样,谁也怪不得。待有机会便将他除去,便不为得着银若雪,只要能消融了自己胸中这口恶气也值得。
童牛儿却对方威不以为意。以为这小儿武功虽高强,但只是个脑大的白痴,不值得一虑。
把家里的事情仔细向卓十七等人交代明白,让他们替自己好生照看赛天仙、林凤凰、白玉香和霍敏英,防止她们受人欺辱。
卓十七知道童牛儿把这几个女孩儿看得心肝似的宝贝,满口应承下后,到春香院里安排下自己的住处,日夜守在她们的左右。
童牛儿见他如此,才放心地上路。
朱雀营加白虎营,共出动锦衣卫八百多名。各个精骑快马,赶路急迫。从京城出发后晓行夜住,只二十余日便已到达广东。
童牛儿却不善长途驰奔,一路下来把他折磨得肝胆错乱,肠胃颠倒,吃什么吐什么。且吃下三两,吐出时就是半斤,多出的二两皆是胆汁胃液,好不痛苦。每日就用蔘丹一类虎狼药吊着,堪堪支撑。
童牛儿此时才知自己这次讨到的竟是如此难熬的差事,心里后悔不迭,以为这救人水火的英雄实在不好当,不如在家里吃喝赌钱来得自在。
这日进入廉州境内。
当地官员早有听闻,已在驿站眼巴巴地守望多时。见众锦衣卫到达,忙不迭地过来见礼,然后迎入城里的驿馆招待。
银若雪和她爹爹雷怒海一样,向来是雷厉风行的性格。先将官员唤到一处询问当地匪患如何。
众人哪敢实讲?皆都用飘渺言语遮掩,只为开脱掉自己为官无能,治匪不利之罪。
银若雪见问不出所以,立时恼了,把在此地当权的廉州知府叫到眼前。见是个肥头大耳,身体胖的连胳膊和双腿都显得短促的中年人。瞧着滑稽,道:“你叫什么?”
这廉州知府长得虽不堪,但面上却有傲色。只将手略拱,道:“下官姓魏,单字名豸。”银若雪没有听清楚,道:“什么?”
廉州知府以为她在戏弄自己,悻悻地重复道:“下官——名叫魏豸。”银若雪也是无心,随口追问:“魏豸?哪个豸?”
却不想坐在一边的方威知道此人底细,向银若雪低声道:“就是‘狼虫虎豸’的豸,古书上指没有脚的虫子。”
银若雪听得这一句,再联想魏豸的身材模样,立时笑喷,道:“名如其人。”
那魏豸见这对男女当着这多属下如此调笑自己,自觉失却尊严。梗着脖子道:“我乃九千岁魏大人的义儿也。”
此语一出,满堂皆惊,惹得一众锦衣卫都转头看他。才知京城里传言的魏忠贤的‘十孩儿’原来有他在内,都不禁在心里暗骂一声‘狗屁’。
银若雪也才明白这魏豸为何敢与自己嚣张,暗地里咬牙,想:认贼作父的畜生,看本将军得机会消遣你。
但面上装得平静,道:“原来如此,失敬。魏大人,你向朝廷报奏说此地匪患猖獗,叫我等千里奔波来平灭。却说说,怎个猖獗法?也好叫我等心里有数。”
魏豸立时急了,回身向都埋头站立的属下咆哮道:“谁说此地匪患猖獗?哪个写的公文?站出来?”却无人应。
魏豸虽呆傻,也知问不出。回身向在上面坐的银若雪、方威、童牛儿三人拱手道:“众大人,休听他们胡言。此地在下官的治理下一向太平无事,繁荣昌盛。从不曾有匪患猖——”
他话音未落,听在驿馆外守卫的差人高叫道:“不好了——汪烧饼又来劫掠了——魏大人——”
魏豸在内的当地官员皆都惊得脸失血色。更有几个抱头便蹿,欲寻个缝儿钻进去躲藏,可见是被吓得胆寒了。
魏豸双腿虽然哆嗦,但还支撑得住。高喝道:“慌什么?众锦衣卫大人尽在,还怕他汪烧饼吗?”这一句倒管事,叫众官员安静下来。
银若雪等人一向是见惯拼杀的,只坐在那里笑吟吟地看着他们慌乱,似看着一窝鼠儿般有趣。
方威低身向前,道:“不是没有匪患吗?这汪烧饼又是做什么的?只卖烧饼的?”言毕哈哈大笑,好不得意。
廉州知府魏豸却被气得脸皮青紫,血涨瞳仁,一张嘴结巴着说不出话来。
银若雪以为这没脚的虫儿虽窝囊,但他既然能当上魏忠贤的干儿子,舔屁股巴结的能为自然不差。若真的惹恼他,去向魏忠贤说些咸淡,怕要给爹爹招来麻烦。说不定就把祸事弄到自己这一班人身上也未可知,何苦?
拿眼睛瞪视方威,止住他的嚣张。然后起身道:“魏大人,我们且去瞧瞧这个汪烧饼是怎样能为的人。敢在这里撒野,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童牛儿自在椅上坐着却不起身。
看着众衣饰华丽的官员尾随在一班耀武扬威的锦衣卫后面轰轰隆隆地去了,觉得好笑。以为和自己没甚关系,不需挂怀。只将新采的冰镇荔枝拿过来一颗颗剥着填在嘴里大嚼,连同酸梅干一起咽下,叫酸甜尽有,滋味齐全。
不过片刻,银若雪等人和众官员又都回转。童牛儿也懒得问,只听他们啰唣着的闲语就知只是虚惊一场,根本没什么汪烧饼来劫掠。
银若雪向魏豸道:“魏大人,这个汪烧饼是怎样来历?”
魏豸见已遮掩不过去,只得实说:“这个汪烧饼其实就是个吊炉子卖烧饼的,姓汪。如今聚下几百号人,打着‘讨饭吃,讨衣穿’的名号四处流窜骚扰。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好不猖狂。下官一直在下力剿灭,已见成效。如今又有众锦衣卫大人前来相助,想来不日即可克功——”
银若雪不耐听他顺嘴说惯了的这些冠冕言语,打断道:“协同我等剿匪的官军都到了吗?由谁调遣?”
魏豸略一迟疑,道:“不得上面吩咐,不曾调派军队给你们。”方威立时恼了,拍案道:“没有军队,叫我等拿什么剿灭匪患?”
魏豸因有魏忠贤在后面撑腰,并不惧他。扬眉抗声道:“你等所来不就是为剿匪吗?还要什么军队?”
方威起身喝道:“我等皆是御封的锦衣卫,身份何等尊贵?岂能丧失在这等不毛之地?”
魏豸一字不让,瞪起眼睛道:“锦衣卫又如何?还不是在我爹爹的治下?我爹爹让你等来剿匪,我看哪个敢不上前?”
他这一句叫银若雪等锦衣卫全都噤声。因魏忠贤提督东厂,人称‘厂臣’,正是锦衣卫的顶头上司,哪个敢不惧怕?
银若雪万不曾想这只没脚的虫儿竟如此地猖狂。但听他言辞间的‘爹爹’二字叫得响亮,以为虫儿虽然没脚,但伏身在魏忠贤这只猛兽的身上也就足够凶恶,可以傲视人间、吞吃天地,让所有人都惧他。觉得不值得和他争执,摆手罢休。
方威也被魏豸的言语吓住,不知觉间止息了火气,消减了威仪。颓身坐回椅上,不再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