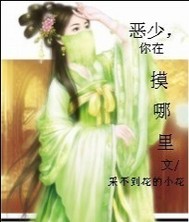第一零八章 梦境
怀衫进入一场冗长的梦境,梦里一个女子慈悲怜悯地笑望着她,眉眼温和,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白衣飘摇,周身笼罩着一层如梦如幻的光芒,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她在梦里呆呆出声,半响不知如何反应
“你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许我可以帮帮你。”
“你是钟玉神女?或许是受那个故事所困,她喃喃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神女含笑地点了点头,“那你是否知道我们之间的渊源,你可知道那个被人篡改地面目全非的传说?”
她高昂着头颅定定答道,“当然知道!你是天帝的女儿,被妖怪所伤,被书生所救。”
神女悲悯地笑着,虚幻的面容增添着一份神秘幽远的气质,“那不是真实的。凡间那些小妖的法力根本抵不过不修行百年的神女,我死于他的手里,他死于天雷地火之中,说不清是谁欠了谁,但你一定知道,自他死后,我便不曾出现过。”
那个被恣意涂抹历经千年面目的传说,在一开始神女因要收服在凡间胡作非为的妖孽而降落钟熟城,遇见那个如宣纸般纯净美好的书生。他们相识、相知而相恋。却因一场误会,最可怕的不是刀剑,她的法力可以抵挡一切,却封不住那些如疾风劲草恣意纷飞的流言蜚语,流言里他们被描绘成各种形象,他是个见异思迁的负心汉,她是个不知来历的妖女。
终于他承受不住压力抢先崩溃,卧病在床。她在病榻前告知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原以为他可以就此开怀,却未料自己迎来一碗下来毒的粥。
她怎会不知道那有毒,可还是含笑喝下去了。书生在她闭上双眼的那一刻,蓄积已久的泪水落在了她冰凉的脸上。她肉身一灭,重归天界,书生在她死后,没过多久也死了。
她等在奈何桥畔,等着他脱离身体的灵魂再一次相见,依然是一身白衣,鬓发凌乱,面容沧桑,而她依然美好如初见。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书生的选择,他看见她的第一反应,是温柔轻柔的笑容,喃喃低语,“你还是这样,真好。”
是的,他宁愿,宁愿在一开始就助她断掉凡根,也不愿每一天的凡间生活一点点磨灭她的仙气,让她再也返不回自己的世界,那样她还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寿命,在他死后,她又该如此度过。
书生并没有顺利投胎,他应该嗜杀神女被天帝降罪经受天雷地火,并将他的灵魂在忘川水里浸泡百年,最终将他化为高山绝壁的罂粟花。罂粟可以救人,也可迷惑人,他的存在彻底成了危害苍生的所在,故这些年我倔强地陪伴在这些花旁边,白天隐去它们的光芒,晚上吸收日月精华稍作修养。
“罂粟花从不是解毒的良方,虽然它有一颗善良的心。”
怀衫头疼欲裂地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她空洞地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一张焦急的脸“你醒了。”程皓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
怀衫点了点头,梦境的景象全然忘地干干净净。她极其自然地抽出了手转身四顾,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呢?怎么样了?”
程皓有些讪讪收起了手,转身挥了挥将恕儿抱到她跟前,“恕儿给你照顾地很好。”
怀衫看看孩子虚弱的脸上浮出一丝浅笑,眉目间的哀愁却未消减,“他在隔壁的房间里疗伤。”程皓声音平静,目光看着孩子,尽量装作一副轻松的无甚大碍的模样。
“我可以去看看他么?”他瞬时笼罩在她浓烈的哀求里,沉默地对视半响,轻轻地点了点头,“但今晚你必须卧床休息,明日我领你去见他。”
怀衫点了点头,看了会儿孩子放心地睡下了。程皓待她重新闭上眼睛,对程凌作了个手势,脚步沉重地走出帐篷。
怀衫在床上昏迷了整整五天五夜才清醒过来,而在这五天里,他不断在两个房间中辗转,入夜就吩咐人在断壁崖上寻觅。五天来他们几乎寻觅了每一寸有可能性的崖壁,却一无所获。瑖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毫无意思苏醒的迹象。在婷芸给他疗伤的时候,他坚持站在一旁,这才看清褴褛青衫下是一举怎样破乱的躯体。他能留延续一口气已是奇迹,若救命的草一直找不到,那么、、、
他不敢再想下去,宫中的情况也一天天危急起来,南疆虽无异常行动,只要夏瑾瑜一声令下,这个江山又该是怎样一场风雨变幻?他只希望康瑖若能够撑到那一天,能够意气风发,自信十足地面对每一个突发情况,能够轻而易举地瓦解每一困境,能够、、、、、、,他这才意识到,从来,康瑖若才是那个决策天下的人,可是他的命,又该由谁来决策?
难道真的是她么?
“如果这样,请你一定要醒来,我们像兄弟那样,公平竞争赢得这个女人的爱情,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积聚一丝一缕不断消逝的生命之光,那你就醒来吧!”他看着病榻上一动不动的他,面容同严峻,浓眉拧了拧,走到外面。
山风呼啸,这些天来,他们根本就不曾下山,他的身体经受不起大程度的移动,婷芸索性就地搭建帐篷,帮他疗伤。太子的伤她没有一丝把握,这些天将他的伤口清洗赶紧用鱼肠缝上,对于受了上的内脏,修补好了外面,里面又该怎么办呢?
她熬完药端来,恰好撞上程皓迎风长立,脚下犹豫还是停了下来,“程少主,若您不介意,今晚我想亲自下去找寻那种草药,我是医师有自己的直觉。”
程皓无声地点了点头,山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模糊了他的表情,也彻底绞碎他一颗混乱的心,强大如斯,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脆弱和无助。
怀衫不一会儿就进入深睡,钟玉神女的笑靥化为梦魇,严严实实地将她笼罩期中,她从未离去,只是以这种方式出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