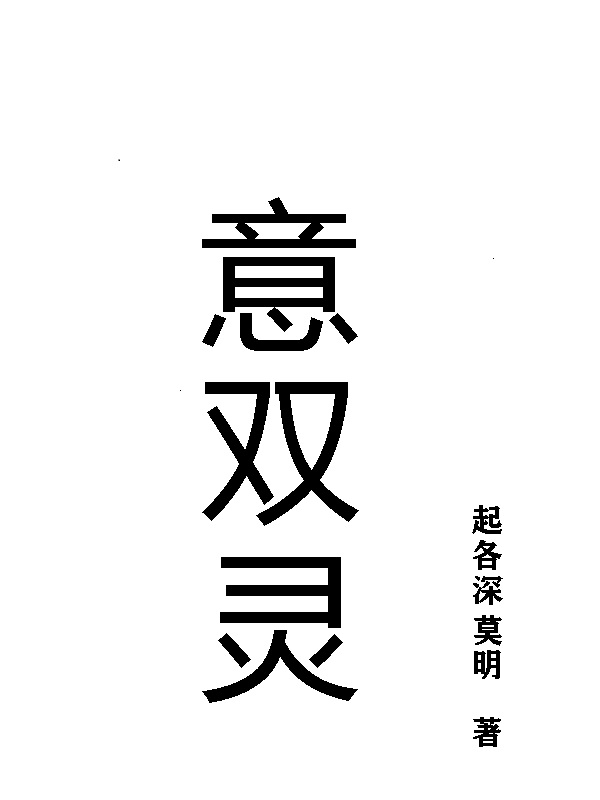下雪后的往事
蓟州孟凡生作于2011年12月2日
正月十五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都会使我想起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件,那就是1971年的正月十五一场大雪后,赵翰林村客土种麦的情况。
已经快到“大雪”节气了,今天终于下雪了,这是蓟县城区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脑海里又浮现出另一件雪中的往事,就是四十年前因为一场大雪,激发出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客土种麦”的奇迹。因为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现象了,故值得写出来供年轻的网友们一阅。
俗话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也不记得1970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是否有“云遮月”了,可在1971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确实下雪了。而且雪下的很大,地面的积雪足有五六寸厚。
当时我正在蓟县刘家顶公社赵翰林庄村从事“斗批改”工作,是“斗批改”工作队的队员。当时工作队的队长是老樊,指导员是聂洪波,队员还有于广兴、老王、张秀云、张志荣等人,当时赵翰林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是王连福。因为在1970年冬季的“斗批改”运动中,赵翰林庄已经完成了斗批改的政治任务(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资本主义倾向;改章建制、改建农村领导班子),建起了新的领导班子。所以,71年春节后,工作队主要任务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
按照正常的春种习惯,元宵节后是应该“赶着冰碴种大麦”的。按照传统的播种方法,都是按“垄”种大麦,就是每隔一尺多远用“耠子”耠出一条垄沟,把麦种撒在垄沟内,再用“划拉”(一种下面有耙齿的长方形木框)和“菜耙”搂平。由于“垄种”的种法产量不太高,当时上级推广科学种田,就要求用“苫种”(先在畦田里漫撒种子,后在种子上面盖一层土的播种方法为“苫”)的方法,实行密植,提高产量。为此,县委、县生产部和“斗批改”指挥部决定,正月十七日在赵翰林庄搞试点,召开推广“苫种”大麦的“现场会”。蓟县西部的邦均、尤古庄两个工委及所管辖邦均、白涧、李庄子、东二营、许家台、刘家顶、西塔庄、尤古庄、侯家营、三岔口等十个公社,二百多个村负责农业生产的干部,都要到赵翰林庄来参观“苫种”大麦现场。所以,在正月十四之前,赵翰林庄各生产队就把“大麦畦”都做好(畦田里要松土撒粪),只等“苫种”了。由于元宵节下了一天大雪,原来“苫种”的计划被打破了。
因为“苫种”需要把畦内的表层土铲起堆在旁边,撒完种子后再把土铺洒在种子上面。这场雪下的比较大,“大麦畦”里的表层土已经全湿透了,不论是“苫种”还是“耠垄”播种,都需等地面晒干些才行,估计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那样必然会影响大麦的产量。为了不耽误农时,同时保证现场会的如期召开,正月十六这天,工作队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商量对策,决定“客土种麦”。就是把村中一块“高地”里的干土(把表层积雪和湿土铲走,用下面的干土)运到大麦畦的旁边,用这些“客土”,来苫盖畦中麦种。“决议”形成后,事不宜迟,确定在当天晚上,利用“大月亮地”,组织社员搞一次“义务劳动”(不给记工分,无偿奉献)。全民“夜战”,刨土、运土,为明日白天“苫种”做好准备。当天下午,聂红波和王连福用大喇叭(村里的广播放大器)对全村进行了“战前动员”,要求全体整半劳力(16至65岁为“劳动力”,要参加集体劳动。其中55岁以上,18岁以下和身体残疾者为“半劳力”。66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少年“非劳力”,如果愿意去队里劳动,队长也安排“轻活”,挣的工分要低于“半劳力”。平时集体开会、晚上政治学习等也不要求“非劳力”参加)不分男女老少,全部参加“夜战”。
正月十六的晚上,满天星斗,皓月当空。赵翰林庄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吃完晚饭就出来参加“夜战”了。大概是“斗批改”运动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也可能是在本村召开现场会(是光彩事)的消息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人们都是兴高采烈的参加毫无报酬的“夜战”,不仅是整半劳力都来了,有些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休寒假)也来了。青壮年劳力都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带着铁锨、大镐、双轮车、独轮车、抬筐、挑筐等工具,汇集在村东地里。老人、小孩们挎着篮子(俗称笼筐子)、背着粪箕子也来了。有的村干部让老人和孩子们回家睡觉去,他们还不走,美其名曰“蚂蚁搬家”,多少也管点事。最后,聂洪波说:“不要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了,愿意干就干会儿吧,累了随时可以回去睡觉”。
现在我想,因为那年代农村还没有电视机,晚上也确实没什么事,又不可能黑天就睡觉。搞义务劳动“打夜战”是个新鲜事,也是热闹事,老年人和孩子们主动来参加“夜战”,凑个热闹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当晚村子里真可谓人欢马叫,热火朝天。
大家来到东边那块“高地”处,男的刨土,女的装车。先装满生产队的大马车,再装人拉的双轮车和手推的独轮车,还有抬筐、挑筐等等。当然运土的大多也是男劳力,女劳力负责装车、卸车。从高岗子地到畦田也不太远,一二百米的样子。土路上人来车往,推的、拉的、挑的、抬的、背的、挎的,还真够热闹。大家边干边说笑,也不觉得累。因为那年代农民们一般没有手表,大家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那些老人和孩子们,干到十来点钟就回家睡觉了,剩下劳动力继续干活。工作队员们那时讲“三同”,就是和社员同吃(各家吃派饭),同住(住在社员家,房东家的姑娘与女队员同住,未婚小伙子和男队员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下地干活)。所以,我们也都跟着大家一起“夜战”,我主要是用铁锨装车。
正在干活时,聂洪波找到我,让我领着几个人到村内的小学校去,为明天的现场会搞点“政治空气”。这时我一看手表,已经是夜间十一点多些了。我们一共找了八个人,第一个是学校的王老师,他负责写大字标语。两个20左右岁姓王的小伙,都是共青团员,负责上树砍手指般粗细的树枝,把树枝削成一米多长的一头带尖的木棍,在地里插标语牌用。以团支部副书记陈秀文为首的五个女青年负责熬浆糊,裁纸,做标语牌。
那时村里有小卖部,买彩纸和墨汁也方便,大队的造纸厂(集体副业)里有收来的废纸箱,拆开纸箱,裁剪成四开纸(一整张纸横竖对折裁成四张)大小的硬纸板,把硬纸板用细铁丝绑在木棍上,再把写好标语口号的红、黄、蓝、绿色彩的纸,用浆糊粘在硬纸板上,这就是标语牌了。老聂要求我们做50个小标语牌。到午夜十二点多钟,陈秀文她们从大队库房领来熬浆糊用的白面,从造纸厂找来废纸箱,从小卖部买来彩纸墨汁等物,当我们准备就绪时,地里“夜战”的人们也“胜利结束战斗”,回家睡觉了。
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天晚上的月亮真圆。而且那年代空气污染少,天空透明度高(过去能看到的星星比现在要多),明亮的月光照的大地如同白昼。午夜之后,村里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只有村外公路旁边的杨柳树上,不时地发出咔咔的响声,那时小王他们正在树上砍树枝。村边小学校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王老师在办公桌上写标语,陈秀文她们有的裁纸,有的在三开炉子(带烟筒的煤火炉)用水桶熬浆糊。
聂洪波、王连福他们到学校看了看,见我们已开展工作,叮嘱几句就走了。这里的工作就有我具体负责督办了。我没有具体活干,就往返于学校与路旁砍树枝人之间,我站在树下不断提醒他们一定要加小心。好在一根大树枝可以做两三个标语牌的立杆,不到一个小时就砍够用了,用小车运到学校内,再截成一根根的小木棍。然后他俩就帮着姑娘们用铁丝把木棍拴在硬纸板上。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小学校的办公室里,灯光明亮,笑语欢声,小王、小陈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没有一点困倦的感觉。王老师挥动大毛笔,唰唰唰的写着大字,不断赢得大家对他书法功夫的赞美声,他也越写越起劲。他写的标语字体大小有三种,有毛笔写的贴在标语牌上的中等楷书,又有写在10厘米宽70多厘米长的彩纸条上的小楷毛笔字,还有用板刷写在四开纸上每张纸写一个的隶书大字。总的看这位教师的书法是不错的。
在凌晨五点钟的时候,王老师把标语都写完了,标语牌也做完了。我们让王老师回宿舍休息,然后就兵分两路,两个人用小推车推着标语牌,到大麦畦的地头和路边去插牌。其他人,拿着笤帚,提着浆糊桶,带着写好的大字标语和小字纸条标语,到村边和主要街道上去张贴。一个人负责提桶,一个人拿笤帚从筒里沾浆糊刷在墙面上,后边的人用手把写好标语的彩纸贴上去,最后一个人拿把干笤帚再把彩纸刷一下。一道工序要四五个人,而且天冷浆糊容易结冰,所以进度不快。天大亮以后,外村来开会的人已经陆续骑着自行车来了,我们还在往墙上贴标语。
天快亮时,工作队的聂指导员、樊队长和王连福等村干部来检查贴标语的进度,表示很满意。表扬几句后,要求大家吃完早饭后继续到地里去苫种麦子,下午在休息。聂洪波还对我说:“小孟你和他们的队长说一下,让他们几个下午在家睡觉,照常记工(下半夜加班等于下午出勤)”。我就去对几个生产队长传达了领导的“指示”,队长们当然要执行了。所以,这天上午,小王、陈秀文他们七个人都到地里去干活了。
上午九点来钟,开会的人们到齐了。我们工作队跟着开现场会的人们一起,先到地里参观社员们山种大麦的情况,然后回到小学校操场(会场),旁听大会。参加会的有二百多人,大家就坐在地上听会。先由赵翰林庄的村干部和工作队领导介绍经验,然后县领导讲话。我当时坐在冰冷的土地上,在听会时竟然抱着膝盖打起盹来。
午饭后我按照领导关于“下午可以睡觉”的指示,来到小学校王老师的宿舍,躺在王老师的单人床上和衣而卧,饱饱的睡了半天觉。因为我和工作队员老王住的房东家没有炉火,王老师宿舍生着煤火炉,我才在这屋睡的。
这天晚上又是集体学习的日子(每周固定几个晚上七点至九点,进行政治学习),我又见到了小王和陈秀文等人,才知道这天下午他们七个人没有一个在家休息的,全都到地里去干活了,而且晚上又全部来参加学习。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睡觉,他们都说“一点也不睏”。要知道他们可是一昼夜没合眼呀,为什么领导安排让他们睡觉都不睡?哪来的这么大的精气神?他们下午去地里干活的举动,既得不到奖励的“工分”,也没有领导人的表扬,他们究竟图的什么呀?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难道就王老师我俩是血肉之身,知道犯睏睡觉,他们都是铁打的身躯,不知疲倦吗?
这件事过去之后,每逢冬天下雪的时候,就使我常常回想起当年赵翰林庄全村男女老少月夜奋战,热火朝天的场景;回想起村里这几个青年人无私奉献、精力充沛、昼夜奋战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