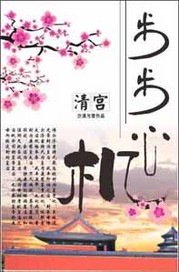江子萱走到江家大门前,奉命赐匾的宫人早已经离去,但江家的热闹丝毫不减,此时天际尚有霞光,管家却已经安排下人在里里外外点起了红烛,烛光摇曳,直到江家大门的街道两旁,地上也铺了厚厚的丝绒毯子。上上下下一片喜庆祥和,若是给不知情的人看了,大概以为江家又要有娶妻嫁女的事情了。
看门的家丁见到她,大喊道:“三小姐来了,三小姐来了!”
话落,一群族中的姐妹纷纷迎了上来,七嘴八舌的与她寒暄。
“三娘呀,恭喜恭喜!”
“三娘真是好福气,能得太后赐字,以后怕是天下闻名了。”
“我早就看出来三娘不是凡夫俗子,这不?能够为普化寺画壁画筹集香油钱,还能打动太后赐她气节才淑的美名,真是了不得了!”
……
江子萱没有应她们的话,前面这些人,曾经不止一次私下里嘲笑她是个口吃的无才女,甚至前段时间,还说因为族中出了她这样失节无才的女子而感到羞愧。转眼间,便开始称赞她非凡夫俗子!人情冷暖,真是讽刺!
她没有出言相讥,却也没有热情应答,不过冷眼旁观而已。
众女说了半天,却见她反应冷淡,不由悻悻然,饶是左右逢源惯了,也再也接不下话去。
“三娘,你回来了?”
听到江邵乐的声音,众女皆松一口气,江邵乐似乎也不喜欢这许多人围在一起,对大家说道:“你们都到厅中用膳吧,各位长辈皆已经入座了。”
闻言,没有人迟疑,告辞离去。
周围终于安静下来,江子萱也跟着轻松不少,还不等她为自己擅自离家的事情请罪,便见江邵乐看向她身后,道:“怎么,尉寒没有跟你一起进来吗?”
江子萱蹙眉,为何石尉寒要跟着她一起回家?
却见江邵乐也蹙起了眉头,面带责备的说道:“三娘,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懂得礼数!尉寒既然将你送到普化寺,又不辞劳苦的将你接回来,于情于理,你都该请他进来喝杯茶才是!更何况,你们已经有了婚约,也没有避嫌的必要。”
江子萱越听越奇怪,问道:“哥、哥哥,你在说、说什么?”
被她这一问,江邵乐一惊,仔细打量她,见她一双无辜的眼睛尽是迷茫之色,心里咯噔一下,道:“难道你……当初是私自从高家的满月宴上逃走了?”
江子萱怔住,而后木木颔首。
江邵乐顿时想明白事情始末,脸色一变,咬牙切齿看着她,似乎想要将她痛打一顿,又似乎下不去手,一副气急败坏之象。
半响,方才痛心疾首的说:“三娘呀三娘,为兄说过你多少次了,你为何总是不改改性子?为何还要任性妄为?竟然又敢私逃出去,你可知道,你不见之后,京中有多少关于你的流言蜚语?”
“流、流言蜚语……”
见她还是一副迷茫模样,江邵乐不由恨铁不成钢,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真是、真是该打!”
说着,他一顿,又道:“当时京城中到处在说江家三娘与人私奔,便是为兄我……也信了几分,亏得尉寒深明大义!虽说你离家是为了让太后赐字给你,但此举委实拎不清轻重。若是石家因此悔婚,你即便得了太后的赐字又有何用?前后被退婚两次,你以为你还有名声吗?”
江子萱隐约想明白当时的情况,定然是诸如江月红之流,知道她不在江家,故意散布谣言污蔑她的名声。
只是,这些,和石尉寒又有什么关系呢?
江邵乐叹口气,也不用她问,径直便解释道:“若不是尉寒登门,替你澄清,说是丘公的旧人赏识你,邀你作画,因为事出紧急,你来不及告辞,他只得替你来说,还保证说等到十七会按时将你送回家。我昨日在寺庙里见到你的画作,还以为他是将你送到了普化寺,没有想到,他是为了保全你的名声而撒了谎,根本是你私自逃离。”
闻言,江子萱的脑海中,浮现出石尉寒从后面搂住她,欢喜说着‘你回来了’的画面。随即,又想起江邵乐说,他是真心喜欢她的话。
她的鼻头不由一酸,她今晚的做法,确实是伤到了他。
江邵乐见她那模样,伸手拍了拍她的脑袋,又劝道:“三娘,我知道你心中还想着谢安然,可是他不是你的良人,他差尉寒许多。”
“我……”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与你说了。三年前,他们谢家在朝廷失势,刚好北方战乱四起,他们的良田产业全都化为乌有,若没有外力扶持,怕是要沦落得变卖京中产业也无法延续太久的地步。那时,他们便已经看上了我们江家,看上了你这个江家嫡女,可偏偏父亲一心想将你嫁给尉寒。谢家有心破坏你们的婚事,谢安然更是借着与江月红这个贱人交往的机会,打探到家中的事情,然后借着她的手,四处散播你不仅口吃,还胸无点墨的事情……”
江子萱感到自己的脑袋被一根粗棍狠狠打了一下,打得她头晕眼花,险些站不稳。虽然,从蛛丝马迹中她早有了准备,谢安然和江月红的关系,绝不像是谢安然所解释的那般简单。但是当得知真相,她还是有些难以相信。
她不由想起三年前,谢安然与她初次见面时,他脸上真诚的笑容,善意的话语……
她曾经以为最美好的回忆,以为可以保存一辈子的情意,原来都只是为了他个人利益而做出的戏。江月红身为江家的二小姐,若不是与他心心相惜、海誓山盟,又怎么会帮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江子萱下意识捂住了心口,她还以为自己做到了淡然,做到了不为外物而悲喜,原来还是没有做到。
江邵乐见她悲恸欲哭的的表情,不忍心再责备下去,转而劝道:“其实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若没有这番波折,你又怎么知道尉寒对你的心意?”
江子萱心不在焉的颔首,她的兄长是局外人,没有经历过她和谢安然之间的种种,自然可以说得云淡风轻。
江邵乐见她不想再说,忙转移话题,道:“好了,不多说了,父亲已经命人备宴庆祝,你随我进去吧。”
“备……宴?”
“你得太后赐字,此乃光耀门楣的大事,自然要备宴庆祝。”
她摇头,此番心乱得很,只想一个人静静。
江邵乐见状也不勉强她,柔声说道:“你不愿意去就不去吧,反正今日只是准备仓促的家宴,明日方是大宴宾朋。你现下好好去休息,等到明日可要打起精神出席宴会,万不能再任性了。”
……
江子萱心事重重,一夜辗转反侧,待到天快亮时方才迷迷糊糊入睡,醒来已经是日上三竿。
她刚洗漱完毕,江邵乐便到了她的院中,说是昨天发请帖之时遗漏了石家,未免石尉寒疑他江家有故意怠慢之嫌,要她亲自上门邀请。
江子萱何尝不知道兄长的用意?这是要借机撮合她和石尉寒的关系。只是,现下的态势,怕是要让兄长失望了。
她脑海中,不由响起长笙公主说过的话,若是她此番去石家,刚好遇到长笙公主,那该有多尴尬?
思及此,她下意识的摇头,只是她的头才摇到一半,江邵乐的脸便板了起来,道:“三娘竟然不听为兄安排了?若是你实在不愿意去,那只有为兄去,可是今日为兄要招待宾朋,哪里抽得出时间来?要不然,你去招待宾朋,我去邀请尉寒?”
江子萱苦笑,她最怕的就是与人打交道,还有她的兄长生气,如今两样都占全了,她如何能不去?
她欲言又止,想说长笙公主现下住在石家,可又不忍心看到兄长失望的表情,最后只能无奈的颔首。
见她颔首,江邵乐立马笑颜逐开,唤了巧儿陪伴她,不由分说就让她出门。
江子萱暗自苦笑,走到大门口时,门口挤满了人,原以为是一些早到的宾朋。她扭头,穿过人墙,发现有个布衣男子跪在地上。
她疑惑,欲举步上前查看,却被巧儿一把抓住了她的臂膀。
“三娘,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快些上马车吧。”
江子萱看巧儿,又看那被人墙围住的男子,面带犹豫。
巧儿了然,知道她见不得这样的场面,不以为然的解释道:“此人是个寒门出身的读书人,许是不太得志,所以想要引起老爷的注意。从昨天晚上就在这里闹了,说什么北方胡人就要打过来,还有暴民也将涌进城里,我们江家若是有钱,应该把它们都用于招兵买马,安抚流民上面。而不是十里红烛,软毯奢华。”
说着,巧儿鄙夷的看了那男子一眼,接着道:“依我看来呀,此人不过是因为自荐无门,所以趁着我们江家大喜的日子,故意在这里来闹,以便引得他人的注意,什么胡人,什么暴民,若是真要打过来了,那些朝廷的武将们是做什么的?”
江子萱张嘴,愣愣的看了地上的男子一眼,喃喃道:“我……一路行来……尸横遍野。他所、所说,未必是假。”
巧儿扯了她往马车里走,边走边说道:“三娘呀,这不是我们女人该管的事情,我们还是快些去请未来的姑爷吧!姑爷可是领军将军,有了姑爷,我们还怕暴民和胡人吗?”
江子萱欲言又止,再次看了跪在那地上的男子一眼,想要做点什么,可是当她对上金光灿灿的江府牌匾时,顿感无力。
进到马车里,马车一动,透过车窗,碰巧看到几个布衣百姓蹲在地上刮拾他们江家昨夜点在街上、没有燃尽的红烛,她的心里又是一叹,这个寒门男子的话未必不可信,可如同她们江家一般的世家皆已经奢华惯了,哪里是一两个寒门子弟能劝住的?
便是她自己,这盛宴是因她而起,她也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再一想到北方胡人和暴民,她一阵心惊肉跳,这个寒门子弟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