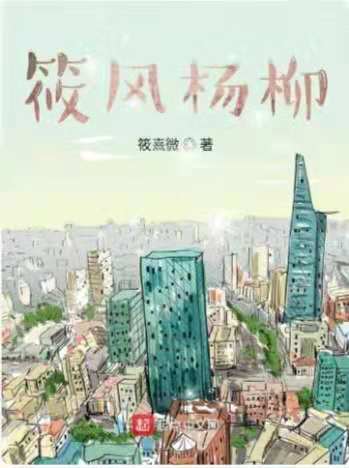马车内实在是太过拥挤,眼见着长笙公主纵身扑过来,石尉寒想躲也躲不掉,他只得用手护住腹部,屏息承受了突然来袭的美人恩。
长笙公主撞到他强健的身体,最初的疼痛过去后,心里产生一阵恍惚。往常里,她只是被他的外貌和气度所吸引,如今真的接近他,方才觉出,他不仅气质非凡,就是身体也比那些士族子弟们精壮许多,这样的丈夫,才是强者,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
念及此,原先的羞怯和矜持荡然全无,长笙公主软了身体,欲靠在石尉寒的胸膛上。
反观石尉寒,没有因为她的投怀入保而表现出丝毫的喜悦,面色倏忽胀红乃至铁青,额上冒出颗颗大汗,手搁在他和长笙公主中间,似乎隐忍般咬牙切齿的道:“公主请自重!”
“石郎,我仰慕你……”
不等长笙公主说完,石尉寒猛力一推,一下将她推撞在马车壁上。
“啊……你……”长笙公主吃痛,正欲张嘴大喝,却发现他正吃力的用手捂住腹部,一副疼痛难忍的模样。
长笙公主立即爬了起来,惊道:“你,你怎么了?”
“劳烦、劳烦公主唤军医前来,我的旧伤……复发了。”
见他说话已经是有气无力,长笙不敢耽误,立即转身,后颈窝处忽然传来一股疾风,她下意识的闪到一边。
石尉寒这一击不中,没有了力气,只得收回了手,软弱无力的靠在车壁上,也不管晕倒在一旁的长笙公主,道:“来人,将公主送回京城。”
长笙猛回头,意识到他方才是想将她打昏送回京城,嘴唇颤抖的说:“将军如此容不下长笙吗?”
石尉寒无力的摇了摇头,脸色惨白,道:“我旧伤确实复发,并非借口!现下暴民四处,胡人为患,我自认平庸无能,无力护公主周全,只得用此下策送公主回京。”
闻言,长笙面露担忧,不答石尉寒的话语,问道:“将军可需长笙为你唤来军医?”
石尉寒摇了摇头,道:“不用,这次行军时间紧促,我乃小伤,不可因此耽误进程。”
“将军顾全大局,令长笙更加钦佩,长笙诚心祈求将军给长笙一次机会,让长笙能够得伴将军左右。”
“公主何必如此?石某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公主乃是金枝玉叶,委实不该在我身上花费时间。”
“将军!我对将军诚意拳拳,将军何故用客套话语搪塞我?”
“哎……公主如此说,那我便也不隐瞒了,其实我早就有了属意之人,所以只能注定辜负公主的美意了。”
他话落,长笙的睫毛上面挂上了晶莹的泪滴,随着睫毛的闪动,那泪光耀耀平添了几分楚楚可怜的风情。
石尉寒原以为她会掩面啼哭,谁知道,她忽然止住了夺眶欲出的眼泪,轻轻说道:“将军,长笙知道将军并不喜欢长笙,却也不该以此为借口回绝长笙。”
“哎……我句句实话,何来借口之说?”
“将军既然有属意之人,为何未听人提及过?天下谁人不知石将军未有妻妾,便是相熟一些的仕女也没有,将军如此说不是借口是什么?”
“非我撒谎,实在是我钦慕之人心中无我,我自然无法让世人知晓,更无法娶她为妻。”
长笙面上愤愤然,道:“是哪家的女子,好生不知惜福,将军能够爱慕她实在是她的福气,她竟然不识抬举!既是如此,将军为何不……”
“公主,请莫要强人所难!”石尉寒虽然依旧客气,语气却不由严厉起来,眼神也十分疏离。
长笙一震,却并不死心,道:“将军,长笙不知道将魂所仰慕的是哪家女子,也不知道长笙似乎比得过对方!但是,将军与其将心思放在一个无心于将军的女子身上,不如给长笙一个机会……将军以为呢?”
“给你一个机会?如何给呢?心意之事,岂是说了就算……”
石尉寒这话说得极为无奈,一向聪慧的长笙自然看了出来,忙再接再厉说道:“请将军允许长笙跟随将军出征,若是将军班师回朝之时未曾对长笙有一点男女之情,长笙自然不会再纠缠将军!若是相反,长笙愿与将军相守百年。”
说到这里,长笙微微一顿,又道:“将军放心,长笙是个省得轻重缓急的人,自然不会拖累将军的。”
“哎……你这是何苦呢?”
石尉寒叹息,眼中似有同情和感叹之色,看得长笙心里一喜,本以为他会答应,却听他坚决说道:“公主何苦如此用尽心机呢?公主是待嫁之身,尉寒是无妻之人,若是你我相处多日,纵使光明磊落,外人如何会相信?还有宫中的太后和陛下,如何会让公主声誉受损,只怕到时候,无论我心里有无公主,都得娶公主为妻!”
“你……你……你的心难道是石头做的?我已经如此哀求……”
石尉寒失去了耐心,重重吐出一口浊气,道:“公主,石某身体不适,还请公主速速离去,那样,石某尚能派人护送公主。否则……”
“否则如何?”
“否则只能将公主强行留在此地,现下暴民肆掠,只怕会伤到公主。”
“你……你竟然敢如此威胁我!”
石尉寒并不看她,话到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他将奉命在马车外等待的士兵唤了进来。
这般一来,长笙公主即便再不甘愿,众目睽睽之下,也只得被迫离去。
她走出马车,环视众人,重新恢复了高傲的皇家气质,抬首挺胸的下了马车,站在马车车厢旁边,小声说道:“石将军,我且等着看,什么样的女子能够得你的欢心。但愿,她真比我好上许多,否则让我如何甘心?”
闻言,石尉寒怔愣,尚不及回答长笙,她已经乘上了自己的马车,缓缓离去。
……
江子萱在六疾馆中连住两日,作了两、三副画卷,遣馆中下人拿出去贩卖,虽然所得并不丰厚,却也能勉强支撑近来的开支。
只是,这到底不是长久之计,她必须筹集更多的银两,否则莫说救助穷人,便是六疾馆里上上下下那百来张吃饭的嘴,也会饿死。
这般一来,她的日子充实起来,暂时便忘记了谢安然和江月红所带给她的烦恼。
若不是,江闵找人唤她回府,她几乎就要忘记江家,忘记她的及笄日子,也忘记了所有的伤痛。
坐上江闵派来接她回家的马车,江子萱便满腹心事,脑海里一会是谢安然深情款款的誓言,一会是江月红得意洋洋的神情。
在进入江闵的院落之前,她又想到了往事,想到惨死的路姨娘,想到妻妾满堂的种种弊端,也想到了丘聃的教导。
人生在世,皆有不可求之事,与其苦苦去求,伤人累己,还不如就此放手,省却大家的麻烦。
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有痛,虽然不舍,可她隐隐得到了解脱,寻到了安宁。
她遭石尉寒当众拒婚,又因为身患口吃之疾而被众人嘲笑,可是,她依旧是高傲的,即便这样的高傲伴随着难以抹去的自卑,她依旧高傲!
她不愿意与人分享夫婿,更不愿意在家里还要提心吊胆、勾心斗角,所以她宁愿现下忍痛成全江月红,也不愿意将来数十年里与她纠葛一起。
她一步一步的向着江闵靠近,心头绞疼,却走得异常坚定。
远远的,便见到江闵高高坐在堂上,眼神晦暗不明。
她上前几步,俯首一拜,道:“爹……”
“哼!还知道我是你的爹。”
听出江闵话中的冷意,江子萱慌忙抬头,小心说道:“爹、爹爹何、何处此言?”
“还想瞒我!”说着,江闵狠狠将手里的茶杯掷到了地上,怒吼道:“自古以来,婚姻皆是父母之命!你和大郎倒好,什么事情都私下做主,将我这个父亲视为无物!”
江子萱一震,垂首不语,生怕说错了什么牵连到江邵乐。
江闵却不依不饶,道:“我来问你,可是你怂恿大郎将二娘送给一个寒门子弟的?”
事情,确实不是她的主意,却是因她而起,江子萱不敢不认,小声道:“是……”
“你还敢承认!好狠的心肠!”江闵连连拍桌子,似乎被气得不轻,砰砰的声音十分震耳。
他吼了好一会,江子萱依旧没有说话,他大概觉得无趣,方才收敛了脾气,语重心长的说道:“三娘呀,并非为父责怪你和大郎,实在是你们这般的做法有失妥当!你容不下二娘,那你可曾想过,以你的相貌和才情,嫁到谢家去,如何能够将谢安然的心给拴住?若是有二娘帮衬着,那便不同了。”
“我、我不需……要任何……帮衬,我惟、惟愿求得……一心人。”
“怎么又说傻话了?”江闵一顿,又继续道:“我知道,你尚且年幼,没有长远的眼光,难免争强好胜,想要与二娘争个高下。只是呀,谢安然到底喜欢二娘多一些……大郎将二娘私下送走的事情我也不追求了,但如今她毕竟有了谢家的骨肉,谢家的家主为了此事也亲自找我谈过,你便宽容一些,与二娘好好相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