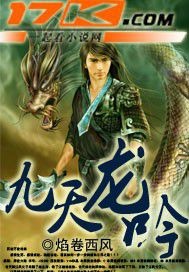江子萱心里乱得很,不想吃饭,不想见人,尤其是不想见江家的人。这些人,或许都知道她和江月红的事情,或许上一刻还以她为谈资,下一刻见到她又要做出十分亲厚的样子。
思及此,她再也呆不下去,告别江邵乐进到屋内,便胡乱收拾了一些行礼,拎着她的大包袱,悄悄从侧门走了出去。
走出不过百步,听到后面有人连声唤她,她不得不停下来,扭头一看,竟然是春红。
江子萱蹙眉,她本就不喜欢春红,在心情糟糕的现下更不愿意见到对方,遂沉了脸,冷冷看着对方,静待对方说话。
春红发现了她的不快,犹豫片刻,终是小心上前,对她屈膝一拜,说道:“小姐,你这是要去哪里?”
“与你……无关。”
“小姐说笑了,奴婢是小姐的奴婢,自然要近身侍奉小姐,怎么能说无关?”
“哼!我、我已经禀、禀明兄长,很快就、就会将你……打发出府。”
“即使如此,现下奴婢也还是小姐的奴婢,理当在小姐周围服侍。”
“你……”
“若是小姐不认可,大可以找家主定夺。”
江子萱为之语塞,她本来就有意避开江家的人,这个春红许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故意用此威胁她。
她紧了紧包袱,愤愤然转身,不再搭理春红。
春红亦步亦趋跟上,几次想要伸手将她的包袱接过去,皆被她拒绝。
跟着她走了将近五里地,春红忍不住宽解道:“小姐,这里……虽然是京城,可城外围有流民,城内也并不安全。以奴婢……之见,你还是回府去吧。那里毕竟是小姐的家,天大的事情也可以与家人商量,何必离家出走呢?”
江子萱装作完全没有听见春红的话,径直往京城的北市走去,穿过繁华的街道,来到一处幽静的小巷子,环顾四周,而后朝巷子深处走去。
春红心里犯嘀咕,将巷子里破败的房屋和难闻的气味自动摒弃,亦步亦趋的跟在江子萱后面。待走了百来步,方才见到一处隐蔽而特别的院落。
泥色的木门、陈旧的石墙,普通而干净,与四周那些脏乱的院子皆不同。尤其是那挂在门上的牌匾,匾上题着遒劲有力的三个字——六疾馆。
春红识字不多,却也能认出个好歹,这样的字,定然出自名家之笔。她尚在琢磨,江子萱已经上前拍打院门,很快出来一个身着粗布麻衣的老妇人。
江子萱从怀里拿出一块青铜牌给老妇人看,老妇人没有多言,俯首行礼,而后将她们二人迎了进去。
随即,拿出了几本账本,恭敬的递到江子萱手里。
春红偷眼看去,刚好看见‘初六,米十担,于北市口救济穷人’的字样,不由诧异,道:“小姐,这个六疾馆,难道是专门行善事的那个六疾馆吗?”
江子萱淡淡颔首,依旧埋头看账本,而后将账本阖上,对那老妇人说道:“下、下月是……赏荷的……好时机,我、我再画……几幅荷花图,你、你着人去卖了……”
老妇人应了下来,而后作难的说:“小姐,实不相瞒,你的画作虽然有不少人赏识,可到底没有丘公的画作受了追捧,所得银两实在是……”
闻言,江子萱神色黯然,老妇人说的话她如何不知?
丘聃一生无妻无子,看似无牵无挂,其实心怀天下,虽然对朝政不满,却也一直致力行善救民的事情。
他真正是个一字千金的人,京城一代的六疾馆便一直依仗着他的帮助筹集善款。可如今,他故去,江子萱继承了他的遗志,却十分吃力。
他只要提笔一掷,便会有无数附庸风雅的人士掏金掏银。而江子萱,纵使被他一再肯定,赞扬她的书画已大成,所作的书画却很难卖到大价钱。
往日里,她只负责作画,然后命人拿去卖了换钱给六疾馆,这是第一次亲自过问账目,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六疾馆的窘迫。
老妇人见江子萱不语,思忖一会吗,道:“小姐,你三年前遣人送来的那副临摹丘公的字画,无人能辨认出来,何不如以后都……”
江子萱蹙眉,曾经临摹老师的字画只因为老师生前答应赠送画作给一位向六疾馆捐赠钱财的善人,却因为病入膏肓无法兑现,她为了保全老师的名声,不得已为之。而现下,若是为了钱,她万万不愿意再做这欺世盗名的事情!
但,若是不做,她的画作只怕卖不到好价钱,对于六疾馆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
又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为何在一天内,她要面对两个作难的选择?
无论选什么,都不是她愿意的,都会有背上和无奈。
她难受的捏了捏太阳穴,起身站了起来,道:“我、我还是……先去作画,这事……以、以后再说。”
说着,她逃似的避开老妇人,拎着包袱几下窜到后院的房间。
春红自然是跟在她后面,见她心神不宁,遂有意转移她的注意力,道:“小姐以前常来这里?”
“没……小、小时候来过。”
“小姐如此作难,为何不向家人求助?”
江子萱摇了摇头,心里苦涩,若是向家人求助,即便亲如兄长,大概也是给一些丰厚的银两应付了她,能解一时之需却不是长久之道。
春红作难,也跟着她蹙眉,似是想到了主意,两个眼睛珠子溜溜一转,道:“小姐,你此番出来,家中无人知晓,想来大公子会很着急,不如让奴婢回去禀报一下?”
“也好。”
……
青山连绵,长路漫漫,官道上面军行如长龙。车辕滚滚,铁骑声声,尘飞马嘶、击鞭锤镫。
石尉寒躺在马车里,一手按着腹部,一手拿着前方斥候送来的消息,细细想着作战的方法。
忽然,外面传来一声禀报,道:“将军,后面有几个人好像在追赶我等。”
石尉寒蹙眉,道:“此次行军时间紧迫,不必理会!”
“这……将军,看对方阵势应该是京城中的贵人,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禀报将军。”
石尉寒思忖一会,道:“你率几个人前去问清楚,若是紧要的事情就稍后带人来见我,若不是什么大事便打发走吧。”
外面的人领命,马蹄哒哒向后面奔去。
石尉寒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继续低头看着斥候的探报和地图,这一仗,对于他来说至关重大,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过了半个时辰,方才领命而去的人回到了他的马车外面,道:“将军,属下有事要禀报。”
石尉寒不悦,道:“你说!”
“将军……这恐怕不方便明说。”
“停车,你进来!”
随着石尉寒话落,他所乘的马车缓缓停下,车舆帘子随即被人掀开,一个头顶青蛇髻的女子探头进入了石尉寒的视线里。
石尉寒的脸顿时冷了下去,低声道:“你是何人?”
来人抬首,一双美丽黛眉和杏仁大眼直直闯入石尉寒的眼中。石尉寒愣怔当场,这双眼睛,让他想到了三年前,初见江子萱时的情景。那时的她,也是这般,带着几分傲慢和灵动,硬生生闯到了他的世界里面。
“将军?石将军?”
听到对方的呼唤,石尉寒回神,因为这双眼睛,他的神色缓和不少,道:“你到底是何人?可知道行军是大事,不容得你儿戏!”
“我……”来人的双眼顿时被泪水盈满,脸色惨白得好像受了沉重的打击,嘴唇颤抖的问道:“我是长笙呀,难道将军不认得了?我是长笙呀,曾经你进宫,还与我说过话。去年,去年你班师回朝,我还亲自去迎接过你。还有昨天、昨天我也去了,只是一直没有见到你……”
对方说着说着,潸然泪下,配上哀戚的表情,显得尤为楚楚可怜。
石尉寒怔住,仔细想想,不确定的问道:“你是十一公主?”
“是我,是我,原来将军还记得,将军还记得……”长笙说着,连忙掏出巾绢将脸上的泪擦拭干净,双眼立时亮了起来,似乎有些欣喜若狂,道:“真好,真好……”
石尉寒所乘的马车是行军所用,只讲究速度,车舆比一般的马车都要小些,如今多了一个长笙公主,便是连空气也沉闷起来,使得石尉寒不自在的咳嗽一声,打断她的喃喃自语,道:“公主,你从城里追到此地,可是有什么要事?”
“我、我……将军……”长笙公主又开始抽抽噎噎,倏忽大哭起来,道:“将军,太后下旨要为我选驸马!”
石尉寒叹了一口气,劝慰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太后如此做也是为了公主着想,此乃好事,公主该欢喜才是,为何要为此而啼哭不止?”
长笙公主抬首看他,欲言又止。
见对方不语,石尉寒又道:“公主若是无事,还请返回京城,行军打战不是儿戏,公主乃是千金之躯,实在不该出现在军营里。传出去,只怕……”
“石尉寒!”长笙公主忽然高声唤他,而后不管不顾的扑到他怀里,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仰慕你吗?我仰慕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