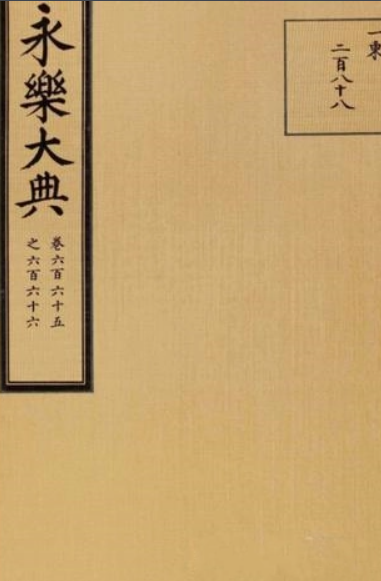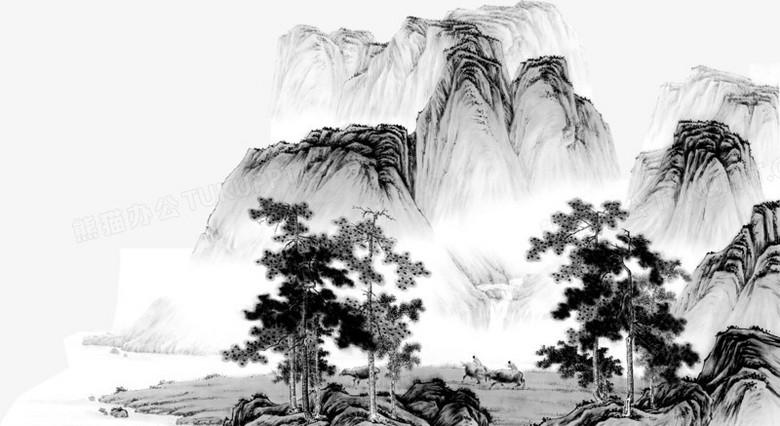仿佛久违的黎明,一夜天地陡旋、老却十载。天边隐约着一瓣瓣薄纱云岚、幻明幻暗,扯得尘寰伟丽高院里的宫灯莽莽苍苍、俯瞰这苍凉。
府邸还是先前那个府邸不变,只是八贝勒府变成了廉亲王府。八爷心下哂笑,可这心境却反倒前所未有的安然下来。争斗后,无论成功失败、谁胜谁负,横竖是历经了那般轰轰烈烈的过程;尽吾志而依旧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臣弟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八爷颔首,双膝一屈便掀袍跪落下去,似是周身绵软软的没有力气、又似乘风娓娓欲归。于此一顿,并没有等那金口玉言的威严皇者道一声免礼,自顾自的猛然抬首,“皇兄,臣弟虽是皇兄的臣下,但道理规章也不能不讲。”分明温润的语气里带着一股韧劲儿,可眉宇神情依旧是恭谦有加、挑不得一丝错处,“好歹皇兄要从我府里带人,纵然是陛下如此,也好歹得让我知道、得姑娘她自己愿意。”言至此处,语气陡然一转,变得略扬,“不然凭什么!”
今日一早,圣上突然摆驾廉亲王府,不由分说,为的便是带走云婵。顺理成章,八爷自不会轻易依顺他。纵然江山社稷陪在了老四手上,但一个人该有的风骨和气节,八阿哥从来都没有输过。
然而八爷的据理力争,最终只换来了龙袍着身的四爷一声冷笑:“就凭云儿是朕的女人!”
只这一句,胜过太多太多万语千言……简单明了的事情便如此明晃晃被摆在了面上,分明占了一筹先锋的事情,变得再也没了得以回旋的方寸余地;就如同,如同且走且观、维系经年的夺嫡大战一样让人无奈。八爷微定,张了张口良久无话。
便在这时,隐在云母屏风后的云婵突然走了出来。
顺着一抹深深交叠在一起的暗影,胤禛转目去顾她。
她身着一件镶着淡淡蓝边的白底点兰花旗装,却没有绾就旗头,及腰长发一半随意的在脑后绾了个髻、另一半散散风华的萎披在纤柔肩膀。整个人看上去清丽素净,大气端庄。
一别若许年,当初她跟了他时,不过取缔在桃李和花信之间的年华;眼下十二年了,十二年过去,她已三十出头。岁月的风霜在她身上斑驳了几度微凉,却没有带去那些美丽无边,只是眼角眉梢多了一层风霜。相比起二十多岁的年景,眼下的她显得更加成熟魅惑,相较起来竟是大相径庭的两种感觉,可顺眼顺心依旧。
审视其间,云婵已经冶步轻移,施施然的走至屏风央处,对着身系明皇至尊龙袍、似是要灼伤了眼睛的胤禛,如是施施然的行了一个规整礼仪,小口轻启、皓齿生波:“我愿意。”轻飘飘的字句。
她明眸一抬,迎向胤禛的眼光淡淡微微、不卑不亢,正如同她当初离开雍亲王府时一模一样。她又补充:“但在临走之前,我有话要跟八爷说。”这次的语气沉稳下来,因为平添沉稳,故又显得颇为严肃。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风尘其间,素衣化为缁的那一份恣意淡然之态,终究不会出现在帝王家吧!胤禛忽而便起了许多感慨,他知道,她该是怨他、甚至恨他的。这种怨恨不仅仅源自于自己付诸在她身上的伤害,还源自于时今这样悬殊的一种地位。君与臣的地位。
只是,只是……他的苦,她为什么就不曾愿意去着想一二?
普通百姓尚且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那么身处帝室皇族,又怎能不借风借浪一争高下?谁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世事如棋局局新、人情似纸张张薄……胤禛没有多说什么,看了一眼如是沉默的八弟,转身走了出去。
八阿哥一张面色没有变化濡染,唇边甚至还浮着一缕笑。这副如玉情态早在经年以前,便养成了习惯;看似不慌不乱,其实心下里许多无奈,从来没谁可以懂得:“有什么要说的?”他侧目凝过云婵,眼眸里温润的光韵跟着落在心里,暖洋洋的。
云婵眼睑动了动,迎着八爷将步子凑前几步。她轻轻笑开,言语间更多的还是冷静淡然。
这么多年过去,看过了太多、历经了太多、也思了想了太多太多,她已经学会了冷眼世事、斩断浮心乱绪的梳理出一份理性自持。理性的人看起来,似乎就显得有些无情、有些淡漠……一如四爷胤禛。
她启口慢道,言着自己既然早已经是皇上的女人、还为他生了儿子,那么此生此世到底都是要跟着他的;况且,我也实在没脸留在廉亲王府、更没脸去寻那蘅苑客栈关门后便断了音讯的掌柜的。只是有一件事,要相求八爷……云婵入宫一事,万不要让十四爷知道。不要告诉十四爷,永远都不要告诉。就跟他说……我已经死了。
言语至此,八爷点了一下头:“我明白。”他一早便一直明白。
以十四的性格,怎能让他知道这些?故而这些年来,关于云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一个字都没有对旁人道去半分。只有同八爷素来亲厚的九爷,在言语间有着几分猜测,却也心照不宣罢了。
云婵垂眸点头,复又扬了一下羽睫,缓缓启口:“我留了一封信,是给十四爷的。”她抬手从皂袖里取出那信,向八爷那边递去,水波目光定定的凝在八爷眉梢眼睑,“等十四爷回来,请八爷帮我交给他。”心里还是动了一下,难以自持。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或许一直都是八爷;从最初的救赎、到日后这近二十年来的纠葛牵绊,其间磨磨洗洗出来的这怀情感,早已深深扎根在了沙砾泥土之下,盘枝错节、撼动不得。可她想……她是不是,她该是,到底还是爱上了十四爷吧!这个问题有如一个压不下的妄念,在她心底里徘徘徊徊反复诘问了若许年。只不过,一切已都不重要了。
八爷一把将云婵搂在怀里。
突忽而来的举措猛然将云婵一怀游丝铮铮拉回;她颤了颤眼睑,将头伏在八爷肩膀,便那般感受着心与心间最为迫切的浓烈温暖。两颗心砰砰跳动,剧烈的韵律震得呼吸也觉窘抑。
良久之后,八爷憋出三个字,声音有些哽咽:“放心吧!”
稀薄的阳光打在身上,似乎顺着衣底渗进肌体、又顺着肌体渗进了寸寸丹心间。两人将彼此放怀,心间积蓄开了闸般难以自持。
青丝顺着风的势头被撩拨的乱飞乱舞,一些凄迷之态便被濡染、点缀的好处恰到。云婵整了整略乱衣边,后退半步,对着八爷霍然一跪,含泪磕头拜谢。
被云岚剪影渲染的有些昏暗的天光荡涤四野,目之所及处的景物便烘托的若了梦寐,一切一切看起来忽而那样不真实、却偏又那样残酷直白的真实如斯。
八爷没有阻止云婵,就那般默默受了她这跪身一拜:“这个辞行大礼,我领受了!”他沉眉颔首,定定的一句。即而曲身微向前倾,将她扶了起来。
世有渊明、菊花无憾;世有林逋、梅花仙鹤无遗;世有嵇康、琴瑟无憾;世有伯牙、子期无憾;吾汝一场相识、今生亦无憾也!
。
十四爷回来了。
没有鲜花着锦、没有空前浩大的列队相迎、没有得胜者的气宇轩昂金戈热血……没有,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这么一副空躯壳、一个孤凄凄的苍茫身影,只影向斜阳。
太突然,一切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不过几月光景,临走时皇父尚还威严森森慷慨以歌,怎么时今再面,竟只剩下一副冰冷的棺椁?他突然觉得自己在做梦,突然便觉得好笑。
晴天霹雳般的,他一瞬间呆住,那般不知所措、不明所以;恍恍惚惚间,他木木的按着新帝的旨令,把大将军印务转交给了派去接替的平逆将军延信,后立即动身回京。
但他才抵京师便被新帝监管控制起来,以防止他有所举措。直至景山寿皇殿拜谒皇父灵柩时,方才得以恢复自由。
万事已成定局,再难逆转些什么。十四冷冷哂笑,压低眉心冷眼着森森众人,并不对新帝行礼、更不叩拜。只是大步款款、扶灵而哭:“皇父啊,在子臣临行之前,您曾亲口对我说过,您属意的是我!时今不过寸月之余,您怎便舍我而去……”
立身于彼的八爷心下微叹,目光只是黯黯然一瞥,其间掺杂着太多无可奈何、又似凄凄悲悯。他了解皇父,知道十四弟是在信口胡诌,也明白十四弟此时哭灵绝非无心举措。
这时,有侍卫实觉不妥,近前想要打破这僵局,便抬臂欲将十四爷轻轻拉开。不想十四一拳便挥了出去,大发雷霆、恨声怒骂:“我是皇上亲弟,岂是你这么个下贱之人可碰的!”他红着眼睛一扭头,正对向良久默看、声息不见的胤禛,语气依旧跋扈忿忿,甚至带着些许威胁味道,“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立即处分;若我无不是处,请皇上即将那下贱之人正法,以正国体!”
……
十四大闹灵堂,遭到了雍正帝严厉的斥责,训他气傲心高、毫无规章。当即罢免了十四的大将军王,下令革去王爵、降为固山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