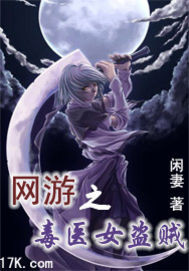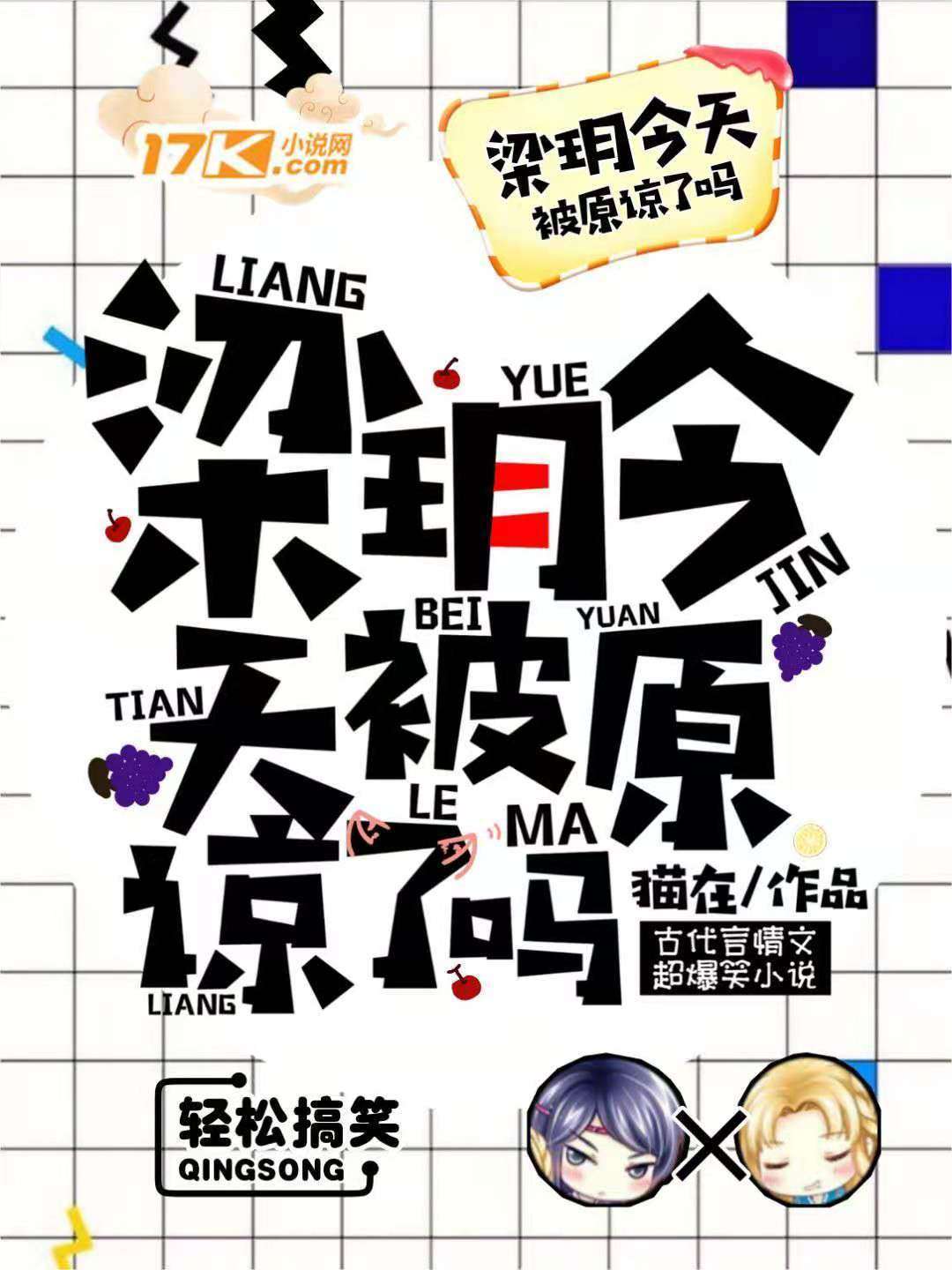萧萧疏风贯穿了一殿微凉,有什么东西似乎在这一瞬变得破碎支离。八阿哥便这样稳稳行前,绣着金丝蟒龙的皂靴点地极轻,每迈一步便仿佛踏在莲花上,但面上的表情却绷的紧紧、极凝重且深沉又隐痛的哀怅样子。
明澈的浮光在他开阔的肩膀周围笼着一层金色光环,在他身畔偏后处,一左一右跟着九阿哥与十阿哥,表情也是阴霾和不忿。
宏宏金殿在这三人走进来的一瞬间,任何声息顷刻便冻滞不闻。诸臣文武皆屏息凝神,不吐一字。中央高高架起的金灿龙椅上,端身威坐的四阿哥……不,现在应该改口称一声雍正皇帝了;胤禛抬头,火一样威严凛冽的目光向着那三个一身素服的弟弟们压过去,只是须臾,鼻息沉沉一哼:“怎么,见了朕,连行礼都忘了!”
一个“朕”字有意咬的极重极重,不是问句,分明训斥;与此同时,那些沉淀在每一寸骨血里的帝王威严便尽数流露无遗。他略扬首,目光满是不屑、又似乎还有一些弥深的莫测;他居高临下,展袖稳稳又闲适的抚着龙椅金棱,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一个强者的姿态……
心下薄薄一个自嘲,八爷没有言语、也没有动,依旧持着方才进殿时的那种目光,稳稳立着身子定凝着龙座之上的所谓“皇者”。
“敢问四哥,皇父他是怎么去的!”九爷沉着语气咬牙狠狠,冰冷森森的字眼似乎浸过了寒冬腊月里最坚硬的冰雪,“从十一月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三日止,皇父那里除了你四阿哥一人进出五次外,竟没有任何一位皇子大臣甚至后宫嫔妃见过皇父的面!”他抬臂拂袖,一把直冲着悠悠然把玩着念珠的四爷指了过去,语气劲劲然高扬起,“后来皇父突然猝死,是与你素日亲厚的隆科多传的消息!也是隆科多颁布的那道所谓遗诏!自畅春园往紫禁城宫内移灵时,又只有你四阿哥一人为皇父更衣、梳洗,乃至移灵的路上仍旧没有任何一位皇子大臣、后宫诸妃得在。”他阴霾的双目噙过一丝丝狠厉,忿忿哼了一声,牙关咬得愈发瑟瑟冷冷,“种种事实表明,早从十一月十日一直到皇父驾崩,皇父乃至皇父的寝宫内外早已被你完全隔离与控制!”
“放肆!”沉默经久的胤禛兀地击掌于案,陡旋而起的脆响在这气氛异常迥异的大殿里分外惊人。
“你怕了?”九爷却没有被这龙威昭著吓退半分,轻笑一声,反倒迎上了胤禛射在自己身上的那两道利剑般、恨不得把人活活撕碎的目光。
就这时,八爷转目低声喝止了九弟一声;老九方止住,又是一声讥诮不屑的轻哼,侧转向一旁去。
见九弟止住,八阿哥适才缓缓然抬目,对向金殿龙椅处的目光是那般不慌不忙。他曲身微微,行了一个素日兄弟见面时的家常礼仪,继而唇边扯过一道温润笑意,连同这出口的语气也都是极温暖柔和的,似乎那些不过是寻常谈心:“四哥,皇父大去,咱们兄弟心里谁都不好过,言语之间不免冲撞,请四哥见谅。”他复又把身子往前伏了一伏,让人不由便有了一种冰消雪化的柔软感动,恨不得做出最恭谦的客套、拿出最原始纯粹的真诚来开诚布公的迎接他、顶礼他。
这个人,该有多可怕……
八爷定了一下,开口接言,唇边那道浅然笑意流转不变,“请四哥拿出皇父的遗诏来,让我们兄弟几个看看、也让诸文武朝臣看看。”于此抬手,对着殿内文武环指一圈,沉默的人群里便在这个顷刻有了交头接耳的细微附和。八爷没有理会,负手于后继续接言,“这样一来,人心便可就此服帖、四哥也能名正言顺了。”无论从神情还是口吻或是措辞,你根本寻不到八爷身上的一丝不妥帖处,似乎他的本意当真便是求一个顺理成章那般简单。
顺理成章,可不就是顺理成章?可不就该如此!
八阿哥颔首,往后略微退了一小步,做的恭谦卓尔;唇边那缕浮着的笑在流转的天光之下竟带出点滴邪魅、脱似一只锦绣俊美的猎豹,又优雅的如了一只抿毛舔抓的晒太阳的黑猫。
“可不是?”十阿哥见八哥言完,得了老九的眼色后便出列一步,慢着声息、眉梢张扬起,“四哥,你拿出皇父的遗诏来让我们大家看看,我们立刻俯首称臣一心保您绝无二心!”语尽侧身挥袖,“诸位大人,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满殿朝臣窃窃私语之音更重,虽迫于天颜威慑不敢高声,但相呼相应之态也是难绝。
胤禛沉着一张冷锐无双的面目睥睨一切,他还没有着那至尊无上的大金色龙袍,但只一张龙椅稳稳坐着、那天家气派就已经极浓重了:“那是口谕。”他眉心压低,平心静气的没有半点挪移余地。他不乱,真的不乱,更真的不慌不急;事态发展至斯,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皇父的口谕?兄弟几个除了你老四以外谁听见了!”九爷转目狠狠接过话锋,于此突然想到些什么,又补充,“还除了跟你一党的老十三!”
“我听见了!皇父说他传位给四哥!”
辽阔的一嗓子来的太过突兀,莫说老九,便连龙椅之上端身坐着的老四也不禁循声去看。
那是一排年幼的阿哥,十七阿哥胤礼便在这时一步出列,扬起一张稚气忽浮的脸,跟几位咄咄逼人的兄长不卑不亢的迎对。
十七阿哥时今只有二十七岁,血气方刚的有点儿像当初的十三。
他分明是扯谎了。
或许十七是看见八哥他们对四哥步步紧逼,心里不忍,故而扯了个谎来向着四哥;或许只是灵光一闪,把心横下赌了一把、站了这么一次队……这都不重要,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他毕生里唯一这么一次站队,说的这么一句话,为他往后仕途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一锤……
簌簌兵戈铠甲交错碰击之声兀然划过耳膜,八爷心里一惊,权且顾不得理会十七这边,下意识猛一转身。
威严的汉白玉道那边涌来一对人马,铠甲生光、阵势巍峨。
领头的是一个粗狂跋扈、通身精气神的汉子,在他身边气宇轩昂、镇定稳沉的一并行进来的,正是十三阿哥。
“年羹尧护驾来迟,请皇上恕罪!”那汉子照直几步迎进,双手抱拳、铮然跪地行礼。
“年羹尧……”八爷心下一揪。恍然之间他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老四啊老四,这些年来我锋芒毕露,你却韬光养晦、小心翼翼没有一刻闲着。
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
兀地一下,八爷几近自嘲。他明白,这场对峙,他已毫无得胜的可能。
。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722年),爱新觉罗胤禛登基,次年改年号雍正。
在登基次日,即封十三阿哥胤祥为和硕怡亲王,并赐予“世袭罔替”,且总理朝政,又出任议政大臣,处理重大政务。
后又命八阿哥胤禩总理事务,晋封和硕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元年,命办理工部事务。
此外,后宫分封自不必说。但雍正帝生母德妃一生不肯移居太后所居的慈宁宫,并言“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直至去世,未曾对皇四子登基继位一事有过承认。
。
缎子般的溶溶金光拂过寸寸天地、拂过广漠江山、大好河山,缪缪天风依旧持着那个智者的姿态为六道一切做着神契般的洗礼。
这样旷古壮大的场景入在眼里,免不得让人起了诸多烦乱;十三低首一叹,心里空落落的。
他不久前去了趟蘅苑客栈,却找不到云婵。
天地骤变、乾坤翻转,短短时间历经了浮生太多事,他太累了、太乱了、也太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境了……以至于诸多一切叠加在一起,只是慌张、只是害怕、只是想哭,却又不得不迎头向前不容辩驳。
玉盏微响,身旁四爷抬目。他时今已经是皇帝了,金灿灿的龙袍辅配这一昆仑靡靡缎金色彩,很是相得益彰:“怎么了?”他的口吻尤是关切细致。
就算四爷登基称帝,他对十三的兄弟感情也不会有纹丝变化;相反,他还会尽自己所能,给这个弟弟更好的东西。
他长十三八岁,又自小一处长大,十三的算学、书法是他亲自教授的。小时候他走在前面,十三便像个小尾巴似的一瞥一瞥跟在他后面,手里抱着从四哥那里“搜刮”来的小物什,或许是几块糕点、或许是一个玉如意……他每走几步便总也不放心的回头去看看,生怕十三弟跟丢了自己;可十三弟聪颖如斯,可是伶俐着呢!
四爷的性子自小便喜怒无常,也不知是怎么养成的、从何时养成的,开心起来又说又唱、性子上来便掀桌摔椅,便连皇父都曾说他难当大任。可在十三面前,他似乎从没有那般过;也是,对着十三,又怎么能生的起什么气来呢。
那时的日子,真的极美好啊……
闻了四哥这一问,十三方抬首侧目,轻轻叹了口气:“没什么,皇兄,臣弟很好。”碍着君臣之礼,许多心事还没出口便已觉寡味。他抿了一下嘴唇,到底终是绷不住的轮换了亲人之间的家常姿态,接口补了一句,“我想寻一处清净的地方。”他微微苦笑,眉心蹙了起来,兀自回忆、兀自纠葛,“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有那种感觉。可偏偏就连那个地方,也物是人非……”
他言的那地儿,是蘅苑客栈。
时今的蘅苑客栈门前荒草哀哀、蛛网薄薄结了一层又一层。莫说云婵,便连那个一脸褶子的胖掌柜的也不见了影踪。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这一席话,也戳到了四爷心里的痛。
经久无声,胤禛面目微有动容,然而很快,便凑化成了一笑泯恩仇:“十三弟。”他拍拍十三的肩膀,缓缓而道,“江山都得到了,还去计较那些失去的东西做什么呢。”于此一沉,他的眉心霍而压低下来,一字一句,缓缓的,“江山,是我们兄弟两人共同的……”
十三垂目,心下脑中却觉空落落的。
得到、失去,失去、得到……聚聚散散、浮浮沉沉,生命不息便纠葛不止,其间烦心燥意事几多呢,从没谁可以挣脱得了过。然而日子,却总是要向前走的,向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