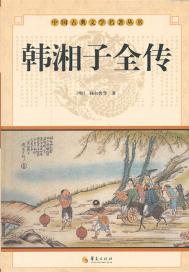一路冶冶的赶过去时,早有公公传了话遣散了一班闲人。
康熙皇帝并没有摆什么阵势,只穿着一件简简单单的粗布马褂、青黑皂靴,俨然微服出巡的行头。
心念迭起,八福晋曲了身子便要请安,被康熙按住。
她是个极聪颖的女人,微扫一眼便已了然端倪。心明白皇父此行是不愿太多人知道的。故不再多说什么,只柔然起身,把皇父谦谦引领进了八阿哥卧病的里间,俄顷遣退其内一干人,后放好帘子退了出去。
淡淡天光包裹着淡淡的景深,溶金生波的内室里,便只剩下这对太多太多恩恩怨怨、纠纠葛葛了半生的苦心父子……
康熙不动声色的向着卧病在榻的儿子那边走近,随着距离的不断缩短,他终于可以看清那个被他一手缔造出的颓颓然残躯病体。
时今的八阿哥早已经憔悴不堪,分明那般剔透可人的冠玉面庞竟消瘦的有骨骼轻微凸起;他阖着双目、紧紧锁着两道眉头,枯槁泛白的嘴唇犹在喃喃。
看在眼里,康熙心里一动,不由落身于榻、向前倾倾身子,终于听清了儿子口里喃喃着的那些残章断句。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般对我……”
“额娘,您在哪里?您真的已经看开一切、超然物外甚至超越轮回了么……您不再要我了么。”
“额娘,您看到了吧!他们容不得我,通通都容不得我……您在世时他们不敢动我,您不在了,凭谁都敢欺负我、讥诮我……”
就是这么几句话,反反复复不断重复。八爷睡的并不踏实,就算身处梦境,也依旧拼命忍受着冰火两重的苦苦煎熬。
究竟是谁,是谁这般的造就了这空躯壳?究竟有着多大的怨忿、多深的执念,多绵长的熬耗心魄放怀不得……字字句句俨如最最残酷的带血利刃,就这般浅浅淡淡间,犹如寸寸闪着寒光的匕首生生刺进康熙心脏里。
父子之间因血缘而起的那股天性驱使,康熙抬手,颤颤的往前伸过去,想要抚平儿子那两道铁一般紧紧纠葛在一起的眉弯。却在即将触及的片刻停住。陡然而起的惧怕让他不敢再前,因为这个孩子眼下是这样的憔悴支离,仿佛这世界上最脆弱的水晶,似乎只消稍稍一碰,便能在顷刻间让他瓦解成灰……
“胤禩,皇父心里的苦,你又怎么懂……”康熙徐徐轻叹。抬起的那只手僵僵的停在半空,须臾后,终是轻轻探了一下八阿哥的额头;滚烫的温度直唬得人心里阵阵发麻。
感觉到了有人探过额头的微小动作,八爷下意识的**了一声,缓缓睁开双目。目光却是如此混沌、如此迷惘不堪……
康熙有片刻的失神。病榻上这个秋风里折了双翅的蝴蝶一般萎顿支离的人,还是他的八阿哥么?是那个永远都是一副端雅高洁、举止卓尔,永远都能够在唇畔捉到一丝和煦微笑的风一般的俊逸皇子么……
“这个梦怎么还没有醒呢。”八爷溢了一丝自嘲苦笑,旋而极其费力的侧了侧头,“竟然……梦到皇上了。”
康熙没说话,就那么默着声息听他自顾自的絮絮叨,边把锦被往他肩头提了一提、顺着脖颈的缝隙掖的紧实。
不过八阿哥却再说不出一句话了,因为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病痛令他求生求死极不好过,竟日连天被折磨的冷汗涔涔、咬牙忍痛。辗转经久,终于勉强又是一句:“真是个……奇怪的梦。或许也只有在梦里,才会见到他吧!呵。”他轻哼,“那个人可真是吝啬,就连梦境,都鲜见的入。”他碎碎吁气,竟是笑起,“原是我执着……我横竖对皇上来讲,都是个无关紧要的。”
康熙这才察觉到,至始至终,他唤的都是“皇上”、而不是“皇父”。
天颜竟把他骇的连一声“皇父”、一声“阿玛”都不敢再唤了么!还是再也不屑这样的称道?
三十余年,整整三十余年的父子情分啊!真真便要在这一朝尽数斩断、再无羁绊了么!
很多个无人的静夜,康熙会忍不住的想,自己这样做究竟是错了、还是对了?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让这个孩子得到什么、又让他乃至让自己让薇儿跟着一并的失去了什么……辗转反侧、纠葛折磨的脑仁儿生疼,不知不觉便又是一朝虚白天明。
米色湘帘兀然被人掀起一角,不大的动静还是扰乱了眼下这一室静谧。是八福晋。
她是一个极会识人心思的女人,她的玲珑内慧并不比那难以估量的深潭涧水浅得了多少:“皇父,贝勒爷该喝药了。”她淡淡,眉宇间噙着一抹哀色,迎前便要将那端在手里的药碗稳稳放下。
半道被康熙截住:“朕来。”这位高伟的皇者从儿媳手里接过药碗,复示意她退下。
八福晋一张微白面目没再有什么情绪轮转,她淡淡然行了一个严整的礼仪,旋即莲步退出。这一碗药,送的真是恰到好处……
儿女心思几多做弄,横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康熙皇帝没有计较什么;他是真的老了,再也分不出多余心思来跟孩子们较劲。他用小勺搅了搅碗里的药汤,搂着半昏半醒的八阿哥,一勺勺喂他喝下。
那般小心翼翼、细致入微。在这一刻看上去,没有帝王皇者、没有天家隔阂,有的只是一位心疼孩子的慈祥老父。他是一位苦心的父亲,是全天下最苦最苦心的父亲,一直都是;可是有很多心思,偏偏又都不能说,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说……
阳光晕波、香榭荡漾。
这天,父子两个倚靠在一起说了很多话。
康熙想要撕裂儿子那张戴在人前的温润面具,十分迫切的想要看看那面具下面有着的究竟是怎样一张脸,一张从没有示人、即便他的生身母亲都不曾见到过的,最真实不过的脸。
八爷有些恍惚,他分不清究竟是梦寐还是现实。横竖半深半浅的伤、半真半假的谎。他就那般靠在皇父的怀里,似乎对着一个梦寐尽情抒发。他笑,肆意无边的虚脱狂笑;他道着那些过往点滴,一桩桩一件件的绵绵道着。忘不了,至死都忘不了!
“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礽……锁系,交议政处审理。”
“辛者库贱婢所出……革贝勒。”
“诅咒生父,阴险狡诈,罪有应得,自作自受,父子之恩绝矣!”
“生命垂危有罪,勒令移宫还家,停米停俸……”
“罢了,罢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雷霆雨露具是君恩,我爱新觉罗胤禩还血还肉还了这一条命,也偿还得过了!”
绵绵呓语起落间,康熙听的一颗心都空了。铁血铸就的过往前尘就被这样明晃晃的掰开了、揉碎了的摆在他面前,那般条理分明、黑白清晰。他无言以对,他从来都不曾回首去看看曾经走过的父子情路,故而他从不知道原来他在有意无意、有心无心间,居然已经把这个孩子伤的这样深、这样彻骨……这一通尽情的发泄过后,他会不会觉得好过一些?
这边八阿哥没有缄住言话,谵谵呓呓,面目却一直都是噙着微微薄笑的。沁着破裂唇角处渗出的微微血痕,那般触目惊心,灿灿然若一道绝美罂粟。然而这笑看在眼里却不觉讥讽自嘲,反倒更像一种超越世事、荡涤人心、洗尽铅华的大彻大悟。
“即便只是一场梦寐,也是有知的吧。”许是想的乏了、念的累了,八阿哥长吁口气,反倒展眉了,“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若是我的错,是不是错在从一开始,我便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往皇父厚实的怀抱深处又靠了几分,似是那样贪恋此时此刻的暖暖温度,“额娘她那么好,为什么要那般作践她?究竟是因为额娘的缘故而看我厌嫌……还是因为我的缘故,而连跟额娘之间的那点儿情分,也生生作弄的荡然无存?还是如额娘念叨的那般,是你们心虚了?”他缓了一下,依旧是极有气无力的,俨若梦魇,“无论怎般,我的身体里都流着爱新觉罗家的血,与那个人如出一辙、一模一样的血。风刀霜剑划过我的身体、溃烂掉未及结痂的伤口处的寸寸皮肉,他就不会痛么……他就不会痛么。”霍然一下,八阿哥似乎拼劲了孱身上下所有的力气回笼于胸腔,着重语气,言的狠绝、一字一句,“我好恨,我、恨、他!”不过须臾,终是颓颓然垂首呵笑,整个身子重新瘫软下来,只是无力,“可是,我却又那么那么的爱戴他……”
就这般默默倾听,康熙已在不觉间红了一双苍苍老目,心下塞堵、头脑冗沉。良久良久,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拥着儿子的怀抱继续往里紧了一紧。
。
临近年关时,康熙皇帝恢复八阿哥银米供奉。
随着时日不断推移,八爷身体日益好起;只是八爷一党就此大伤元气、圣眷寥寥。行路若撞见旁人,总是垂首绕道、躲避而行……
冠玉一般剔透优秀的男儿,润玉一般温文卓尔的贤王;只道他平易近人、识礼周成,却偏又铮铮竹节、高傲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