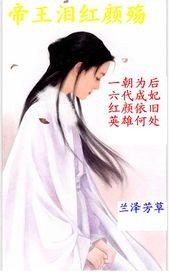踏着剪了清辉的月华如织,胤禛负手于后,一个人茕茕的踱行在午夜最冰冷的回廊小道上。他的身影清冷依旧,覆着一层冰霜的面上满满的都是冷峻;在临着偏院厢房一角的同时,他回身喝退了尾随身后服侍的小厮。然后闭目,长长的吁气落在唇齿间。
仿佛已经过去了太多的时日,这是人心的隔阂,滋生出的时空的错觉吧!
夜已经入得不算太浅,但云婵还没有睡。自打入得雍王府后,她的作息便被完全打乱。
虽然不过小一个月的身孕,身形还不算太显山露水,可时不时袭来的害喜反应依旧够她受的。且如今形势与以往大不相同,一天天的她没多少时光是得着安宁的。后来白日里有了云微陪着,过得倒还好些,可每每到了一个人的永夜,她那怀强自按捺下去的散散乱思便会飘忽的又高又远……原以为自己这一颗心已经成了死灰,又为何依旧还是会有那样真切的惦念?甚至,疼痛。
她放不下八爷、放不下十四爷、甚至放不下曾经那样让她恨得牙痒痒的九爷。
她离开的这些日子他们在做什么?会念起她么?她微笑,会的,或许只是在下棋亦或品茶的时候,或许只是在那么极清闲的时候,他们会极随心的顺口道句“小婵那丫头眼下在做什么?该是沉醉在亲人重逢的喜悦中快意的不亦乐乎吧!这个小没良心,去了大几天的都不见往回稍来半个报平安的字迹,怕是一见了自己的亲人啊,便把我们给忘了干净……”念及此,她心口忽又揪了一下,忙手抚心口徐徐碎碎的喘着虚气平复。
月华如洗、疏影交叠,四爷就在这个时候一步步走到门边,屈指抬起,却僵僵的停在半空始终没有落下、亦不曾收回。
溶溶的烛火映出他一圈乌尘影像的轮廓,在夜的浮光下,烘托的清冷而干净。
云婵无意识的一侧目,刚好瞧见了门边木格子页扇间的这圈依稀人影,下意识的拿捏,她皱眉厉声:“谁!”
良久无声。
这么烛火幽幽、夜风阵阵的,门外便那么静静然立着一个沉默的人,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会被实实吓着。云婵心下骤惊,一股后怕紧贴着划过脑海;偌大一个雍亲王府她并不太熟悉,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莫不是……进了歹人?念此不由一声惊呼脱口而出:“姐姐,有贼!”才出口的惊呼,她自己都吓了一大跳。这一次不是因为门边立着的那个歹人,而是被她自己的下意识给唬住。
云婵跻身的这处小小院落平素没有几个专程伺候的下人,轮班的那些基本没有不偷懒的;而云微的院落跟她纵然隔得不远,也是断断听不到她眼下的这声唤。方才这声“姐姐”,完全是出乎了她的下意识。不知不觉间,她竟把云微当作了她唯一的倚靠啊……
“姐姐?”四爷心下奇怪,不由皱了一下眉头暗自嘀咕。
意识到了那声呼唤根本没有效果,且这么皓月清风的永夜里根本寻不到一个人影。云婵那股浓郁的惧怕愈发深沉到化不开。这歹人若对自己行凶,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到底会是吃亏的那一方,且吃的还是大亏……灵光一闪,她蓦然有了主意。
半晌寂寂后,云婵有意把那嗓子娇柔几分,佯作与男子盈盈撒娇的小女儿调子:“四爷,外面有人呢,莫不是哪个下作的歹人?”边这么装模作样,素指顺势擒了案上一只青瓷花瓶牢牢抱住,想着万一那歹人没被自己吓退,硬冲进来时,可以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爷,你说你要出去擒贼?”她又将那调子高高扬了几分,明明媚媚全是底气,“好,妾身还没见识过爷擒贼的手段呢!刚好让妾身开开那眼……”这底气明显是装出来的。她就这么一边一唱一和的兀自演着双簧,一边偷眼悄看门口那贼人被吓走了没有。
胤禛先前听了云婵那句唤的煞是悦耳暧昧的“四爷”,心下铮地一喜、后兀地一下陡然奇怪;但又往后听那一干接连,才知这个蠢女人是把他给当成了歹人,佯作自己就在她屋里,想用这个老掉牙的法子吓退“贼人”。
念及此,他没忍住噗地一笑,这个女人演的还真是像!
却说云婵这边偷眼瞄了半天,愣是不见歹人有半点吓退的趋势;干脆抿了一下薄唇,一不做二不休的唤的愈发暧昧百般:“四……”
“别装了,是我!”
胤禛的声音赶在这个空挡忍不住的喝出来。
霍然一下,云婵身体僵硬,怀里死死抱着的那只青瓷花瓶“啪啦”摔在地上,清脆的声音震得她耳膜轰隆隆闷响,接连只觉整个脸颊都是火辣辣的升温滚烫……她到底不了解胤禛,没有办法单靠一圈轮廓、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便将他辨认得出。
屋里屋外具是少许的沉默。
须臾后,四爷咳了一声打破这尴尬:“……开门。”他张了张口,一时想说的话有很多,但真正出口的句子只有这简短的两个字。简短,但简洁明了。
他让开门……云婵懵在当地。这是他的府邸,自己是没有理由不照他的吩咐做事的;但……她抿抿檀唇,将方才那怀乱绪渐次平复下来,再出口的语气已经恢复了素日里的冷然淡泊:“奴婢睡了,四爷请回吧。”不加情态。
这话听在耳里横竖都是惹人发笑的。胤禛暗叹。
永夜汩汩的天风扑在身上有些刺骨,蒸凉叠生间,他心下涩涩。哪里有男女夫妻以这样的理由来做搪塞?况且那个女人她做的真够决绝,便连一句夜深了、当心受凉的话都不屑对他唠叨……
“夜深了,爷快回去吧!当心受了凉。”
才念及于此,云婵如是淡漠的一句补充忽在凭空里幽幽荡起。
胤禛心下一怔。
算是心有灵犀么?
轻微的恍惚陡然斑驳了半壁心房,他苦笑,但旋而出口的字句却是一贯威严凛冽不减半分:“呵,你不是不怕死么?怎么还那么惧怕一个歹人!”这句话分明带着几分讥诮不屑;只有胤禛一个人知道,他的本意其实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四阿哥,是一个面冷心热、内涵渊深的人。有些时候,他仅仅只是不善于在女人面前表达一些情态;又或者是天性如斯,能表达却不屑于表达。
迂回的穿堂风带起了夜月的寒凉,自外向里不断萦绕。云婵鼻息薄吁,眉目淡淡,绯色唇瓣竟是笑起:“奴婢还有未尽的义务,又怎么能死。”她这句话回的浅浅的,一时半会子那般难以捉摸,更是不知悲喜。
一门之隔,隔断两处景深、两种迥然不同的郁郁心境。
“未尽的任务”?她把一切都当成任务,只当成任务……这是她的真心话么?是么?
胤禛没有动,也不曾言;云婵便在这时将身前探,呵的一下吹灭了垂着泪花的溶金红烛。
黑暗,屋里屋外整个世界顷刻进入了无止无尽的浓浓黑暗,肃杀的气息迅速将方寸大的地界吞噬、围拢的几近窒息。
明明灭灭的星子在浮云聚散间,忽地遮住、忽地又显现。夜深如水、更漏绵长,四爷又那么默立一阵,觉得愈来愈无趣。他将那停在冰凉门棱处的手指紧紧一收拳心,重新展袖负后,稳稳然转身,踏着浓厚夜露一步一步离了清冷萧条的小小院落。
我们之间,当真连一星半点妥协的契机都不能有么?
他是皇子,是雍亲王,他的生命里有过太多太多的女人,睡一个婢子谁人敢说不是顺理成章!偏偏这事态为什么竟……竟会被衍化的这样复杂!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搞不懂。
一路阔步稳行,四爷的眉目随着思绪渐深而变得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冷冰冰,这使他看上去更多了一种坚韧残酷的迷人魅力。这样一位心机深沉、不苟言笑的铁面亲王……
昨天的街,刚刚扬过初春的雨,那些蛰伏在地表尘泥里的泥土特有芬芳气息,跟着迂回穿堂夜风一圈圈涣散在周围。
一派不见五指的黑暗无边里,云婵缄声独坐,面无表情。这副神情倒跟四爷那般相像,越来越相像……云婵啊云婵,方才你是给自己留有了一处余地么?她暗叹。
到底,还是没有跟四爷彻底撕破脸的把事儿做绝、把话说绝……
她不是君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为了活而活的辛苦小心、心机渐次变得深沉下去的弱小女人。
大千世界、千难万苦负尽了千般罪、历尽了万重难,归根结底为的无外乎是那“生存”二字。尽管这样辛苦的过活不死,真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或许,这便是人吧!果然是愚蠢又滑稽的凡人啊……
总道浮云解聚散,昨日的夜,梦寐阑珊不告而别了谁;浮生韶华、过往种种,一时间静得闹哄哄。
了却了往昔的美好,去收拾昨夜的残梦;夜半笙歌、风沙迂回,总是月难成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