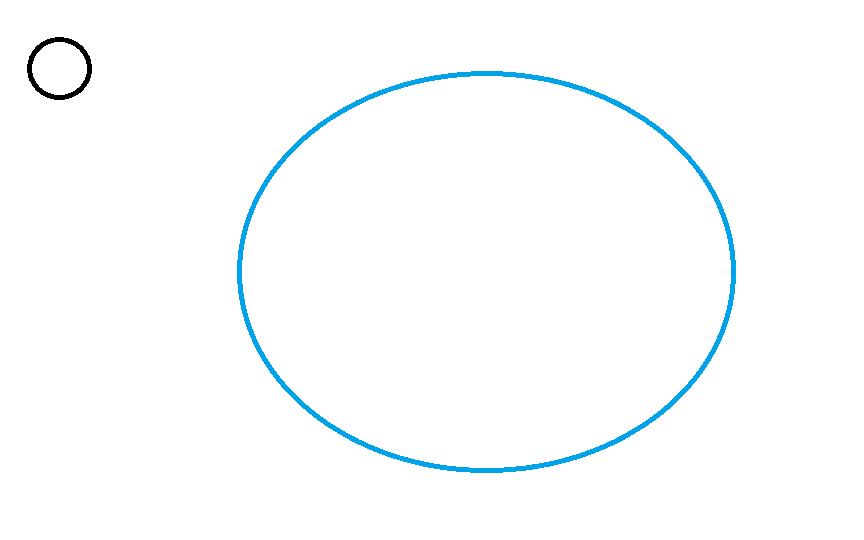一个人必须记住,在经济领域里,一个集体的目标之一就是尽一切可能取得垄断地位。
对于数以万计的暴风星系人来说,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大萧条,也被无可非议地称为“浑浊的三、四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凋敝、银行业破产、技术和工厂业倒闭、矛盾激烈的罢工运动、农场种植业的废弃、等待救济的流浪游民无家可归,惨状遍布大小城市。这个时代阴云密布,危机最为严重的831年,约有七千多万人被解雇(约为整个星系的35%)。
但是,新生的泥泽邦团伙却没有经济之忧。这个十年是它们即将延续到下个世纪的空前繁荣和倾力合作的开端。在859年召开的泥泽邦高层帕维亚秘密会议上,富有远见的罪案天才乌利亚·尼希米为几十个现存泥泽邦奠定了相对合理的基础,而这些团队即将利用它来构建非法产业的网络。
作为现代星系泥泽邦创建大会的与会老板之一,加利佐·斯福尔扎对尼希米出色计划所开创的长久和平感到由衷地高兴。“在城堡之战结束后的近三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发生过损害泥泽邦团结的内部斗争,也没有出现威胁集体或我本人的外部干涉。”斯福尔扎在自传里用惊讶的口吻写道。
尼希米的管理革命意在构建层层堡垒,以期在班子成员进行犯罪行径时,能有效地保护和隔离自己,同时也能使其他老板避免受到牵连。因此,每个头目或教父都将从集体的罪案生意中获利,却不会有遭到控告或监禁的风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希米的计划是要保护绝大多数通道老板,但他自己却是他那个时代被长期监禁的唯一一名碑界地区船番人。
药油萃取物禁令是把三十年代的街头帮派转变为平稳运行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罪案团伙的催化剂。像尼希米、斯福尔扎和贡扎加这些人最初都是不入流的暴徒而已,后来才逐渐转变为泥泽邦船番人的巨头。生产和贩运私药让他们在危险环境中得到了实际的管理历练,教会了他们如何筹划运作复杂的系统,来制造、运输大批量的违禁私药萃取物。尚处在二三十岁的年龄段,在把资深贩子、货车驾司机、装卸工人和安保护卫队整合成一个罪案团伙这方面,这些新型的船番人俨然已成了老谋深算的行家里手。年轻时就暴富起来的船番人则熟练地利用洗钱活动来避税,还很快学会了如何贿赂和操纵当局政治和警方侦探,来化解让人头疼的执法难题。
帕维亚会议取得了成功,权力布局也已到位,全星系的泥泽邦头目们达成了至少表面上的默契。他们都同意每隔四年就在星系罪案会议上聚集一次,以进行友好交流、探讨共同担心的问题,这很像一个政党或宗教教会会议。
尼希米和斯福尔扎那新班子的内部实力也得到了扩充,这是城堡之战的一种副产品,即高伤亡率的战斗对支援需求所催生出来的结果。而尼希米计划和管理委员会联合星系所有泥泽邦团伙时,在成员资格的规定等方面仍然存在区域性差别。加利佐·斯福尔扎拒绝响应将其巢穴作为所有塔图因人融合之地的建议,他坚持说,只有完全的博洛尼亚血统才能忠实于星系泥泽邦的文化和责任。
有意思的是,所有家族都不同意用泥泽邦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碑界地区各团伙启用了“咱们的事”,帕维亚团伙称自己为“团队”,波坦察团伙则选用“扶手”。新奥里斯塔诺团伙偏好听起来比较中性的“代表处”。
最后,在团队中确认船番人身份的最普遍方式,就是那个简单的措辞:“他有关系。”
当泥泽邦代表们散会离开帕维亚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药油萃取物禁令那取之不竭的印钞机器,已经处于即将寿终正寝之际了。大部分民众和绝大多数政界人物都希望废止这部法律。因为在他们这些人看来,它既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又非常不得人心,而且特别容易致使执法机关滋生普遍的腐败。对于867年暴风星系**尼古拉斯·塔勒布的新一届政府来说,持续恶化的大萧条为它提供了反禁令的另一个理由:支持废止该法律的一些实力人物声称,他们将复活合法的萃取产业,并能创造数万个工作机会。
968年12月,第二十二修正案正式获得通过,废止了禁止生产药油萃取物的第十一修正案。近三十九年干旱期结束的第一个夜晚,碑界地区数十万药油萃取物的客户涌到萨佩洛广场上,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大规模人群甚至需要紧急动员全区域所有数万名安保人员来维持秩序。
碑界地区五大泥泽邦团伙为这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做好了准备。禁令慷慨地让他们迅速暴富,所以他们有充裕启动资金为新的非法生意来提供经济支持,或者干脆从其老仇家曼图瓦和法哈德团伙手中抢地盘,有个关于泥泽邦资金来源的例子,电影制片人福特·奈布哈尼称尼希米曾告诉过他,835年他单单从私药贩卖生意中就赚得了超过两千万马赛的毛利润,再扣掉货运和安保队伍的成本、向执法机构和特工行贿的费用后,净利润依旧接近一千万之巨。
禁令刚刚废止,碑界地区泥泽邦就在享受各种形式罪案活动的盛宴:赌桌经济、资金借贷、情色淫业、恶性药物交易、货物抢劫和彩票发行等等。“分割式社交”成了代指泥泽邦这些行径的流行语,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前两个世纪的奥利斯塔诺,确切出处不得而知。不过它通常的含义是大声吵闹喧哗、兴奋放纵或狂欢作乐。在上个世纪中后期,这个词开始指曼图瓦裔暴风星系人举办的私人聚会。为了资助他们的“分割式社交”,班子成员就要求商贩和周围的居民掏钱捐款,否则其财产和生命都将面临威胁。
“诈捞人”是纯粹的星系标准语造字,或许是某个新闻记者为指代三十年代标新立异的泥泽邦船番人而杜撰的新词语。
后药油萃取物禁令时代的船番人借用了一种已消失的手法,注册假冒的“安保服务公司”,穿着整齐、拿着仿制的工商注册证书资料,对店铺和餐厅老板声称,有他们保护就能让在深夜里恣意纵火和破坏的街头混混有所忌惮。凡是不信任他们的身份、不愿意委托他们来保障自己的店铺餐厅,经常不是窗户玻璃被突然砸个粉碎,就是在夜深人静时被投掷熊熊燃烧的火把。
有意思的是,这些虚张声势的船番人,还故弄玄虚地挑选了几个只能忍气吞声、与之配合的老板,称其为生意合作伙伴的典型成功样板。这些老板主要经营机械电气维修、食品零售、公寓旅店和能源服务为主。船番人先教会他们背诵好编撰的说辞,诸如“安保服务公司”帮助他们消除了勒索和报复给生意带来的麻烦,迎来了安定,每当他们准备去新的店铺推介其“服务”时,都要拉上这几个“演员”。当这些船番人无所事事空暇休息时,就盘踞在这几家店铺门口,与匆匆而过的路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看起来是整条街唯一凶神恶煞般的存在,是真正让生意难以开张的关键原因。
碑界地区的法哈德泥泽邦,则在其占股比例相当高的服装中心市场创新了产业敲诈的技巧。在二十年代罢工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法哈德泥泽邦曾受到 产业活动中多方的邀请。他们既破坏罢工,来为工厂股东们服务,又充当暴徒分子,受雇于有权势和大规模的工会,来胁迫工厂经营方就范,同时又在团伙运动期间受雇于工厂,到那些空出来的人力岗位去上班,分化罢工运动的威力。
当对抗运动基本偃旗息鼓时,这些曾经为双方效力的船番人则用威胁手段挤走其他人,自己留下来加入到工会和管理协会中,发挥他们自己的影响力。通过与工会领导人相互勾结,这些法哈德泥泽邦敲诈者就频频威胁停工,和煽动工会化运动,来向工厂股东业主们开出各种充满了欺辱性质的勒索条件,包括在工厂里开办泥泽邦控制的商店、让泥泽邦成为供货商等等。一些船番人干脆用武力手段挤进公司、成了秘密股东,从老板那里索取报酬。
在禁令时期,乌利亚·尼希米是唯一和法哈德泥泽邦保持亲密关系的教父。他没费多少力气就把法哈德在服装中心市场的生意吸收到自己的领地中。服装业是碑界地区最赚钱的生意之一,在这个行当里,法哈德暴徒成了尼希米的小兄弟。据从不曾与法哈德泥泽邦打交道的斯福尔扎说,在三十年代中期,尼希米是服装行业的船番人老大。“尼希米对服装这整个行业,特别是对服装工人联合会有着广泛的兴趣。”斯福尔扎后来写道。乌利亚·尼希米提议把斯福尔扎的人安排到联合会中的重要职位上,而这个联合会是男装和童装生产行业的主要工会。假如一旦在工会中掌有了实际权力,斯福尔扎就可以像尼希米那样,控制关键人物、随心所欲地拟定工会的合同条款,分享工厂的酬金。
但是,尼希米的提议,却被礼貌地回绝了。因为斯福尔扎不想因为另一个团队而承担责任。想要独立施展拳脚的斯福尔扎还有另一个不错的理由:他自己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服装业工会——国际企业服装工人联合会有着联系。
像碑界地区其他老板一样,斯福尔扎有许多传统的生意活动让他忙碌不停。他接手了包括三家服装厂、一家星系货运公司、多家高端洗衣店品牌和奶酪生产厂。另外,在弗罗西诺内区还有个斯福尔扎殡仪馆,有人怀疑,这里其实是处理被家族谋杀的受害者的地方。据称富有创造才华的斯福尔扎曾使用特制的双层棺材,在已登记的尸首下面,留有一个秘密隔间,这样可以同时掩埋掉两具尸首。他拥有的企业可作为生意收入源源不断的借口,足以应付税务稽查,并为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依据。
斯福尔扎那潜在的资本主义哲学,植根于一种指引着他和其他老板不断前行的基本理论:排除所有竞争。“一个人必须记住,在经济领域,一个家族团体的目标之一,就是尽一切可能取得垄断的地位。”他在《妥当》中写道。
除了服装业,运用高压手段和在工会里的影响力,五大泥泽邦还染指了许多其他经济实体,从中勒索报酬,如弗罗西诺内区的码头接驳装卸服务公司、贝内文托水产品市场、乌迪内和弗罗西诺内的肉类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筑和运输公司,以及酒店餐厅等等。
在每年五个亿马赛的合法鸡肉生意中,博洛尼亚-塔图因泥泽邦甚至会迫使法哈德“诈捞人”放弃了其拓荒者的江湖地位。碑界地区大量的法哈德人口及其饮食习俗保证了对家禽产业的稳定需求。法哈德暴徒们满足于简单而过时的诈取保护费的手法。他们只进行一些小额的敲诈活动,目标是那些害怕受到伤害、没有防卫能力、竭力以求自保的公司。在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推动下,泥泽邦有了更多的宏伟计划。贡扎加的爪牙们抛开其法哈德同伙,运用后来成为敲诈生意经典模式的手法,促使一批活禽供应商、批发贩子和屠宰工场建立了同业联盟。贡扎加甚至成立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假冒贸易集团“碑界地区鲜活家禽商会”,然后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大多数合法的鸡肉企业参加进来。为了遏止自由市场的竞争,价格也被定死了,每家公司都会被分配一定的市场份额。作为回报,公司依据销售总额向泥泽邦的家禽商会缴纳会费。毫无疑问,因为成立了同业联盟,贡扎加捞到了大量不法收益,同时还堵死了新的公司参与竞争的道路。而那些上缴部分利润的联盟成员,只需提高些价格,这部分“罪案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
在他们所控制的行业内部,从服装批发档口到货船码头接驳区,泥泽邦还从非法赌桌生意和借款放贷中进一步谋取利润。
五大泥泽邦不允许存在竞争者。在他们寻求绝对控制权的咄咄攻势面前,法哈德和曼图瓦的泥泽邦并未进行多少挣扎和抵抗,尽管在私药禁令期间他们都曾有实力强大的团体。即使对三四十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哈德家族大佬赫伊里·卡米勒来说,他的绝大多数计划都需要事先取得其他泥泽邦伙伴班子的同意。卡米勒陪同尼希米参加泥泽邦大会,但却从未被允许坐下来商讨问题。
在泥泽邦接手之前,二十年代当之无愧的法哈德罪案大师,即纳吉布·海迈姆。他那涉及面广泛的罪案活动,包括国际私药和能源贩运、劳工诈骗、证券股票价格陷阱欺诈、珠宝和债券销赃、毒品走私、赌桌操纵和洗钱。
海迈姆的传奇之作是策划了819年世界职业网球锦标赛的“黑血丑闻事件”。在这次赛事中,夺冠势头最猛的帕威亚“铁拳队”被里沃诺“雪山队”击败。被称为精明人士和“大投资家”的海迈姆是个面容和善、言谈温软、衣着光鲜的人。他的权力由一批生性残忍的亲信来行使,拜倒在其门下的包括一群法哈德和塔图因泥泽邦的明日之星,包括卡米勒和尼希米。据说在费茨杰的小说《杰出的西哥特》中,主角的原型就是魅力超凡的海迈姆。
在私药禁令被解除前,海迈姆给泥泽邦接收碑界地区非法生意所造成的一切障碍,都被彻底清除干净。828年4月11日傍晚,有人发现他腹部中弹,跌跌撞撞地走在乌迪内街头人行道上。海迈姆活了三天,但他严守自己的“Omerta”戒律,不肯指认凶手,也不愿意透露被害的可能动机原因。“我不会告诉你,”一名探员引述他在医院临终时所说的话,“你忠于你的职业,我做好我的原则。”他死时四十九岁。
马可·奥勒留是碑界地区的一名法哈德裔律师,在三四十年代曾为佰扎和法哈德泥泽邦船番人做过当庭辩护。他近距离审视了泥泽邦中新的种族关系变化。“两个团伙总是令人惊讶地默契配合着,”奥勒留评论说,“塔图因人佩服法哈德人的经济头脑,而法哈德人喜欢静静地待在幕后,让塔图因人施展必要的武力。”
泥泽邦的威慑力量来自于他们极端的有结构犯罪形式——设案谋杀。在859年的帕维亚会议上,老板们象征性地添加了只有船番人才能处决船番人的规定。同时他们还可以处决外人,甚至因为可能威胁了一名船番人,就有可能面临被处决的报复。
法哈德诈骗活动专家奥托·提比略曾提出过警告,提醒人们如果在经济方面的问题上挑战泥泽邦的权威,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作为一个局外人,法哈德泥泽邦在任何主持或谈判中,总是输掉的一方,”他抱怨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反正总是我们在付出,即使在我们没有犯错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在私药禁令期间,曼图瓦泥泽邦控制了碑界地区的很多地盘和资源。他们最为强大和无情的偶像,是奥尼·卡利古拉。他最初是个十分危险的持械劫匪人物,在乌迪内的地狱厨房附近出没。他在禁令期间的活动最终让他成了一个在多家夜总会都有投资的知名富豪,而其有仇必报、诡计多端的名声,和他在市政厅里的政治影响力,使得塔图因泥泽邦也不敢跨越他的领地边界半步。
但私药禁令的废止和泥泽邦的崛起,让卡利古拉相信,他在任何领域都不能和塔图因泥泽邦共存,或者对抗。863年,四十多岁的卡利古拉宣布退出碑界地区,南下到古莱什镇重新安营扎寨。那时古莱什镇地方当局素以腐败软弱闻名,使得这里成了各种江湖人士各显其能的乐园和避难所。经历了碑界地区的剧烈斗争之后,卡利古拉发现古莱什镇的环境很适合他擅长的生意活动,他后来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非法赌桌之王。
在后私药禁令的其他各城市,泥泽邦对曼图瓦和法哈德船番人的斗争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盘踞在帕维亚和达尔贝尔的曼图瓦行动队具有相当的实力,还有达累斯萨拉姆的团伙和摩苏尔城的法哈德团伙,都面临着两种选择出路:要么被击败,成为实施特定犯罪的雇佣帮手,要么向泥泽邦缴纳例费,从此只能以赌桌生意经纪人的身份来开展业务。
碑界地区各泥泽邦在三、四十年代纷纷巩固自身基础的时候,打击他们的执法工作却正处于最无序的状态中。然而,受到隔离保护的老板们仍然在密切关注阿布德·以利沙马失前蹄的法律陷阱——逃税案。
阿布德·以利沙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均不得而知。各种档案显示,他出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生地如果不是塔图因南部,就更有可能是在弗罗西诺内堡。和许多他那个时代的船番人一样,以利沙早年就辍学,随后作为街头团伙里的一名新助手,接受了些基本的训练。在一家星系连锁酒吧里做场内安保时,以利沙的左脸被肇事匪徒用利刃砍伤,这让他博得了一个凶恶绰号——“伤疤脸”。
当私药禁令进入白热化的时期,他动身来到了帕维亚,匪夷所思地成了安保委员会的一名初级外勤侦探,同时,他还承接当地商贾富人的持械贴身保镖。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利沙经过一路拼搏,坐到了帕维亚泥泽邦龙头老大的位置,控制着数千万马赛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生意。私药禁令造成的浮躁无序的社会风气把船番人变成了媒体名人和流氓枭雄。得意洋洋的以利沙出尽了风头,他接受采访时常说的话是:“我只是个做生意的人,急人所急、给人所需”和“我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身材矮胖、头顶渐秃的以利沙没有打算避开公众视线的想法。他喜欢坐在体育比赛的前排包厢里,让热情的运动员们在身边蹲下来排队等他签名。他还喜欢在帕维亚或纳吉布的豪宅里举办热闹嘈杂而混乱的宴会。
他的招摇态度与暴力最终给自己惹祸上身。877年情人节那天,费达·法瓦兹的五名手下,还有一个碰巧逛街而来的眼镜店验光师,靠着一面篱笆墙排成一排被机枪扫射而亡。令民众胆寒的是,帕维亚的执法机构被以利沙所成功收买,他们并未对这起街头屠戮或以利沙的任何活动做认真全面的调查。但这可怕的情人节惨案激怒了加尔巴·维斯帕总统的政府,促使它决心对目中无人的以利沙开刀。此外,这一届星系政府继续推行私药禁令,而名声在外的以利沙的公开挑衅,也让星系政府感到非常尴尬和窘迫。
财政部的一个特别小组曾做过大范围的调查,不过也只是触及以利沙真实非法收入的皮毛而已。但这个由资深审计调查员带领的小组还是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包括以利沙最近五年期间超过了一千多万马赛酬金的相关证据,这些收入从来没有申报纳税。打败以利沙的竟然是这些勤奋的会计师,而非星系联邦调查局,也不是电影和电视剧中的那些风靡一时的警方侦探。
被查明犯有逃税罪后,以利沙于879年开始服刑。身患晚期癌症的他先后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教养所和联邦监狱里待了近六年。885年末出狱时,曾经不可一世的以利沙变成了一个颓丧的可怜病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帕维亚,899年他死在哈巴雨林谷的家中。
除了提醒碑界地区的老板们需要提防税务调查风险外,他的垮台对他们并无实际影响。以利沙的权威仅仅局限在帕维亚地区,他在管理委员会的席位可很容易地由其副手来填补。碑界地区人们曾经怀疑以利沙并不是泥泽邦文化和团队集体的真正信徒。他们抱有这种疑虑是自然而然的,毕竟他拒绝把船番人的入会仪式引入到他的班子当中。实际上,人们怀疑他甚至并不把自己看成船番人。对泥泽邦纯化论者来说,以利沙的“团队”在运作时,更像是个搭帮结伙形成的企业,而非一个传统的罪案家族。而且他还违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把核心职责托付给了非塔图因人去履行。
以利沙从他的庞大生意中赚了很多钱,但他好出风头,其声誉在举止低调的碑界地区教父中多受贬损,徒有光鲜亮丽的虚名。最终,以利沙在泥泽邦言过其实的存在,反而要了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