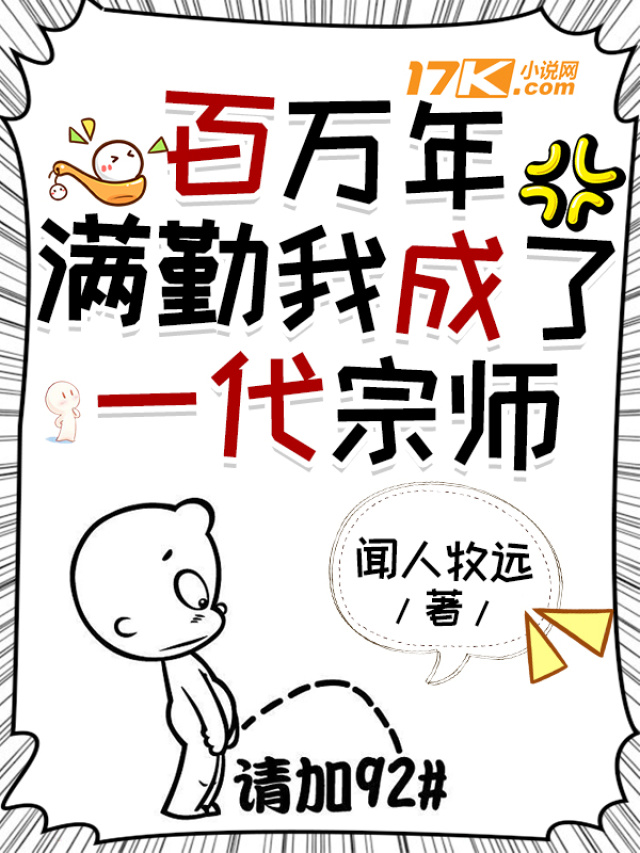玉奴本名叫什么,她自己都早已记不清,只是五岁那年出城时的点点滴滴倒是记得分外清楚。
那年蜀中大旱,本是佃农的家中更是颗米没有,正巧三哥一场大病,看样子就是不行了。可惜,老天还是留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一个过路的妇人上家里来讨碗水喝,听说他们的情况,又看看躲在一边偷看的玉奴,眉开眼笑起来。
“我看你这幺女儿长得倒也标致,何不交予我,你们也好得些银两,给三儿子治了病还能剩些度过眼下的难关。”
听到此番话,父亲犹疑起来,“这位嫂子是哪户大户人家的?”他以为是城里的大户要收些丫鬟粗使。
不料这女人话锋一转,道,“我这也不怕告诉你,我乃京城人氏,出身京城最大的翠红楼,你女儿能放在我手里调教,必定大有所为。”
听到这,父亲才恍然大悟这人竟是鸨母,只是母亲有些不明白的小声问父亲道,“这翠红楼是什么地方?”
“妓寨!”父亲没好气的说道,母亲听后长大嘴巴,半响才喃喃道,“我们不卖女儿。”
妇人轻蔑的啐了一口,道,“我这翠红楼才不是那些低下的娼寮,是官府明文在册的官寨,来往的也竟是些达官贵人,你女儿在这地方,大了也最多嫁于山野匹夫,而看她的长相,说不定也是一场祸水。”妇人看几人是听了进去,语气稍微平缓了些,继续劝诱道,“而你看看你那可怜的三儿子,如若请个大夫来看看,也许还有条活路。”
母亲往里屋瞅了一瞅,眼泪就要下来,三哥自小乖巧懂事聪明伶俐,最得父母的宠爱。
那妇人一看有了松动,再接再厉道,“再说,我接你女儿是去享福的,巧了被那个官人看中,不也是荣华富贵一辈子,也好过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生啊!我刚才瞧着你家邻居是否又刚死了人?”看母亲轻轻点头,那妇人又道,“这是老天要给你们家活路啊!不说别的,先把眼前这道鬼门关跨过再说,什么都好过这一家人抱着一起死的好啊!”
鸨母舌灿莲花,轻易说动了父母,就这样,她离开益州,前往京城长安。
送行那天,父亲没来,来的只有母亲和向来疼爱自己的四个,母亲抱着她痛苦,口里直说着对不住的话,而四哥则在一旁信誓旦旦,说是要替自己早日赎身。五岁的她什么也不懂,却漠然冷眼旁观一切,最后竟是连手也没挥头也未回,被鸨母牵着就走了。后来回想,自己竟也是没心没肺之人,对于至亲,却也是这样冷漠淡然。
来到翠红楼后,鸨母为自己起名红玉,丝丝带血却冷硬如冰。
那翠红楼却是烟花繁华之地,每夜都是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不断,只是这醉生梦死之地呆久了便看清这不过是人间炼狱,埋葬了多少女子的青春与血泪。
说是清倌,开始不过是粗使的丫鬟,为各位姐姐端屎端尿也没少挨藤条鞭棒,最厉害的一次,被当时的花魁一张雕花凳子当头砸下,顿时头破血流,而鸨母为了让花魁消气,又罚自己跪在中庭一夜,血流了满脸都干掉,自己的右耳只能听见微弱的声音。
后来那花魁呢?
听静姝这样问,玉奴娇媚一笑,后来她人老珠花被几个男人玩弄抛弃之后,疯了好些日子,鸨母把她赶出去,我又把她捡回来,为楼里的姑娘们做些端屎端尿的活路。
玉奴的笑带着恶毒的光芒,其实她心里是恨的吧,也许从五岁那年被卖掉开始就恨了吧。
十二岁时,她被脱得精光裹了层布单就被扔到台上拍卖,那个买走她初夜的男人脑满肥肠,脸上带着猥琐的笑意,而他各种变态的要求,把她折磨的几乎死去。
倚门卖笑,背身痛哭,这便是姑娘,和在不在京城最大的翠红楼没有关系,也和是不是吃喝官粮的官妓没有关系,妓女就是妓女。
虽说看了男子不少丑恶嘴脸,却仍是十四五的怀春年纪,仍是日夜盼着哪个俊俏公子风流官人能把自己救出火坑。
十八岁时,她相信自己遇到了命定的那个良人,不是什么俊俏公子风流官人,而仅仅是一个年过四十的太中大夫。
说道这,玉奴停下来,目光闪烁,细看下,竟是含着眼泪。静姝也不敢出声,知道她还沉浸在回忆里,一段看起来似乎不太美好的回忆。
“云静姝,你相信男子的誓言吗?”玉奴突然问她,静姝呆呆的想了会儿,摇摇头。
“我从未接受过男子的誓言。”苏桦烨与她的婚约算吗?不算。
玉奴柔柔一笑,去了那股邪魅之气,竟也有些纯真,“我相信,即便知道那不过是个谎言,却也是最美最真实的谎言,即便知道那是假的,我也相信。”
是吗?即便知道誓言不过是谎言,也要相信?
“你上次说你活着,不过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誓言,就是这样一个誓言吗?”静姝问她,想起那夜她的质问。
玉奴轻轻点头,对静姝说道,“如果你听过,也会相信的。”
听到此,静姝垂下眼,她会相信吗?即便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