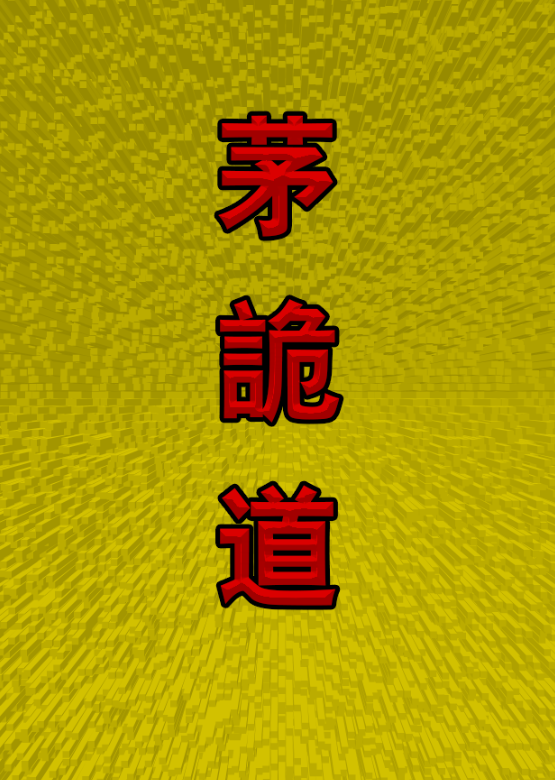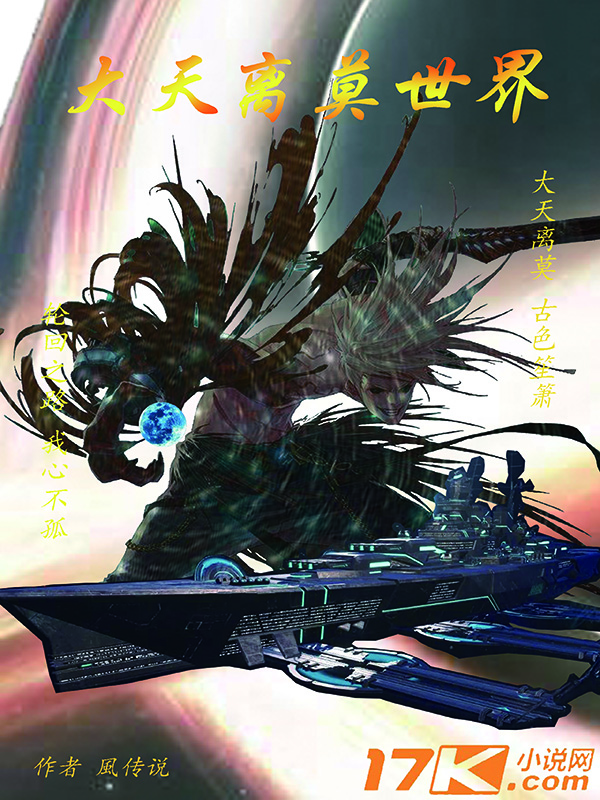静姝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身在自己的帐篷,里面点起了炉火,把整个帐篷都烘烤的暖意浓浓。她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脚,除了有些僵硬,一切都还好。
她撑起身子看看,帐篷里没有人,不知为何,悄悄舒了口气,只是转头时,一道人影闪入眼帘,顿时吓了她一跳。
“醒了?”阿史那端着一碗温热的马奶酒,似笑非笑的问道。
静姝看他一眼,下意识的问道,“我怎么会……”剩下的没说出口,因为想也知道,如若不是他同意,她怕是会活活冻死的在雪中。
阿史那起身走到静姝面前,递给她手中的木碗,“喝一口暖暖身子。”
静姝摇头,别过脸,问道,“一切都结束了吗?”
“结束?”阿史那冷笑一声,“没想到你这么没用,一场小小的初雪都敌不过。”
小吗?静姝在心底鄙夷,没有人可以再雪中跪上一天还不晕的,更何况她还……不过静姝并没有多做解释,长吸一口气后又说道,“那你为何要把我弄回来?”
“你活着还是有些用处。”阿史那又把碗放在她眼前,“不过你的不知好歹真是让人困扰。”
静姝瞪他一眼,抢过木碗,却因用力过猛,酒液泼洒在床铺上一些,“我知道我该做什么。”说毕,仰头一饮而尽。
那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进胃里,开始灼烧出一股暖意,而唇齿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奶香,这酒犹如江南的米酒,醇而不烈,回味无穷。可是静姝没什么心情回味这酒香,她把木碗随便一搁,就又倒头睡下,背对着阿史那,说道,“我要休息了。”
阿史那看着静姝的样子,突然间觉得有些好笑,像耍起了孩子脾气,跟那天口口声声跟他较劲儿的女子大为不同。这个女子到底有多少面呢?而哪一面才是最真实的她?突然间,阿史那对这个问题好奇起来,一股兴奋的战栗刺激着他。他笑着,带着某种算计的光芒,又找到些有趣的事情呢。
静姝等到背后完全没有了动静,才小心翼翼的转头看看,发现阿史那已经出去,这才完全的放松下来。她嗅嗅身上搭着的皮裘,一股奶香扑鼻而来,而胃里的暖意也在驱赶着四肢的寒意。再看看,床头的木碗也消失了,看来是他顺手给带了出去。
她有些猜不透阿史那青利这个人,对于他来说,自己应该不过是个俘虏是个工具,可是他又亲自为自己上药又准备了驱寒的马奶酒,静姝甩甩头,甩掉还没成型的想法,他这样对自己,不过是因为自己对于他来说还有些用处,她这样告诉自己,仅此而已。
什么积雪草,什么马奶酒,云静姝,难道你忘记那个人是怎么对待你的吗?你所有的苦难和耻辱都来自于他,你说过,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报仇!报仇!
静姝在脑海里对自己一遍一遍的重复,那些她再也不愿意触碰的记忆被迫在脑海里回放,记住痛,只有痛!
迷迷糊糊,静姝又昏睡过去。
玉奴进入帐篷,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云静姝在哭,紧抓着被子,小脸皱在一起,哭红了鼻子,声音很低,压抑着情绪,却让人看了更加心酸。
“云静姝?”玉奴走近,发现静姝原来在梦中哭泣。看来是做恶梦了。
玉奴轻摇她,她睡的浅,一摇便在眼泪中转醒了。
“你……”静姝迷迷糊糊的醒来,一时间有些分不清眼前何人。
玉奴笑笑,“做恶梦了?”
静姝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静姝用手背胡乱擦擦眼泪,有些不好意思,“看见些不好的事。”
玉奴也没有再多问,只是替静姝理理枕头,让她斜靠起来。静姝才有些理性思路,想到,“你怎么会来的?”
玉奴是红帐之人,在营地中地位最为低贱,而这营地中央是首领贵族所在之地,她本该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玉奴也明白静姝说的是什么,答道,“阿纳赐带我来的。”
听到这,静姝放下心,如果是阿纳赐的安排,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来找我,何事?”
“难道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吗?”她嘴微翘,又是那种独有的娇嗔。
静姝忙答道,“不,当然可以。”
“那你可觉得好些?”
“好多了。”静姝低头。
“看着你昏死过去可真是把我们吓得不轻,那个阿史那青利也是,竟真是把你丢在雪堆里就是半天,也不怕你出什么事。不过……”玉奴话锋一转,“后来看他紧张的样子也不是不顾你的死活,还说什么你成为圣女需要奇迹,如果人真死了,要什么奇迹还有什么用?”
玉奴牢骚发了一堆,看静姝睁着眼睛看着她,好似没什么反应,又轻拍她的手,道,“你也真傻,他让你跪着你就跪着,怎么也不求救呢?”
静姝把手从她的手里抽出来,冷笑一下,“他让我跪我不跪,可以吗?”
一句话,玉奴沉默了。她们的命都是攥在这些突厥人手里的,哪有什么反抗的余地,不是连军妓都做了,跪一跪有什么大不了。
“只是……”玉奴有些犹疑,“你要一辈子都这样吗?”
“什么?圣女吗?”静姝撇撇嘴,“如果我可以当一辈子的话。你我很清楚,我根本不是什么圣女,也不会有所谓的奇迹,那些人迟早会发现这一点,也许那时候……可是连火坛我都上过了,还有什么地方能吓住我呢?”
玉奴望着静姝,她在笑,却很凄凉,这算是一种洒脱吗?还是仅仅是无奈。
“也许……”
“就比如说现在,我根本没有能力治愈这些病,那个突厥人太高估我的能力,我连这关都过不了。”
“谁说的!”玉奴突然变得有些急,“其实……其实这场瘟疫很快就要结束了。”
静姝偏头看她,有些不解,玉奴索性继续说下去,“死人埋,活着的人也埋,你说这瘟疫怎么传播。”
静姝讶异,张大嘴瞪着她。
玉奴反倒显得有些无所谓,“其实每个地方对付瘟疫都没有区别。知道七年前益州的那场瘟疫吗?”看静姝点点头,玉奴继续说道,“那场瘟疫中,足足死了万人,官府封城,不让人进不让人出,益州城几乎沦为死城。”
静姝是听说过那场轰动全国的瘟疫的,即使身处的洛阳,也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愁眉不展,家里各处洒满了雄黄酒,那股刺鼻的味道两月不散。
“你是益州人氏?”静姝看她伤感的样子,问的有些小心。
玉奴沉默良久,才说道,“不,我五岁那年就离开那里了。”
听她的语气,静姝知道,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