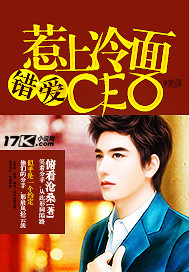直走到离人群好些距离,月奴才停下来,甩开静姝的手,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脚下的草。
“怎么?”静姝索性在草地上坐下来,拔起一根草绕在指上,河水在脚下流过,比起夏日小了不少。
“没有。”
“不喜欢为何要买下来?”
“谁说我不喜欢。”月奴说的有些赌气,却也乖乖在静姝身边坐下,“我喜欢的紧。”
“骗人。”静姝说的轻,几乎未闻,却仍旧飘进了月奴的耳朵,她红了眼,犹疑了几下,仍旧开口。
“云奴,你生气了。”
静姝摇头。
“那你为何……”
“不是吗?”静姝转头望向她,看她的泪轻易滑落,攥起衣袖为她拭泪,“你何故那样针对玉奴?”
“我……”月奴不知该如何表达,想了想才说道,“不光是我,红帐里的姑娘都讨厌她。”
她说的理直气壮,却因把刚上的胭脂弄花,更显狼狈。
“因为她是汉女?”
“不全是。”
其实静姝心里是明白的,女人针对女人的敌意,只有一种,因为对方的美丽。玉奴是红帐里最美的姑娘,无可否认。所以,同为汉女,月奴可以亲近她,却敌视玉奴,普通的样貌,是她的幸。
一阵悠扬的乐声飘来,两人同时望去,发现不远处一人临水而立,广袖宽带,卓尔不群。他手执横笛放于唇边,轻忽间,悠扬之声从唇间溢出,婉转而悠长,仿佛顺着着白水飘向远方。
一曲完毕,那人转身,才发现身后两个听得如痴如醉之人。
“献丑。”那人含笑,眉目间自有光华。
静姝回他一个浅笑,“这一曲本是江南小调,婉转流长,却在阁下手中幻化出长河落日般的空寂辽远,佩服。”
“呵呵,”那人听静姝这一赞誉,知道遇到了知音之人,笛子在手中一转,“曲倒是一样,只是这壮阔景观给人不同感受罢了。”末了又加一句,“姑娘也是同道中人?”
“不敢,只是略知一二。”
月奴在旁边看着这两人一来二往来了兴趣,拉起静姝就凑上前去,“你从哪里来的?”
那人看看眼前这皱着鼻子声音清脆的小姑娘,觉得煞是可爱,不答反问,“姑娘看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知道你是汉人,我是问你可否从那长安而来?”在月奴的心中,长安便是大唐,大唐亦是长安。
咳咳,那人突然掩嘴轻声咳嗽两声,再清嗓答道,“我的确从那长安而来,不过,在下却是扬州人氏。”
“扬州?”静姝轻声惊呼,惹来两人侧目,静姝却笑笑掩饰住惊讶,岔开话题道,“公子像是病了?”
“西域风凉,这几日感染了风寒,不碍事。”
他这么一说,月奴才注意到男子两颊泛起不自然的红晕,似乎有些病态。
静姝继续问道,“公子不像商贾,跟着这商队是要去哪?”
那男子被静姝说中,目光调高,落在不远处正乱哄哄做着买卖的人群里,吐出短短两字,“求佛。”
这条商路沟通东西,自汉代以来便担负着东土与西域互通有无的任务,东边,送去丝绸瓷器和茶叶,而西边,带来了珠宝马匹以及佛教。
“我自幼体弱,被家人寄养在佛堂,方丈说我颇具慧根,收了我做关门弟子,整日的佛经佛法念下来,才方知佛量无边,为寻佛缘真谛,从扬州到长安,现在又从长安出发。”
听完他的叙述,静姝静静接道,“你这一去,怕是要到天竺吧。”
男子又是一笑,有些惊叹她料事的神准,“姑娘果然见多识广。”
“不敢,只是求佛,不去天竺又去哪呢?”
言语间,静姝的目光掠向远方,有淡淡寂寥的味道,男子似乎也被这样的气氛感染,敛目说道,“其实能否抵达天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求佛之路,佛驻人心天亦道,求佛本在‘求’字不在佛,这千里黄沙路便是人世劫难历练,走过了便求到了。”
这一袭话毕,无人再语,半响,月奴才愣愣冒出一句,“不懂。”一下子打破了低迷的气氛。
男子缚手一笑,“姑娘懂得,这人生百味又有谁人不懂。”
月奴用怪异的眼神看他一眼后,趴在静姝耳边咬起耳语,“这人好怪,我们还是快些走好了。”
“姑娘,背后议论可不好。”显然,月奴的声音并不够小,男子抱臂望她们,摇摇头。
月奴白他一眼,拉着静姝转身就要走,却不想被男子手中笛子一横拦住。
“怎么?”月奴立眉。
“只是觉得在这他国异乡,能遇见姑娘这个知音人实属难得,”男子顿顿,“这把笛子算作见面之礼,还望姑娘笑纳。”
听他这么一说,静姝打量起面前的这把笛子。不过是普通的青竹短笛,没有任何文绘装饰,只是拿它的手指干净修长,握在手中自有一股清新文秀之气,似乎竹汁未干,夹带着江南的烟雨朦胧。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月奴不屑,正想挥手打掉竹笛,却不料静姝反手制止她,轻轻接过笛子。
“谢过公子。”
“云奴?”月奴很是不解,无故受人物品,这绝不像静姝的作风。
静姝拍拍月奴的手背以示安抚,转头面对男子,“云奴身无长物,就借花献佛为公子吹奏一曲,聊表心意。”
说罢,竹笛信手横在嘴边,一串轻巧的音符旋即而出,似晨雾中黄鹂鸣叫,清脆婉转,紧接着,几段长音高亢而出,却是红日刚上露水才消,听者无不弯起嘴角,期待不已,只是忽然间,音调大起大落,一串颤音之后几段低语呜咽,情绪急转直落,最后在这低吟徘徊之中,笛音默默收尾,予人无限感慨。
一曲奏罢,男子神情肃穆,望向静姝的眼神有些许哀愁,此刻,人群中暴出呼喊,却是催人上路的,这里,不过是他们的过站。
“姑娘,保重。”男子说的郑重。
“保重。”静姝回礼,手上多了一截青笛。
两人目送男子离开,直到商队远离红帐,消失在茫茫的荒漠之中两人才收回目光。月奴看看静姝在手中玩弄的青笛,撇了撇嘴,“你一定很喜欢那男人。”
喜欢?静姝对这个词皱眉,“何解?”
月奴甩甩手,跑前几步,又回身说道,“你对他笑,又收了礼物,不过我挺喜欢你笑。”
经月奴这么一点,静姝才惊觉自己已经久未露出笑容,而刚才对着那男子的笑意,除了礼貌估计还有异地同乡的亲切。她也是扬州人氏,五岁前一直生活在那里,虽然模糊了记忆,骨子里仍感觉的到那股江南的潮气。
“不过,”月奴把脸凑过来,“你吹的曲儿叫什么名字?还多好听的。”
静姝放缓脚步,慢慢道来,“这曲儿没名,不过是家乡的小调,讲得是临行送别之意。”
“送别啊?”月奴有些懂了,“怪不得你要吹这么个曲儿给他听,后面听着的确有些悲哀。”
月奴不知道,这曲子讲得是异乡送亲人,有家归不得而遥望的怅然,那扶木而望的女子因远嫁而思乡,怀捧着盛满血泪的玉壶,是怎样的凄凄惨惨戚戚。
月奴不知道,可是那男子知道,一首家乡小调就已经表达一切,可是他能如何,他不过是路过的旅人,在这变幻莫测的荒漠中已是自身难保,又有何能力带她脱离险境,所以,罢了,换来一声保重也好。
静姝重新把目光调向商队离开的方向,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她手中的那玉壶,怕是也早已溢满了心血,只是故乡只能遥望,离开,开始变得模糊。
玉笛轻吟浅低产,一条血路无归途,却是黄泉生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