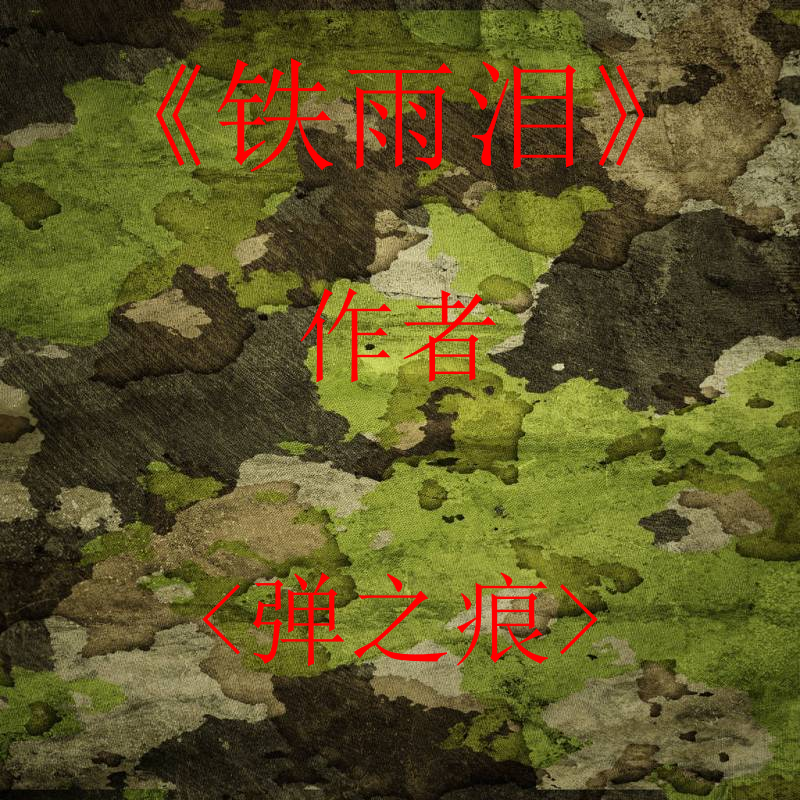夜色凄凄,阮卿看不清定儒脸上的表情,唯独他流光的眼眸,如镜湖水一般柔和温暖。他双手捧住她的脸,轻轻吻在她脸上,暖暖的,痒痒的,更无法形容心中那一份窃喜。他说:“我喜欢你,我只怕你不跟着我…我只怕你,不跟着我…”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似在叹息,似在呢喃。
阮卿睁开眼睛,觉得脸上凉凉的,用手一抹,全是泪。上官笳推了推她,压低嗓子问道:
“定儒哥哥是谁呀?是谷底那个漂亮大哥哥吗?”
阮卿一愣,定定地望着她,微光里上官笳的眼睛如黑宝石一般闪着光,她立刻别开头去。上官箫、上官笳、上官篌、上官寥,这些人的眼睛无一例外地都亮得怕人,她不喜欢。上官笳又道:
“你总叫他的名字,都把我吵醒了,给我说说嘛,我保证不告诉大哥就是了!”
阮卿脸上一红,啐道:
“我才不跟你说!”
说着,阮卿穿好衣服走出帐外,东方已露鱼肚白,树林里不知名的鸟儿一声声啼叫着,清晨的空气格外新鲜清冷。一眼瞥见上官竽正同仆人们一起喂马,这位爱马如命的主儿总爱亲自伺候自己的良驹。阮卿上前叫了声:“竽哥”,便同他一起喂起马来。上官竽瞧了她一眼,道:
“起来了!”
阮卿“嗯”了一声,随口问道:
“箫哥呢?”
上官竽未及答言,背后忽然传来上官篌的声音:
“离了箫哥你还不能活了?”
阮卿转身狠狠瞪了他一眼,正要发作,上官篌已然抽身离去。阮卿回身猛抓了一把饲料塞进马嘴里,冲口道:
“这家伙烦人透了!”
上官竽并不转头,仍认真地喂着自己的马,状似心不在焉地说道:
“只因他心中有你。”
阮卿诧异地望向他,正要发问,上官竽推开她,道:
“有你这么喂马的呀?去去,别跟我这儿捣乱,找你的箫哥去!”
阮卿被推得倒退了两步,怏怏地拍了拍手上残余的饲料,转身走开。上官家这些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上官竽与上官篌不待见她,上官篌是事事与她作对,上官竽则是真正将她当自家妹妹一般,要训就训,要打就真打。阮卿即使敢跟上官箫使性子闹别扭,跟上官篌吵到天昏地暗,甚至敢挤兑上官寥,却从不敢对上官竽不敬。正好上官箫也出了帐来,见阮卿只穿了棉布小袄,外面罩了件披风,微凝了眉道:
“快把大袄穿上,怎么能这样单薄就跑出来了?”
阮卿心中本来有气,冷冷地道:
“要你说,我又不是离了你就不能活!”说罢,跑进帐中添衣服。上官箫微微怔了怔,哑然失笑:八成是受了谁的气又撒到我头上来了!
阮卿添衣洗漱完毕,天已大亮,奴仆们正准备着早膳,热腾腾的香气飘出老远,阮卿立刻心情大好。跑上前去要仆人盛一碗汤给她,捧在手里边吹凉边小心翼翼地喝起来。众人都陆续起了,洗漱完毕聚拢来用早膳,顺便各自发一番雄壮之论。阮卿笑得极其乖巧:
“我只要一头梅花鹿,割下胸脯肉给笛哥吃!”
上官篌道:
“我要一头梅花鹿,割下胸脯肉给笳妹吃!”
阮卿的好心情又被破坏,横了上官篌一眼。上官笳毫无机心,笑道:
“谢谢你啦五哥!”
上官箫见场面又有些僵了,遂笑道:
“这么巧,我也要一头梅花鹿,割下胸脯肉给卿儿吃!”
阮卿看着上官箫笑了出来,众人也都笑了,除了上官篌。众人一顿早膳吃得津津有味,香气引得周围的动物也零零星星地聚拢来,瞧着这一群人直流口水。阮卿坐在上官笛对面,忽见他双目圆睁,看着阮卿身后的丛林,连汤都忘了喝。阮卿诧异地问:
“笛哥,你怎么了?”
上官笛仍是瞪着眼,目不转睛,怔怔地道:
“我的胸脯肉!”
阮卿回头一看,一头漂亮的梅花鹿半身隐在粗大的树干之后,露出小巧可爱的头,一双亮汪汪的眼睛直盯着众人。阮卿大喜,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碗站起身,解开缰绳翻身上马,勒转马头,那鹿儿已散开四蹄逃了,阮卿叫道:
“哪里跑!”伏低身子,举鞭在马臀上一击,马儿嘶叫一声蹿了出去。
那鹿儿矫健轻灵,在树林中穿梭奔驰,忽隐忽现,游刃有余。阮卿勾唇一笑:好鹿儿,肉质一定鲜美异常。马蹄声纷乱急疾,阮卿回头一看,上官箫与上官篌两骑已追了上来。上官箫大呼道:
“卿儿,五弟,咱们三面围追堵截,量它插翅也难飞!”
阮卿清亮的声音响彻山林:
“得令!”
上官篌也中气十足地答道:
“好,且看今日鹿死谁手!”
三骑马转眼分为三路,阮卿在中,上官篌左路,上官箫右路,同时追击。若在平地千里的大草原上,凭三人坐下良驹,要追上一只梅花鹿实非难事。但在丛林之中,鹿儿对地形的熟悉和身形的轻灵占了大便宜,高大健壮的马儿倒显得束手束脚了。三人追赶着梅花鹿奔驰了一顿饭的工夫,仍是忽近忽远,难以追到左近。阮卿心急,稳了稳身子,从背后取下弓箭,拈弓搭箭,“嗖”地一箭射了出去。此时距离忽然拉大,阮卿这一箭劲力不足,还未追上鹿便已跌在地上。左路立刻传来一阵冷笑,显是上官篌发出的。阮卿不由得脸上一红,咬了咬朱唇,心道:好啊,就这么耗下去吧,我们这三匹可都是千里马,瞧谁耗得过谁!又追出一顿饭的工夫,三骑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形成一个庞大的包围圈,将鹿儿逼向唯一的方向逃窜。阮卿越追越是兴奋,滴水成冰的气温下鼻头竟沁出了汗,拈弓搭箭,“嗖嗖”又是两箭,却都射偏了。阮卿呼出一大口气,隐隐感觉背上有汗发出,将弓背在肩上,举鞭抽了下去。太阳越升越高,即使在遮天蔽日的密林里,也感觉到了它耀眼的光芒。三骑疾驰,枯叶翻飞,湿泥飞溅,三人衣袂飘舞,英姿飒爽。那鹿儿渐渐体力不支,脚步开始显得有些踉跄。左奔,上官篌一骑逼来,右突,上官箫一骑封路,背后阮卿一骑,随时都要发难。鹿儿慌了神,脚步越来越杂乱无章。阮卿大喜,却不再放箭,她终于知道为什么上官箫没有放箭,就是要耗尽鹿的体力,这会儿眼见就要大功告成,若再分心放箭,速度定然慢下来,让上官箫得了头彩倒没什么,输给上官篌却实在憋屈。
又奔出数里,面前出现了一条小溪,鹿儿“嘡嘡嘡”踏水而过,三骑毫不迟疑地追上去,霎时水花四溅。鹿儿忽而一闪身,窜入了一条羊肠小路。上官篌与阮卿两骑不得不会师,一同追赶。上官箫心道:卿儿这样想得到这只鹿,我若与她争,她定然是争不过我的。我不过陪她玩罢了,让她得了去高兴高兴。于是他放慢了速度,跟在上官篌与阮卿两骑之后。再追片刻,鹿儿已经近乎虚脱。阮卿与上官篌互不相让,各自拈弓搭箭,“嗖嗖嗖”不停地放箭。一击不中,上官篌又从箭筒里拔出一支箭,金头白羽,煞是夺目。他微微侧过身子,箭在弦上,弓已涨满,嘴角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嗖”地一声箭离弦而出,猛然插入鹿的背脊。那鹿儿倏地浑身一缩,痛得呜咽了几声,又跑出几步,一跤歪倒。
上官篌大喜,正要上前取猎物,一眼瞥见阮卿体力不支,马儿纵身跃过一个小土丘,她手上缰绳一松,身子一歪便要跌下。上官篌大惊,大叫一声:“卿儿”,双足蹬离马镫,身子旋起,瞬时已落在阮卿身后的马鞍上,左手拉住缰绳,右手一托,阮卿便稳稳地坐在他怀里。这一连串兔起鹘落,极为迅速漂亮。上官篌时已十四岁,只比阮卿大一个月,阮卿因练了熔岩掌,看起来要比他大上几岁,可上官篌的身材已比她高大了。第一次碰到阮卿的身体,上官篌不由得心中一荡,鼻子里嗅到阮卿身上幽幽的处女体香,脸上有些发烧,双眼怔怔地竟不知道该瞧哪里了。上官箫纵马上前,急叫道:
“卿儿,你没事罢?”
上官篌如梦初醒,将手里的缰绳交到阮卿手里,提气纵身跃回了自己的马背,勒马停蹄。脸色又回到了一贯的冷傲:左右有人照顾你,我等闲凑什么热闹!上官篌下了马,那鹿儿还想逃跑,被他一掌打得瘫软在地,伸臂抱了放在马上。抬头看上官箫与阮卿两人,哪里还有闲情管这鹿,一个惊魂未定,一个问伤问痛。上官篌没来由地心里有气,翻身上马,掉转马头,一言不发,纵马驰去。
三人回到营地,众兄妹奴仆们都已满载而归,见上官篌一马当先,马上卧着一头梅花鹿,上官笛笑道:
“原来是五弟得了头彩,看来的确指望你比较靠谱,我这胸脯肉怕是泡汤了,笳妹倒是好口福!”
上官笳抚掌笑道:
“五哥真好,五哥真了不起!”
上官篌脸上殊无得意快活之色,勒马下镫,将鹿丢给奴仆。阮卿与上官箫也都下了马,阮卿兀自喘息不住,上官箫拿过水袋,打开塞子递给她,她举起水袋仰头“咕嘟咕嘟”灌了半袋下肚,背上越发涔涔汗出。她缓了缓神,对着上官篌的背影喊道:
“五哥,谢谢你啦!”
上官篌顿了顿,却没有转过身来,兀自拿起水袋喝水。上官箫笑了笑,心道:这小子愣头愣脑,怪道总找卿儿的茬,今日才算弄明白了,想想实在好笑。
上官笳眨了眨眼睛,问阮卿道:
“谢他做什么?他答应分你胸脯肉吃?”
阮卿横她一眼,不答。
检点猎物,上官竽当仁不让,竟打下一头东北虎,众皆赞叹。上官笛得了两只野兔,上官笳两手空空,奴仆们倒是得了不少,有鹿、野猪、黄鼬等等。上官笛声称自己差点打到了黑熊,一箭射瞎了它的左眼,却让它逃了,众人皆哄笑不信。
众人逶迤回到傲然宫时已是黄昏,见过了上官寥和夫人,回禀了个人的收获。上官寥听闻上官竽得了一头虎,上官篌得了一只鹿,均大加赞赏。上官笳笑着对父亲说:
“五哥那头鹿的胸脯肉是给我的,他答应我了!”
上官寥瞧着女儿憨态可掬的脸,竟破天荒地笑了出来,道:
“哦?你一个人吃得完么?”
上官笳道:
“嗯,还有卿妹妹一份,五哥也答应她了!”
上官笳始终以为阮卿谢上官篌是因为分得了鹿肉,阮卿瞧着她腹中偷笑。上官寥似乎心情很不错,又笑了笑,“嗯”了一声,点点头。
阮卿这一日是累坏了,回了房便叫丫鬟放热水,想洗了澡早些安寝。她将自己泡在浴桶里,舒服地闭上眼。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镜湖,水热得直冒热气,舒服得她连太阳下山都不知道,累得定儒四处找她。阮卿想着想着,嘴角露出了笑意,这笑意忽又渐渐淡去,终于不见了。定儒哥哥,我今日没能打到鹿。定儒哥哥,你骑射的功夫一定也很高吧,可惜却没能教给我。什么时候能与你一起骑马打猎呢?与你在一起,不管做什么都好,可你如今,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无谓地问了两遍,阮卿忽然鼻子一酸,落下泪来。眼前浮现出定儒的脸,清朗俊美,温文尔雅,和蔼淡然。虽然总是温和,却自有一股震慑力,令阮卿不敢任性胡闹。他教给的功夫,她已练得越来越纯熟,想得到他一句褒奖竟不能够了。他说过的话,一句句言犹在耳,一字一字,都清清楚楚刻进她心里去。
阮卿抹了抹眼泪,片刻间竟浑然没有了睡意。洗了澡穿好衣服,阮卿披了件披风,出门往瑶池殿走去。丫鬟为她开了门,立刻禀报主子:
“大小姐,卿姑娘来了!”
阮卿大步走入,跨过几道门槛,掀开几道门帘,到了上官筝的卧室。炉子里的火焰跳跃着,屋子里暖融融的,上官筝歪在暖榻上,见阮卿进来,这才懒懒地坐起身子,笑道:
“卿儿妹妹来了,狩猎收获如何?”
阮卿望了望她,见她虽然笑着,秀丽的容颜却明显挂着一丝病容,遂问道:
“筝姐姐,你身上不好么?瞧大夫了没有?”
上官筝的神情有些怪异,眼神闪烁,微微笑道:
“不过是累着了,不用瞧大夫。”
阮卿当下也不多问,丫鬟为她解下披风,送上椅子。阮卿坐下,叹了口气道:
“筝姐姐,我今日是两手空空回来的。五哥虽然讨厌,但骑射功夫实在不错,我比他可差远啦。那只鹿都已经脚步踉跄了,可我还是射它不中,筝姐姐,我可真不是你的好徒弟。”
阮卿上清冷崖后,骑射功夫是跟着上官筝学的。南方多舟少马,阮卿从没骑过马,一开始学得极为吃力,半年过后才渐渐好一些。想不到上官筝貌似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儿,臂力却是惊人,连极为沉重的战弓也能拉满弦。阮卿对她佩服极了,怪道连定儒也赞她,百姓们叫她“雪山圣女”了。这“法力高强”四字岂是随便当得起的?阮卿在谷底就听过上官筝的名字,自然对她别有一份亲切,如今定儒与上官筝都成了她的师父,想想倒也是奇缘。阮卿每每想告诉她镜湖女妖的事,却又怕传进上官寥耳朵里,只好藏着不说。
上官筝只是温柔地笑着听她说话,这两人年纪差了十岁,倒真似一对师徒似的。阮卿又道:
“我也不是定儒哥哥的好徒弟,轻功学了个半吊子。筝姐姐,我这样整天吃喝玩闹,日子过得忒也没意思,唉!”
上官筝笑道:
“小小年纪倒学会叹气了,那卿儿究竟觉得怎样才有意思呢?”
阮卿望着上官筝,竟怔怔地答不出来了:
“究竟怎样才有意思?究竟怎样…”
上官筝微微低了头,心道:卿儿原本说得倒也不错,这日子确实好没意思!
正在这时,窗外忽然传来一声低叹,似是男子的声音,叹息声里饱含着深深的无奈。两人俱皆大惊,阮卿跳起身来喝道:
“谁?装神弄鬼的,想干什么?”
上官筝却红了脸,神色惊慌:是他么?声音好生相像,他来这里做什么,不怕给父亲撞见了?当下六神无主,双手绞着衣服,贝齿咬得下唇快要出血:快走,快走,莫要被人发现了,我…我可如何救你!我怎样都无所谓,可是你,你若有个什么,我却如何…
阮卿冲到窗口打开了窗,大叫道:
“是谁?胆敢私闯傲然宫,胆子当真不小。”
只听得一个声音冷笑了几声,忽然间一个黑影不知从何处窜出来,“呼啦啦”地掠身而去,霎那间融入了浓黑的夜色里,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