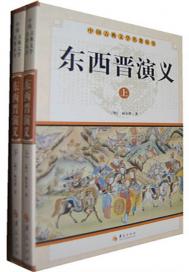话音未落,只听得“呼呼”两声,眼前已多了两个人影,锦衣华服,雪雕玉琢,正是上官篌与上官笳。阮卿立刻跳将起来,摆出全神戒备的架势,喝道:
“又想来抓我么,不妨上前比划比划!”
上官篌怔怔地盯了阮卿半晌,皱眉道:
“你吃了什么仙丹,竟长得比我还要高了?”
上官笳忽闪着大眼睛,点点头,接口道:
“是呀,你吃了什么仙丹,竟长得比我还要美了?”
两人说着,四只眼睛不断地上下打量阮卿。阮卿脸上一红,立刻含了胸,啐道:
“少废话,谁先上?”
上官笳将目光从阮卿的身体上移开,灿然一笑,道:
“我们又不是来跟你打架的,干什么这样凶巴巴的?大哥怕你冻死饿死,带着我们下谷底来找你。这都找了快一年了,你躲到哪里去了?不过看起来,你好像活得很不错,还认识了一个——”说着朝定儒望了一眼,敛眸一笑,“一个漂亮大哥哥,比起我们大哥来也不逊色!惹得我也想在这谷底住上几年了,呵呵呵!”
定儒望着这三人,只是沉默不语。上官篌与上官笳是一对龙凤胎,上官寥的幼子幼女。定儒在傲然宫生活这么多年,也只是听说过两人的名字而已。他们口中所说的大哥自然就是上官寥的长子,少主上官箫了,却不知他找阮卿做什么。江南扬帆镖局阮家的小姐,又是怎么来到傲然宫的呢?一连串的疑问在定儒的心里徘徊,令他忽然觉得阮卿离自己好遥远。
上官篌望了望定儒,冷冷道:
“比起大哥来,到底还差一些!阮卿,你这辈子就不要妄想了,就算我大哥不要你,你也不能另嫁他人!”
定儒凝了眉:怎么,卿儿竟已许配给上官箫了吗?
阮卿又羞又怒,更不多话,脚踏影步,瞬间飞身上前,举掌便打。上官篌反应更快,几个漂亮的旋身,身形已跃上了山头。转身狂妄地笑了笑,对阮卿道:
“连七步轻身都被你偷学了去,当真好不害臊!”
阮卿心下一凛:糟了,他知道我学了寒凝诀和七步轻身,回去告诉上官寥,那我可就惨了!当下脑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我抓住他,关在谷底,不让他上清冷崖!我封住他的哑门,让他不能说话!我挑断他的手筋,让他不能写字!不然,干脆杀了他,一了百了!
想到这里,阮卿眼中忽而燃起两团蓝光,美丽的脸庞顷刻间变得阴冷邪恶。上官篌眼睛一眨,阮卿已站在面前,这才发现自己比她矮了整整半个脑袋。他冷笑一声,竟不躲闪,运起寒凝诀一掌拍向阮卿左肩。手掌刚一触及她的皮肤,便立刻缩了回来,阮卿的身子像一快热炭般,将他的寒凝诀掌力化解得无硬无踪。上官篌大惊,抬头看见阮卿眼中蓝光大盛,朝自己邪恶一笑,他心道不妙,足点影步便要逃跑。还没来得及抬步,便看见阮卿抬掌往他天灵盖击落。上官篌心下一凉,只本能地闭上眼举掌挡隔,心中想着:完了,被她这一掌拍下来,我哪里还有命在!
只听得“呼”地一声,上官篌睁开眼睛发现阮卿已被定儒拉下了山头。定儒摇了摇阮卿的肩膀,皱眉道:
“你怎么了,你刚才险些杀了他!”
阮卿眼中蓝光熄灭,如梦初醒般看着定儒,又看看上官篌。心中一片混沌:我差点杀了他?我怎么会杀人呢?我连一只小动物都不忍心伤害,怎么会想要杀人呢?
上官篌惊魂未定地望了阮卿半晌,才开口道:
“什么邪门功夫!”
上官笳一阵小跑,躲到上官篌身后,可怜兮兮地望着阮卿道:
“小姐姐刚才好怕人!”
上官篌道:
“她不知好歹,咱们别跟她啰嗦了,去找大哥来!”
上官笳点点头,两人同时转身,掠步而去,不一会儿便不见了踪影。
定儒凝了眉,向阮卿道:
“卿儿,你刚才似乎迷失了心智一般,邪气大盛,这镜湖女妖教给你的功夫还是不要再练的好。”
阮卿点点头,道: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就想一掌打死他,好让他不能向他父亲告状。定儒哥哥,我是不是也变成小恶魔啦?”
定儒摇头笑了笑。阮卿道:
“我恨上官寥,可我从来也没想过去杀他。女妖教我武功,要我去杀死他,我心想我一家人被他害得那么惨,就答应了杀他。可是定儒哥哥,我一见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只盼着跟你长长久久一处做伴。就算要去救回妈妈,找回爹爹,我也想要你陪着我。你叫我不练这功夫,我便不练了,以后都跟着你,做定你的小尾巴了!”
定儒听得心中暖意融融,伸臂想拥阮卿入怀,终是忍住了,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忽又想起上官篌的话,心道阮卿若果然已许予傲然宫少主为妻,我又何德何能与他相争。卿儿此时与我亲密,不过因着在谷底无依无靠罢了。只怕见了上官箫,就把我抛在脑后了。顿时心中怏怏不快,缓缓说道:
“我只怕你不跟着我!”
阮卿嫣然一笑,轻轻握住了定儒的手。
当晚,阮卿忽然身上燥热难当,这情况在镜湖底的时候也发作过几次,是由于练熔岩掌太过急功近利,气血流动常常不受控制,动辄怒张奔腾。定儒将阮卿安顿好,说道:
“我去找些凉水给你喝,或许能好些。”
定儒出了山洞,想爬上山头找些干净的雪,给阮卿含在嘴里,化了喝下去。阮卿迷迷糊糊地躺着,浑身热得像被丢进了熔炉,连骨头都要被烧化了。挣扎**了半晌,张嘴吐了几口热气,连叫的力气都没了。隐隐约约感到有个人进了山洞,阮卿只当是定儒回来了,带着哭腔叫道:
“定儒哥哥…我…我快要死啦,我…我难受…”
那人蹲在阮卿身前,问道:
“你怎么了?”
阮卿喘息着扭动身子,浑身已像落水般被汗液浸湿,豆大的汗珠颗颗从额头滚落。那人将手掌贴上了阮卿的额头,顿时惊得“呀”了一声,说道:
“阮姑娘,我是上官箫,我们曾见过的。父亲将你打下无底谷,如今一年之期已到,我这就带你上去。你身上烫得厉害,须得立刻请大夫医治。”
阮卿脑中糊涂得厉害,听得上官箫的话,只含含糊糊地重复着:
“上官箫…上官箫…”
定儒手里捏着个大雪团,急步走来,忽然在山洞外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自称是上官箫。他顿时心中一凛,竟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近前。只听得阮卿痛苦地**着:
“我好难受…我要死了…水…水在哪里…”
定儒想到手里握着的雪团,便欲抬步上前。只听得上官箫说道:
“你不会死,我这就带你上清冷崖,宫里的大夫都是极好的,一定没事。”
定儒不自觉地又停步,立在原地,心道:是呀,傲然宫的大夫定能医治卿儿的病,好过于我现在手足无措。可是又想到阮卿这一去,两人见面之日遥遥无期,说不好重逢之时,她已嫁为人妇。但这谷底荒凉寒冷,实在不是女孩儿家应该待的地方,让她上清冷崖,进傲然宫,像筝儿一样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岂不是好?一时定儒心中犹豫不决,想到阮卿将要离开,又说不出的酸楚,五味杂陈,只愣愣地立在当下,不知所措。
上官箫将阮卿抱起,出了山洞,渐渐走远。定儒望着他的背影呆立半晌,终是没有追上去:卿儿该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将来,傲然宫上官箫,是比无底谷上官定儒好太多的选择。想虽这样想,心中却像压了块石头般沉甸甸的,令他呼吸有些困难。忽然觉得谷底格外荒凉寂寞,心里空荡荡的,茫然若失。感到手上一片湿冷,原是雪团已然化尽了。
阮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软绵绵的锦绣大床上,鼻子里嗅到淡淡的香味,是母亲最喜欢的龙涎香。一张美丽而略带忧郁的妇人的脸出现在眼前,她眼圈微红,想是哭过了,她焦急地轻声唤她:
“卿儿,卿儿,你可好些了?”
阮卿眨了眨眼睛,当她看清楚眼前的人时,泪水早已滚滚落下,她大叫了一声:
“姆妈!”翻身坐起,伸臂紧紧搂住阮夫人。阮夫人——如今已是上官夫人的阮夫人紧紧搂住女儿,刚刚止住的泪水又流了下来。两人相拥而泣,良久,母女俩终于擦干了眼泪,四手交握,四目相对,脸上带着笑容,怔怔地打量彼此。半晌,阮卿问道:
“姆妈,我们回家了么?”
精美的卧室,雕栏画栋,一张红木雕花大床,铺着蚕丝锦面熏了香的被褥,床头的小几上放着一尊金兽香炉,正袅袅地焚着香。窗前一架檀木梳妆台,漆色鲜亮,梳妆台上一面圆铜镜,将窗外的阳光投进屋里。这屋子,实在太像家了,令阮卿不禁怀疑,这一年来的种种遭遇都是一场噩梦,到头来发现梦醒之后,一切如初。
阮夫人低头,似是微微叹了口气,然后摇了摇头,正欲回答,一个丫鬟上前来,毕恭毕敬地打了个千,说道:
“夫人,您还在月子里,主上吩咐您好好保养身子!”
阮夫人点了点头,叫小鬟退下。阮卿怔了怔,问道:
“什么月子?”
阮夫人面有赧色,顿了顿,说道:
“卿儿,我们分开才一年,你怎么变成如此模样,倒好似过了四五年一般。”
阮卿欲言又止,泪水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阮夫人笑道:
“我们母女重逢,心中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一时倒不知从何说起了。卿儿,你身子还虚着,尚要好好养几日才可下床,我身上也不好,不如我明日再来看你吧!”
阮夫人说完便起身欲走,阮卿急喊:
“姆妈,再陪我一会儿!”
阮夫人脸上虽笑着,眉宇间抹不去的忧郁,柔声道:
“等卿儿大好了,等我也大好了,我们一刻也不分开。”
阮夫人转身离去,阮卿又叫了几声,她终是没有停步。阮卿眼里的泪汹涌而出,怔怔地望着阮夫人的背影。脚步声响,丫鬟撩开珠帘,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见到阮夫人,他恭恭敬敬地垂下头去,道:
“母亲!”
阮夫人亦恭敬颔首,道:
“少主!”
两人具各毕恭毕敬地行过礼后,阮夫人抬步欲走,上官箫道:
“母亲不多陪陪卿妹?”
阮夫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却是勉强得很:
“主上要我多多保重身子,我这就,我这就不多待了。”
上官箫垂首道:
“母亲走好!”
丫鬟扶着阮夫人缓步出了阮卿的卧室,阮卿又叫了声“姆妈”,阮夫人的背影消失在珠帘之后,阮卿掩面大哭起来。
上官箫走到阮卿床前,早有丫鬟搬了椅子来,他却不坐,柔声对阮卿道:
“卿妹,母亲身上不好,这才不能多陪你,别伤心了。”
阮卿抬头看他,只见他长身玉立,月白色锦袍飘动,腰间一条苏绣腰带,悬着荷包香袋玉佩等小物件。目光移到他脸上,但见他剑眉入鬓,星目炯炯,鼻如悬胆,唇形温柔,真真好一个美男子。阮卿打量了他半晌,心道他这般容貌,倒能与定儒哥哥一较高下,只是他一双眼睛太亮,像两把剑似的,猛一见到令人不敢逼视,不如定儒哥哥的淡定从容。阮卿问道:
“你是谁?”
上官箫露齿一笑,撩衣坐在椅子里,说道:
“你还不认得我?我们都见过两次了,我叫上官箫。”
阮卿眨了眨眼睛,皱眉道:
“这么说,这里是…”
上官箫点头道:
“不错,清冷崖傲然宫凌云殿,从今以后是你的家…”
上官箫话还没说完,便看见阮卿又哭了起来,愣了愣,柔声问道:
“卿妹怎么了,这里不好么?还是身上不舒服?”
阮卿红着眼睛,哭道:
“谁要你把我带上来,快送我回无底谷去,我要回无底谷,我要跟定儒哥哥在一起!”
上官箫隐隐觉得“定儒”这名字有些耳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当下见阮卿哭闹,便笑着安慰道:
“无底谷阴冷荒凉,你可不能再去了。这里也有很多兄弟姐妹与你作伴,不会冷清的。”
阮卿冷哼一声道:
“清冷崖清冷崖,我如今知道这名字实在叫得不错,姑娘不稀罕你们兄弟姐妹,定儒哥哥不在,这清冷崖就清冷得紧!我要回无底谷去!”
阮卿说着就要掀被下床,可是身子到底还虚,两个丫鬟上来将她按回床上,她只觉得浑身瘫软毫无反抗之力,想到定儒,泪水又滚滚流下:他并不知道我上清冷崖来,这会儿找不到我,定是着急得很了,这可怎么办。上官箫听她如此说却并不生气,仍柔声说道:
“你可别再任性了,父亲再生起气来,我也难保你周全。如今你母亲已是傲然宫的女主人,刚生了个小弟弟,叫上官簧,等你大好了便去瞧瞧他吧。还有,我心里仍叫你阮姑娘,口里却是不敢,你在父亲面前别再倔强了,可好啊?你不爱与我们兄弟姐妹作伴,原是应该的,我们彼此不熟悉,也怪不得你。你且住些日子,慢慢的就亲热起来,大家都是极随和的。”
阮卿越听越是惊讶,最后,竟像个傻子一般定定地看着上官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无底谷住了一年,到头来仍要她改姓上官;母亲竟然嫁给了上官寥,还生了个小弟弟。这太荒唐了,太可笑了,太令人无法接受了!
上官箫看着阮卿的神情,也知她一时不能接受,见她眼神哀哀,眼里泪光盈盈,哭一阵,又叹一口气,心中很是不忍。越发轻柔了语气,说道: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可以跟我说,若是闷了,我也可以陪你说笑解闷。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别总想着父亲待你不好,便要与他作对,好么?”
阮卿只听到“一家人”三个字,心里突然想到上官寥一句话就将她许给了上官箫的事,眉头便紧紧地攒了起来,瞪着上官箫,冲口道:
“谁跟你是一家人?我的心事,为什么要与你说?你走开,我不想见到你,不要见到你!”
上官箫一愣,顿了顿,却又笑道:
“好,那我先走了,你好好歇息,我明日再来看你。”
上官箫说罢,起身离去,丫鬟上前撩起珠帘,他略躬身,身形已隐在珠帘之后。
阮卿又挣扎着想要起身,但手脚实在一点力气都没有,挣脱不了丫鬟的钳制,折腾半晌,阮卿只觉得浑身冒汗,头晕眼花,气喘微微,只得乖乖躺好。无力地闭上眼睛,眼前是定儒淡定如水的容颜,一看之下便让人觉得无比安心。他专注地瞧着她,眼里是镜湖一般的温柔,他说:“我只怕你不跟着我。”
只怕你不跟着我,只怕你不跟着我…阮卿反反复复想着这句话,心中无限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