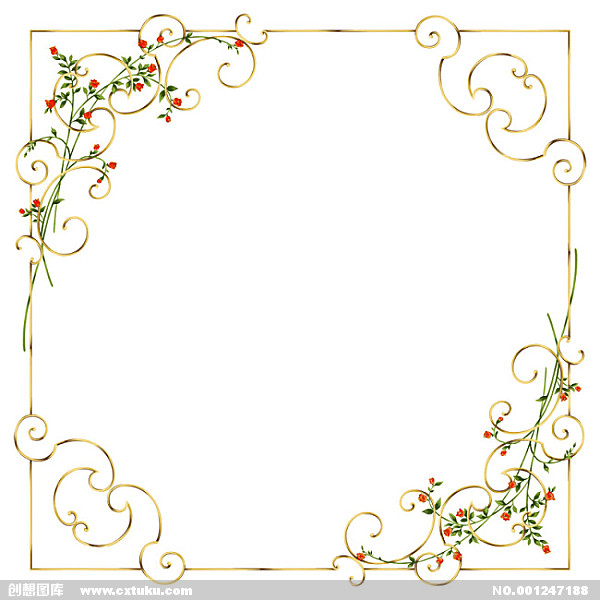阮卿不吃不喝不睡,整整在湖中泡了四天四夜,血才渐渐止住。在这四天四夜里,她也记不清自己流了多少眼泪,叫了多少声妈妈。穿好衣服爬上岸,觉得浑身软得像一团烂泥,也没有力气运功将身上的水蒸干。她拖着湿淋淋的身子沉重地迈步走去,走不了几步便天旋地转,瘫倒在地,晕厥过去。
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软软的细草上,鼻子里闻到烤鱼的香味。阮卿挣扎着坐起身环顾四周:温暖干净的小山洞,两张细草铺成的床,一张石桌,两张石凳…却不是定儒的家是哪里?阮卿心头一热,正想着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耳边却听到定儒的声音:
“卿儿,你醒了?”
他缓步走到阮卿面前蹲下,细细打量她:
“脸色仍然苍白得很,该吃些东西了。”
阮卿怔怔地盯了他半晌,十七岁的定儒看起来与四个月前并无太大差别,只是更加高大了些。他这般温言慢语,亲切淡然,一如往昔,仿佛他们的离别只是昨天的事。阮卿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一腔的话不知从何说起,愣愣地掉下泪来。定儒温柔一笑,道: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阮卿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哀哀地望着定儒,断断续续地道:
“定儒哥哥,你…你还…认得我?”
“险些不认得。”定儒微笑的神情中流露出些许忧郁,“卿儿,你这些日子究竟遇到了什么?”
阮卿心中一紧,豆大的泪珠颗颗滑落,伸手捂住脸大哭起来。定儒默默地看着她,并不说话。阮卿哭了半晌,才抬起脸来,道:
“定儒哥哥,我…我心里好难过,我才十一岁,可是…可是…”她低头看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胸,突然想到定儒是男子,脸上猛然一红,捂住脸大叫道,“我…我变成怪物啦!”
定儒微微一怔,才明白她的话,眼见阮卿哭成泪人一般,也不知如何安慰。他乍一见到阮卿,确实惊讶不已。他将她抱回山洞,守在她的身边,她娇美的容颜就近在眼前。眉若黛青远山,鼻若琼瑶玉峰,唇若朱丹凝脂,还有那渐渐显山露水的身段,无一不在激荡着少年男子的情怀。他听得阮卿说自己变成了怪物,心道:你不是怪物,你好美!口中却说不出来,只怔怔地瞧着她。良久,定儒微微笑道:
“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再好好讲给我听。”
吃饱了肚子,阮卿觉得精神好了许多,其实她只是因为四天四夜不吃不喝,这才虚脱晕倒的。阮卿恨透了上官寥,又受了镜湖女妖的怂恿,决定要杀死上官寥。如今她又得知定儒也是上官家的人,本不想再与他有所牵扯,可是重逢之后,心中满腔的信任和依赖,迫使她将事情一五一十毫不遗漏地告诉了定儒。定儒听后,只是沉思,半晌不语。阮卿犹豫良久,开口问道:
“定儒哥哥,你真的姓上官?你与傲然宫主上官寥是什么关系?”
定儒道:
“不过是同族亲戚罢了。”
阮卿点点头,不再多问,她一向对定儒深信不疑。想了想,又笑道:
“原来你的名字叫上官定儒!”
定儒微笑不语,阮卿又道:
“从前我恨死了上官寥,听到‘上官’两个字就觉得无比讨厌,可是这两个字加在你的名字上,我却觉得不那么讨厌了!”
定儒瞧了她一眼,但觉她的笑容柔媚动人,明艳不可方物,目光竟别不开去。阮卿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问:
“筝儿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女妖一听到她的名字,就那样动容?”
定儒道:
“筝儿是上官寥的长女。”
“哦!”阮卿轻轻答了一声,笑容立刻明朗了许多,心中没来由的松了口气。上官筝,上官定儒,不是兄妹便是姐弟了!转念一想,女妖如此关注筝儿,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筝儿是女妖与上官寥的女儿?脑中一闪过这个念头,阮卿立刻大大摇头。若女妖与上官寥曾是夫妻的话,怎么可能处心积虑地要杀他呢?她年纪尚小,又不懂情爱之事,只觉得夫妻恩恩爱爱,乃是天经地义,却不知世上还有“怨侣”。
定儒沉吟了良久,对阮卿道:
“卿儿,如今你内功已有些底子,从明天开始,我便教你轻功。”
阮卿点点头:
“早就见识过上官家的绝世轻功了,但若是别人来教我,我偏不学,只有定儒哥哥你教我,我才愿意学呢!”说罢,抿嘴一笑,笑容如涟漪一般渐渐荡漾开去。这几句话撞在定儒的心坎里,他不由得心中一荡。
第二日起,定儒便开始将轻功教授给阮卿。
“这门轻身功夫叫做‘会当凌绝顶’,出自唐代诗人杜甫《望岳》中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阮卿抚掌笑道:
“好大的口气,怪道上官家要在长白山之巅立足,还要建一座‘傲然宫’,便是傲视天下,一览众山小的意思了!”
定儒点头道:
“不错,傲然宫闻名于中原,多半是借了绝世轻功的荣光。”目光与阮卿的目光相接,讲解道,“这轻功原不难学,但是三百年来,中原武学之士绞尽脑汁盗取‘会当凌绝顶’的秘籍,却仍然练不会。其中原因就在于,练这门轻功,首先要练寒凝诀。只有体内积蓄了三四成寒凝诀的内力之后,才可练此轻功,否则就好像舞蹈一般,有形而无实。可是寒凝诀的内功心法,却是口头相授,代代相传,铭刻在每一个上官家子孙的心里,任谁也偷不去。”
阮卿眼珠一转,笑问道:
“那么,如果筝儿嫁了人,她丈夫要她说出寒凝诀的心法,她丈夫又不姓上官,这可怎么办呢?”
定儒道:
“上官家的规矩,女儿可以学习寒凝诀,但是在嫁人之前,必须由宫主亲自废掉全身武功,用冰玲珑封住哑门,才可出嫁。”
阮卿倒抽了一口冷气,瞪大了眼睛问道:
“这么说,上官家嫁出去的女子,全部都没有武功,而且都是哑巴?”
定儒点点头,阮卿变色道:
“好狠毒的手法!”
定儒道:
“所以上官家的女子,为免此灾难,往往终身不嫁。”
阮卿又道:
“即使不能言传身教,那将心法写下来总可以吧?”
定儒道:
“上官家严禁女子习文!”
阮卿吐了吐舌头,心想若是被上官寥知道她练了寒凝诀,不将她大卸八块才怪。想了想,又问道:
“那徐叔这些人也不姓上官,怎么会用这门功夫呢?”
定儒笑了笑道:
“上官家支脉繁盛,有些支脉人员犯了错,便被逐出上官家族,冠上一个外姓,贬为奴隶。可是寒凝诀的心法却仍流传了下来。这些人为傲然宫的一等奴仆,世世代代无法翻身。”
阮卿道:
“这么说,清冷崖上的奴仆倒有许多曾是上官家族的人了?”
定儒点点头,道:
“徐、陈、董、余四大姓皆源出上官家族。”
阮卿点点头,怔怔地望着远处,没有再说话。定儒便言归正传,开始讲解会当凌绝顶的步法要点。
会当凌绝顶的轻身步法共有七种,所以又被武林中人称为“七步轻身”。这七种步法分别为旋、腾、掠、纵、迈、翔、影,每种步法又有若干种变势,组合在一起幻化出无数种身形。背阮卿上清冷崖的徐叔所用的是七步轻身中的“腾步”和“纵步”,而上官篌用的则是“影步”。这些步法练习起来需要深厚内力,若没有练过寒凝诀的人,只要内力深厚,也可以练习,只是事倍功半罢了。阮卿忽然想起镜湖女妖那如鬼魅般的身形,在她还没看清楚之前,脸上已吃了她两掌,只怕也是七步轻身中的“影步”吧。女妖内力深厚,但仍无法将这门轻功练全,是以上不了清冷崖。寒凝诀的内功心法与一般内功相反,是将十二经脉气血倒转运行,是以丹田常常空虚。在施展会当凌绝顶之时,空虚的丹田就好似鸟儿的空心气囊一般,可以增加身体在空气中的浮力,自然大有裨益。
阮卿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将七种步法和各种变势一一记住,再往下学,却是一层比一层难。七种步法中最容易的属旋步与影步,旋步主要用来逃脱敌人的钳制,影步则用于追击敌人。这两种步法的诀窍只有一个字:快。而内功练到一定程度,要达到这样的速度已是不难。两个月后,阮卿已练熟了旋、影两种步法,但要说运用自如,却还差着一些。接下去要练的便是腾步与纵步,顾名思义,这两种步法主要是登高之用。腾、纵两种步法对内功和耐力的要求颇高,也是这门轻功中难以达到的境界。
阮卿练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丝毫成就,心中不禁有气。又是一日练到天色擦黑,阮卿早已气喘吁吁,定儒却仍在要求她调整步伐,深深提气,奋力再练。阮卿黑了脸,站在原地不动。定儒走上前来指点她的步法,阮卿冷哼一声,提一口气,飞快地离地,无数个漂亮的旋身,人已到了半空中,将定儒甩得老远。定儒一愣,立刻脚下一点,瞬间身子已到了半空。阮卿还没看清楚他的身形,腰上一紧,身子倏然一沉,定神看时已被他抓了下来,稳稳地落在地上。七步轻身中的旋步与影步,被这两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定儒勾唇笑道:
“好啦,今儿不练了。”
阮卿柳眉一竖,冲口道:
“很好玩吗?你功夫好,就这般戏弄我!”
定儒凝神看她,夜色下她双目炯炯有如星光,脸上浅嗔薄怒,更添娇艳,当下不由得看得痴了。定儒心细如丝,早已看出阮卿面有倦色,但是他年纪尚轻,急于求成,没有顾及到阮卿的能力。这会儿阮卿大发脾气,他却无措了。半晌,他才说了一句:
“我可没有戏弄你。”
阮卿冷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定儒跟上,道:
“卿儿累了,回去吃饭吧。”
阮卿气往上冲,转身对着定儒大叫道:
“我累,我累,你累死我算了!我就是笨,我就是练不会!整天果子烤鱼,吃得我快要吐了,你自己吃去吧!”
定儒顿时愣在当下,回过神来的时候阮卿早已走远。定儒叫了两声“卿儿”,清冷的夜里只听到一些回声。他怔怔地站了半晌,心中隐隐有些酸楚,来来回回想着阮卿的话:她发这么大脾气,想是累得很了,我却没有早些让她休息,只顾着催她练习。不知道她身子经不经得住,若是伤了元气,倒是大事了。原来她不爱吃果子和烤鱼,每每见她吃得津津有味,原来只是为了讨好我。
定儒一面想一面往回走,肚子饿得很,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夜已深了,定儒心中又添担忧:不知她去了哪里,饿坏了可不好。又等了半日,仍不见阮卿回来,定儒叹了口气,和衣而卧:等她消了气,自会回来吧。
睡到半夜,定儒隐隐听到轻轻的抽泣声,立刻惊醒了,问道:
“卿儿?”
月光下一个纤细的倩影抱膝坐在他的面前,却不是阮卿是谁。阮卿抬眼望着定儒,眼里泪光闪动,晶莹剔透,如清晨荷叶上的露珠一般,颤悠悠地闪着光。定儒不由得心中一紧。阮卿哽咽地道:
“定儒哥哥,我错了,我…”
定儒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柔软了,微笑道:
“卿儿爱吃什么呢?从来也没跟我说过,你现在告诉我,以后一定做给你吃。”
阮卿心中猛然一荡,哑然一瞬,愣愣地瞧着定儒。他眼中的怜爱似要涌出,好似父亲的眼神一般,带着宠溺,温柔,专注,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叫她生生别不开目光。良久,阮卿轻轻将头靠在定儒怀里,柔声道:
“定儒哥哥,你待我真好,我以后都听你的话,再不发脾气了!”
定儒笑了,伸手拍了拍阮卿的背脊。阮卿抬头专注地看他,湿润晶亮的美目犹如两泓泉水,定儒心中一股莫名的悸动,捧起阮卿的脸,低头在她脸颊上亲吻了一下。阮卿脸上一红,吃吃地笑了两声,道:
“定儒哥哥喜欢我么?”
定儒的手掌轻轻摩挲她的脸颊,柔声道:
“喜欢。”
阮卿低头,黑暗里看不清她的笑容,她侧身在定儒身旁躺下,闭上眼睛。定儒怔怔地看了她半晌,将毛皮披风盖在她身上,然后仰面躺下,闭上眼。两人均很快进入了梦乡。
之后,阮卿果然再无怨言,每天刻苦练功,定儒却更为体贴她,多给了很多休息的时间。那日,两人坐在山石上歇息,阮卿笑向定儒道:
“定儒哥哥,我心里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说,可是你好像有很多事不愿意告诉我。”
定儒笑问:
“比如?”
阮卿嘟起嘴,一件一件说来:
“第一件,你连姓什么都没告诉我,要不是我自己知道了,你这辈子都不打算说了,是不是?第二件,你从来不在我面前练功,要不是你主动教我功夫,我还当你是个文弱书生呢。第三件,筝儿的事为什么也不跟我说说,害我在女妖面前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该说什么。”
定儒温柔地笑着看她,静静听她说完,只觉得能这样看她听她说话,已是十分快活的事。阮卿回来之后,由于身体上的巨大变化,使定儒常常忘记她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不自觉地被她的少女气息吸引。阮卿心中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对定儒更添一分依赖。两人之间不知不觉愈加亲密起来。定儒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于男女情事上已懂得,眼见着阮卿日渐娇美动人,对他又是亲昵,心想两人彼此喜欢,将来等阮卿长大了,定是要结为夫妻的,于是对她更为爱惜。
阮卿嗔道:
“喏,这三件事,你还想赖吗?”
定儒笑道:
“以后,我什么都告诉你。”
阮卿敛眸一笑,长长的睫毛盖了下来,称着吹弹即破的肌肤,美得慑人心魄:
“这还公平些!”
定儒想了想,挑眉说道:
“你还说我,你不也有事没告诉我么?”
“什么事?”
定儒道:
“这些日子偶尔见到一男一女两个身着锦衣的孩童出现在谷底,似乎在找你。”
阮卿秀眉攒起,冷哼道:
“哼,上官寥生的两个小恶魔,休想抓到我!定儒哥哥,下次他们再来,你可要帮我,那个叫上官篌的狂得很,武功也不差,可别让我被他们抓了去。”
定儒只是微笑点头,阮卿看着他笑,也笑了出来。
“嗳嗳嗳,小姐姐,你怎么又骂人,我什么时候惹了你,竟变成小恶魔啦?”冷不丁地从两人头顶上传来一个女童的声音,正是上官笳。紧接着,是上官篌的声音说道:
“跟她废什么话,她今儿有帮手,我一样抓得着她!”
阮卿变色道:
“不好,说曹操曹操到,这两个小恶魔又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