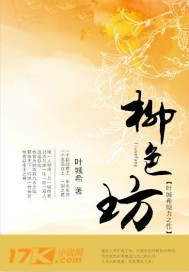上官箫挟着阮卿登上了灵岩山顶,才将她放下,阮卿站稳身子,定睛一瞧,眼前的人却不是上官箫是谁。她眨了眨眼问道:“箫哥,真是你,刚才为什么不回答我?”上官箫似笑非笑,眉宇间没有了一贯的温柔:“我只道你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阮卿呆了一呆,又问道:“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上官箫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不答反问:“你的锁片呢?”那锁片是阮卿十二岁生日的时候,上官箫赠与她的,她戴了两年,却在江南随手将它送给了一位陌生少女。阮卿愣了片刻,才想起那锁片的去向,自觉有愧,答道:“弄丢了。”
上官箫不依不饶,仍问道:“丢在哪了,怎么丢的?”阮卿脸上一红,低头轻声道:“丢了就是丢了呗,知道丢在哪儿不就找到了吗?”上官箫轻笑了两声,说道:“是不是,丢在我这儿了?”阮卿抬头一看,只见上官箫的手里拿着的,正是她戴了两年又随手送人的锁片。她想不通这锁片何以会在他的手中,也无法再圆这漏洞百出的谎言,她通红了脸怔怔地望着上官箫。他依旧英俊,气宇不凡,但眼中的目光却是她从未见过的,思念、幽恨抑或悲伤?这样的一双眸子镶嵌在他雕琢一般的脸上,顿时令他整个人都阴暗了下来。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的一个笑容几乎能让长白山的积雪融化,让冻僵了的心灵回温,可是现在,他的笑容在哪里,他的温暖在哪里?
上官箫勾起的唇角微微僵硬,那笑容苦涩而寂寞,他幽幽地说道:“这么多年,你一向刁蛮任性,而我千依百顺,你知道是为什么?只因我总以为你是与我亲近才这样,客客气气倒显生分,哪里想到,原来你是厌弃我。只因我高看了自己,总以为世间男子虽多,却无过我之人,况我这般待你,你岂有不动心之理?如今想来,我真是痴傻疯癫,病得不轻!”
阮卿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并不厌弃上官箫,而上官箫的确是世间男子中之佼佼者,可他就是走不进她的心里,她也无法。也许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而迷恋一个人却是完全盲目的。有些人可以痴在心里,面上装出平静淡然的神情,而有的人却忍不住要将自己烈火一般的热情灌注在对方的身上。上官寞是前一种,阮卿和上官箫是后一种。
两人在风里站了许久,谁都没有说话,夜幕渐渐降落,将郁郁葱葱的灵岩山罩上了一层黑丝纱衣。阮卿伸手拢了拢自己的衣领,以轻不可闻的声音说道:“箫哥,我走了,你住在哪间客栈,改天我来看你。”上官箫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并不回答。阮卿瞧了他良久,缓缓地转过身去,迈步离开。才走了两步,上官箫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就住在这里,从今往后,我们都在一起。我不要你来看我,我要你守着我。”阮卿一愣,不禁停下脚步,不防上官箫身已飞至,再次挟了她掠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