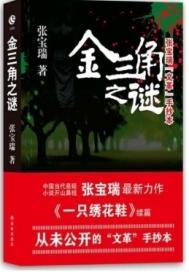绿衣女子气得俏脸通红,阮卿嫣然一笑,心道:看你没了钢鞭还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鱼肠剑出鞘,一招“吴楚相争”迎面向她递了过去,直取绿衣女子一对亮晶晶的眼珠子。绿衣女子一凛,纤腰反折,矮身躲过,左手擎住阮卿皓腕,这才发现她臂力甚弱,如大病初愈般。她唇角一勾,道:“小妖女恁地歹毒!”阮卿笑道:“小魔女半斤八两!”
绿衣女子冷哼一声,右手伸出两根手指,定儒叫道:“云门、曲池、合谷!”阮卿一愣,电光火石间已明白过来,这女子要点她右臂和虎口上云门、曲池、合谷三穴,迫她短剑脱手。阮卿立刻剑锋回撩,作势要挑绿衣女子左手手筋,那女子心中害怕,不由自主左手一松,放开了阮卿手腕,右手两指再想点她穴道,已然来不及。
绿衣女子怒道:“说了不许相帮!”定儒道:“我不过说了三个穴道的名称,既没说你要点穴,又没叫她当心,何来相帮之说?”绿衣女子哑口,但见阮卿笑得洋洋得意,双靥生霞,心中忿然,一咬牙又再攻上。两人堪堪拆了十余招,阮卿仗着鱼肠剑短小锋利,对方始终近不了她身。
二十招已过,鱼肠剑法早已使了几个来回,绿衣女子看出了门道,勾唇一笑,寻了个破绽绕至阮卿身后,伸指便点。定儒叫道:“委中、委阳、昆仑!”这三处穴道分别在膝关节窝和小腿肌肉中点,被点中立刻小腿酸麻,屈膝跪地。阮卿抬腿两步登上桥栏,反身将手中的短剑刺出,这是一招“拜别慈母”,绿衣女子身形甚是灵活,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一招,可是她精妙的点穴手法却又被化解了。
如此四五个回合,每当绿衣女子要点穴时,总被定儒叫破。阮卿原本武功逊她甚多,可因为她失了钢鞭,定儒又在旁叫穴,是以始终与阮卿不相上下。两人斗了一顿饭的功夫,鱼肠剑法招式甚少,已被绿衣女子摸了个清,阮卿每出一招,总被她提前撞破。阮卿重伤甫愈,此时已体力不支,绿衣女子却是越斗越勇。
阮卿心道不妙,银牙轻咬,素手一扬,一颗冰玲珑打了出去。只是她功力甚弱,冰玲珑划过绿衣女子的脸颊,打不进穴道里,却掉在地上。绿衣女子一呆,伸手抹了抹被打痛的脸颊,手指上沾了些血痕。若伤在别的地方,这等小伤口自然不值什么,可是偏偏伤在她白皙的俏脸上,等于叫她破了相。
绿衣女子顿时大怒,阮卿心中害怕,辩解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要毁你容,我本来要打…”话音未落,只听得“嗖”地一声,紧接着是绿衣女子的惨声痛呼,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接着阮卿的话道:“这儿!”阮卿一愣,她本来是要打两锁骨间的天突穴,让那女子回去好好咳嗽半个月,谁知手一抖就打偏了,可是此时,那颗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冰玲珑正打中了绿衣女子的天突穴。瞧此人的手法功力,那女子回去可能要咳嗽气喘半辈子。绿衣女子眼中的目光如利刃般射向阮卿,阮卿慌忙摆手:“不是我打的,你别找我报仇,真的不是我打的!”
正在此时,一个白影如旋风般袭至,掳了阮卿便走。这身形实在太快,快到连此人是男是女都没看清。定儒亦不示弱,将手中的九节鞭随手一甩,恰在那绿衣女子纤腰上绕了两圈,即刻足踏影步追了上去。两人轻功不相上下,堪堪追了一顿饭的功夫,小桥流水的江南姑苏,只看见两个白影一前一后,忽而飞踏屋脊,忽而足点碧水,忽而翻腾跳跃,向着远处疾飞而去,瞬间消失在烟云薄雾里。
阮卿只觉得天旋地转,根本无法转过脸去瞧那人容貌,鼻子里却闻到他身上的香味。这香味很是熟悉,是上官箫惯常戴的香囊的味道。阮卿问道:“箫哥,是你吗?”上官箫故意不答,他早已来到江南,几次三番瞧见阮卿与定儒亲亲密密,心中又酸又怒。此番又见阮卿与绿衣女子相斗渐落下风,而定儒袖手旁观,他怒气直往上冲,一个没忍住便出手封了那女子的天突穴,掳走了阮卿。
天色将暮,天边一片醉人的晚霞,将小巷碧水的姑苏晕成了红色。定儒追着上官箫,两个白影跑遍了大半个姑苏城,上官箫怀中挟着阮卿,速度渐渐慢下来。定儒早已猜到掳走阮卿的是傲然宫的人,否则轻身功夫不会如此出神入化,再一推测,便认定是上官箫。
一想起上官箫,他便心中怅然:他定然不会伤害卿儿,或许他只是将她接回去,毕竟他们是未婚夫妻,卿儿心中若情愿跟着他去,我这般追着人家又算怎么回事?如此越想越是泄气,脚步竟渐渐缓了。上官箫的身影转过郁郁葱葱的小山丘,定儒追上去的时候已不见了他踪影。
他立在原地愣了半晌,心中顿觉空空荡荡。山风撩动他的白袍,他一双如水的眸子怔怔地望着远方,竟不知望向何处。他想起在无底谷,上官箫将重病的阮卿带走,自己就站在背后,却不敢阻拦。当年他是一无所有的乞丐小子,如今的他已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为什么,他仍是不敢,仍是裹足不前?他敢在无底谷上官寥的眼皮子底下韬光养晦徐图大计,敢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江南隐居修炼,敢纠集江湖群豪同剿傲然宫,这世上的事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可他就是活在上官箫的阴影里,他喜欢阮卿,但不知她心里怎样想,即使她说了,他仍不信。只要上官箫一出现,他便觉得自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阮卿的心里如果爱着上官箫,叫他这一番痴心却情何以堪?定儒站在山丘上,迎着山风,夜幕渐浓,晕染了他一袭白衣,他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苦涩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