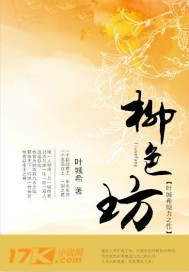阮卿带着定儒游遍虎丘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吴王阖闾和夫差父子的故事。说到馆娃宫,便说起越女西施;说到平门,便说起贤相伍子胥;说到专诸,便说起鱼肠剑,说起专诸刺王僚的苍凉故事。阮卿解下腰间的鱼肠剑,舞起了家传的鱼肠剑法:“生死一剑”、“穿衣透甲”、“功成身死”…如血的夕阳落在她的身上,勾勒出她侧脸的轮廓,山风撩得她衣摆飞舞,她跳跃力刺,纤细的身形扭动伸展,让他不禁想起那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定儒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这一刻他真的相信,她是属于他的。他忘记了悲惨的遭遇,忘记了仇恨,忘记了傲然宫,忘记了上官箫,他的心里只有她。阮卿舞毕了最后一招,还剑入鞘,向着定儒嫣然一笑,头上的束发金冠映着夕阳,黄澄澄地闪着光。定儒心中怦然一动,轻轻牵起她的手,问道:“冷么?别站在风口里了。”阮卿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比她更凉,她轻声笑道:“你比我冷,我给你捂捂吧。”定儒情不自禁地揽她入怀,轻轻叫了声“卿儿”。阮卿甜甜地笑着,等着他说下去,谁知他却只是叫了她一声。可是他的心里,何止千言万语。他不知该不该说,从何说起,说了又会如何。他想告诉她他的身份,他与傲然宫的仇恨,他的所有思想和经历,以及他对她难以自拔的迷恋。如果她没有识得上官箫,他定然丝毫不对她隐瞒。他答应过她,以后会什么都告诉她,可那是在无底谷,在上官箫将她带走之前。他无法控制自己怀疑她,就像无法控制地喜欢她一样。有朝一日,如果她知道了他所有的秘密,却带着绝世的美丽笑容站在上官箫的身边,他会怎样,他不知自己会怎样。越是爱,越是怕,越是无措。
阮卿深深地沉浸在甜蜜里,丝毫想不到定儒的心思竟是这般复杂矛盾。她紧紧地依偎着他,又说起了范蠡与西施同游西湖的故事,语气里满是艳羡。她想起了长白山,想起了天池,想起了他给她讲的那些故事。阮卿微笑着,幽幽地说道:
“定儒哥哥,我还记得你给我讲天池的故事,天池里有一种鸟儿,头上的羽毛是白色的,常常成双成对地在水里游弋嬉戏,那叫做什么鸟?”
定儒轻声答道:
“那是鸳鸯。”
阮卿的声音更为轻幽,缓缓地问道:
“头上的羽毛是白色的,那又为什么?”
定儒觉得自己的心都酥软了,柔声答道:
“鸳鸯相守,白头偕老。”
阮卿低眉一笑,说道:
“你说范蠡与西施,像不像一对鸳鸯?”
定儒轻轻地“嗯”了一声,阮卿募然红了脸,声若蚊吟地道:
“我们何时也去同游太湖,做一对鸳鸯?”
定儒听见了她的话,却只当没有听见,他深深地拥抱她,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芳香。真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回到纷繁扰人的俗世中。就像范蠡和西施一样,就像天池的白头鸳鸯一样,相携嬉戏,无忧无虑。只羡鸳鸯不羡仙。
天已渐渐地暗了下来,夜风拂动着两人的衣摆,他们四手交握,胸膛紧贴在一起,几乎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阮卿的脸又红了,红得发烧,红得滚烫。她抬头将嘴凑到定儒的耳边,轻声说道:
“定儒哥哥,我想嫁你!”
定儒的心“突突”地跳,他多想将她抱起来疯狂地欢呼,可是他心思百转,数千次的来来回回,进退徘徊,终究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道:
“孩子话!”
阮卿想要争辩自己不是孩子,却娇羞得不敢说下去,半晌,她才低头幽幽地说道:
“我终会让你知道,这不是孩子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