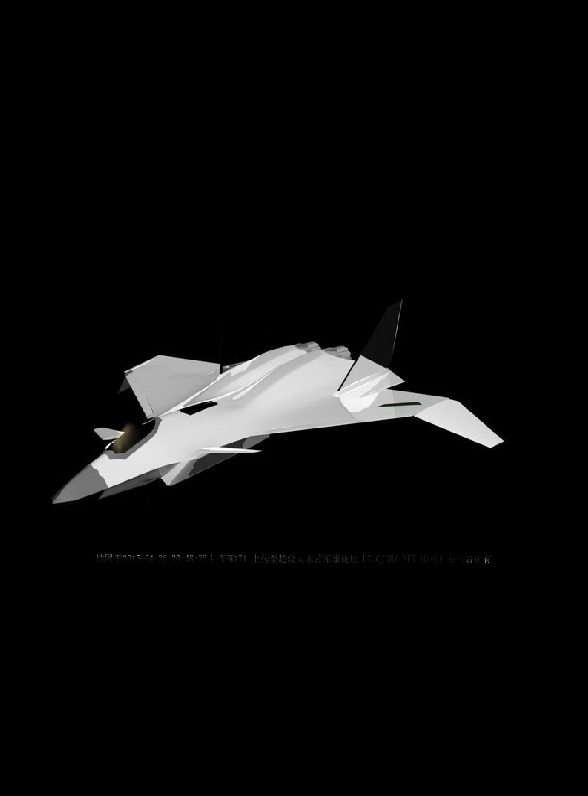永宁元年四月初十,王师挥师北进,遇敌于永川,王师锐不可挡,挫敌锐气,退敌200里于关外……
王师寻踪追击敌军,直入敌军属地,然敌擅游遁之术,终不能寻其主力……
五月初六,王师久战难克,行旅已疲,敌军乘隙狙击王师粮草,王师孤军深入敌境,处境堪忧……
草原的夜色沉静如水,五月的原野上早就铺满了青草,此刻和着草原上独有的春风抚过来,让张凌被战报冲昏了的脑袋稍稍安定了下来,再深吸一口香风,张凌大步跨入中军营帐之中。
“禀将军!属下张凌来见!”
位于中军帐主位中的魁梧男子闻声略抬了抬正抚在一只枭身上的手,含糊的“吾”了一声,却没有说话。
张凌却似乎很习惯这样的沉默,直了起身也不发问,只往军帐中一个晦暗的角落再施了一礼……
“咳咳……”那团隐在角落里的阴影似乎动了一下,只是立刻便传来一阵嘶哑的咳嗽声。
张凌听到这咳嗽声,垂下的手,似乎动了一下,但是即刻便忍住了,更敛了眼色,静立在一旁。
那团影子被挡在两片帷布的褶皱里面,其实若不仔细看,倒实在看不出中军帐中竟还有这样一个阴瑟的角落,更想不出这里竟还藏着一个人。只是那人似是十分的虚弱,这会儿也不过只是略挣扎了一下,便不住地咳嗽低喘起来,
但是这中军主位上的男人人却似乎听不到那人的咳嗽低喘,一只手一直不时轻拍一下那只枭,就是张凌也再没有半点触动的表情……
也不知过了多久,大帐之中窒人的咳嗽和低喘声渐渐平缓下去,那人略撑了上身,只是似乎更加虚弱,整个人都倚在身后厚重的枕头上面,脸虽然还是隐在暗地里,但是借着灯光终于能看出个大概来——算是很秀雅的一张脸,眼尾斜长,眉头微微颦着,应该是极苍白的脸色现在隐在黑暗里面,略略显出青色来,整个人说不出的疲惫……
“张将军刚从左营口回来,那边情况如何……咳咳……”那人略休息了一会,开口问道,只是嗓音沙哑,显然是身染咳症已久。
张凌先望了一眼那位主位上的男人,然后躬身答道,“等我赶到的时候,左营那边的突袭已经结束。我们这边并没有太大伤亡,只是步兵营的帐篷废了几顶。只是……那些蛮人只怕不会就此罢休,毕竟……”
那个病弱已极的男人撑开一直眼睛看了一眼张凌的脸色,再瞟一眼那个主位上的人,嘴角微微上扬,竟然是笑了……
张凌看着眼前这个几乎一阵风就能吹垮的男人嘴角慢慢扬起,已经泛白的嘴唇缓缓拉成了一条弧线,略发青的脸色竟然诡异的透出红色来,只觉得什么说不出的东西顺着那弧线律动开来,竟让那疲惫的似乎要死去的人无端的变得邪魅、甚至妩媚起来……
“嘎!”
只是那笑容也只是一瞬间而已……张凌只听得那枭一声诡异的嘶鸣,再抬眼,那个虚弱的男人脸上已经被鸟爪划了一条血痕,殷红的血液从男人苍白的脸上滴落下来,竟衬的那张脸异样的残艳起来……张凌觉得心跳似乎乱了一拍,再抬眼看时,那男人的脸色瞬间便黯淡了下来,眉头颦了更深了些,一双手死拽着身下的被褥,却是倔强的硬挺着,不肯露半点声响。
“张凌……”
“在!”跟随这位主帅十五年,张凌知道这时候再容不得他有半点的分心,更何况那个男人的生死荣辱原就不是他可以插手的。
“你知道这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么?”
张凌听不出这声音中的喜怒,却是双膝一颤,跪了下去,“属下自知罪该万死,只请将军依律处罚,属下断不敢有半句多言!”
“张凌,你真是越活越糊涂了,你一个副将,既不是你押的粮草也不是你下的军令,你能有什么错。你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但是就算丢了你的命也未必保的了我……”
“将军……”
“张凌,我这里有一封信,你先看看吧。”
张凌双手接过那个牛皮信封,抖开信纸……半晌抬头,眼色却近似红色,目光闪动,良久才重重跪下,“不瞒将军,属下本已决议为将军赴死,以解此次之危。如今既得了此计……属下不才,不能断朝政是非,但若真如信中所言,将军此次只怕难以全身而退,更何况,深入敌境而粮草被截乃兵家大忌……属下跟随将军多年,自知将军一代名将,风骨天成……只是这手下数万人的生死荣辱可是都握在将军之手……”
张凌追随容德日久,他和这个熊一样的男人一起经历过生死荣辱,亲眼看到过这个男人身上天神一样的荣光,也知道这个男人身上狮子一般不容侵犯的骄傲,如今且不论这封信真假如何,在这个男人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吧……
“果然连你都这么说……罢了……你便带五千轻骑至屯谷看守吧,到时只管听我将令就是……”
“是!”张凌只觉得身上一轻,再顾不得其他,马上领命而去了。
目送着副将出去,容德把手里的枭一抛,朝那团阴影里面走了几步,缓缓坐在那人的床沿上,过了一会竟掏了手帕为那人擦了擦脸上的血渍,一面说,“允忝,你看我是不是又老了一点,否则怎么会就这么心甘情愿的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还是,我看起来已经虚弱到不能够反击了……”
那个被叫做允忝的男子,淡淡看了他一眼,“你若真有那么一天,还能容我活着么?只是这次你似乎招来了一个好对手呢……”
“是么?说起来还真是期待啊,很久没有和你一样好的对手了……允忝,我很怀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