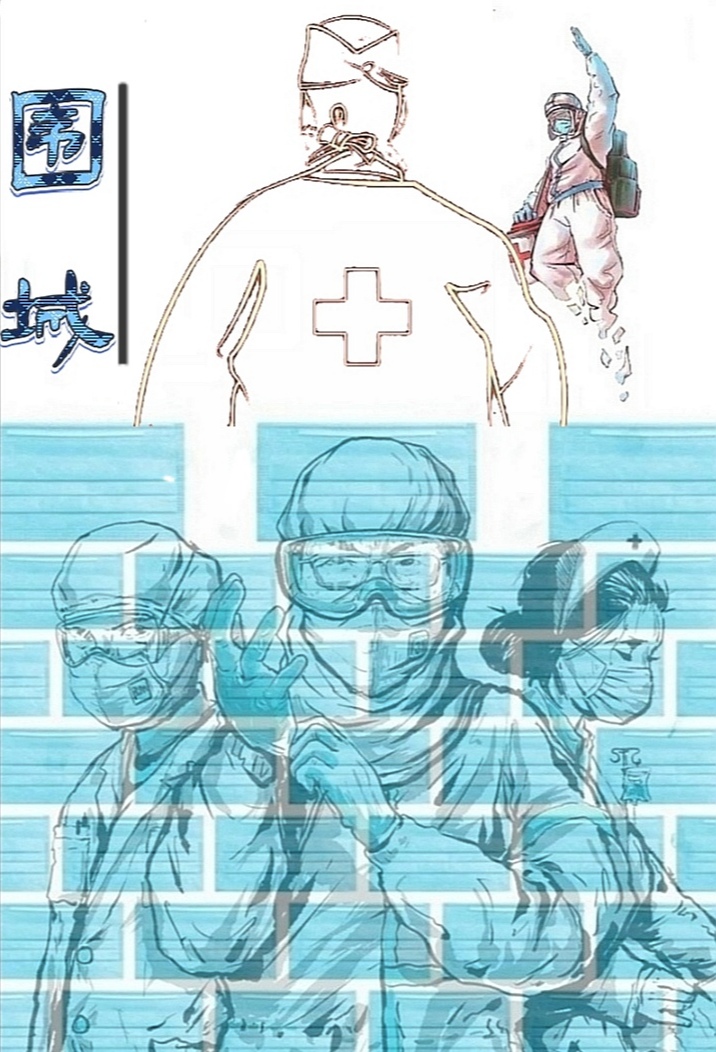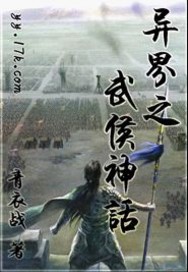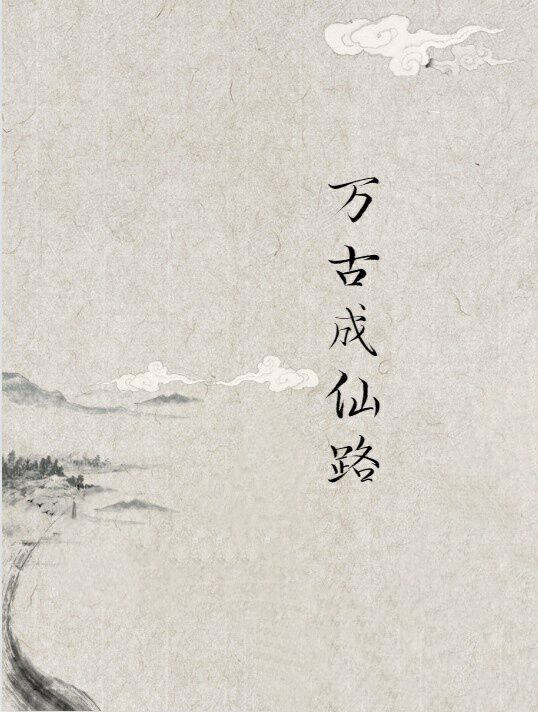厂门口小卖部,范斌和张河正在啃烧饼,旁边就是一个卖烧饼的摊子,我从范斌提着的塑料袋里拿过一个烧饼,告诉他们陆明今晚有事,答应明天晚上可以练球。不一会儿,曹先锋、包大有还有李小松也陆续到了。最后,还来了一个人。
怎么是他?
只见张涛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个足球。我便问范斌怎么回事?范斌告诉我说:“昨天中午他们几个练球,碰到了张涛,他就过来同我们闲聊了几句,并说第二天晚上练球,如果有空一起来看看,本以为只是说说,没想到还真来了”,我心里顿时感到腻歪,把眼光移到烧饼摊儿上。
张涛上来同我们打招呼,我也礼貌性的点点头。他说贾春本来就让他有空的时候组织一下训练,而最近忙没有时间,我心想,清闲的办公室忙个屁。但脸上还是面无表情。人齐了,就直接奔电影厂的技校操场,几个人一边走一边吃着烧饼,张涛说他在办公室垫吧了一口,我们也就不客气,省下了两个烧饼。
来到操场,我换上了运动短裤和训练鞋,他们都没带短裤,只是穿工作服裤子或平常穿的裤子,鞋子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鞋。张涛看看我,没有说话,从往兜里拿出足球扔给我,我直接用脚停住,十足的装逼味道。
先做些简单的准备活动,压压腿、伸伸腰,活动全身关节。然后,围成一个圈儿,把足球在圈子里踢来倒去,不一会儿就感到索然无味。我看到操场另一侧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看年纪应该是这个学校的,于是,跑过去邀请他们对阵一场,几个学生也爽快的答应下来。
一直快到天黑,几乎看不清足球了,才结束这次小场比赛。我尽管踢进两个球,也懒得问输赢,便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第二天,踢球的装备都没带,实在不愿意同张涛为伍。想起前两天的密谋,本来打算先放下一段时间,不知咋地又躁动起来。想想英雄救美,还有安塞冬的美人计,脑袋里一团浆糊。
下午的时候,许姐说有我电话。拿过电话,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你猜我是谁?”我一听回道:“鬼?”刘荣荣在电话道:“我打死你,然后咯咯笑起来,”我问:“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她回道:“今天可以出去玩儿,你下班过来找我,记得啊。”然后把电话挂了,好像我一定会答应似的。
好吧!猜对了。
莫名的高兴起来,似乎开心的源头都在厂外。回忆一下她曾告诉我的单位地址,然后看看时间还早,过去打包机那儿帮忙,周雷去厂诊所看牙,让我替他一会儿。
一下午过的很快,在站台等车的时候,又碰到了张涛,这货这两天阴魂不散似的,估计又去道外黑天鹅,今天没心情搭理他,你去约会,老子也不能总是看你们约会。见104来了,赶紧上去。
下车后,从国际饭店的侧门进去,来到101号房间,门开着。看见站在门门口的我,露出妩媚的笑容说道:“等我一下,”然后,把电脑关掉,桌子锁上,把椅子归拢放整齐,背起起一个挎肩小包。
她穿着那套黑红格子套裙,下面穿了黑色高筒的丝袜,脑袋上还别了一个晶莹的小发卡。见我傻乎乎的打量她,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我们去哪儿?
我很想说,去天边。
但还是问了个紧要的问题:“你吃饭了吗?”
都刚下班,怎么会吃过饭,可废话有时也变得理所当然。我们在对面北方剧场楼下,吃了碗炸酱面。然后,去坐101路电车,她也不问去哪里,就这么跟着。
在车上我问道:“你也不问我们去哪儿,不怕我把你卖了,”她回道:“不怕,我可以帮你数钱,”说完,咯咯的笑几声,如果不是在车上,真想好好夸她,我仰天长叹,她见我那样儿,又忍不住笑。
下车后,来到江边。
我说带她去一个地方,并说到了就知道。来到道外的老铁桥,我告诉她,这个桥还是日本人建的,有好多年了,两头还有石头砌成的碉堡,我指着碉堡上的一个个机枪眼,说起以前抗战的一些事情,充当了一会儿历史导游。
然后,带她走到桥上。桥上的人行通道不宽,大概有一米多,钢筋和铁丝网隔开的是火车道,时有火车在桥上通过,告诉她到时别害怕。
桥上的人不多,我们往江北岸走去。走在桥上,江风明显大起来,不时吹起发丝。她好奇的看着远处的江面,江水蜿蜒向远方,在阳光下闪亮,脚下的江水拍打桥墩的声音,在空气中显得清脆。她站在那里发呆,我同她一起发呆。她回过神儿来,对我笑笑说:“从来没这样看过松花江,”是啊,站在高处才能领略到松花江的大气磅礴。
我们继续向前走,桥下突然传来不停的震动,我赶紧抓住她的胳膊,告诉她火车来了。火车轰隆隆从身边穿过,几个习以为常的人继续走着,我们驻足了一会儿,才继续前行。很快,火车走远了,一下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她也从紧张中放松下来,对我说道:“火车经过,有害怕和刺激的感觉,过后却莫名的兴奋。”我告诉她多走几次就不怕了,她说不怕就不好玩了,我心想:怎么同我一样,喜欢找虐。
不知不觉的,已走过江桥的中段。前面有一块铺桥的铁板坏了,露出一块空空的地方,能清晰看到流淌的江水在下面打着一个个小旋涡,我轻松跳了过去,然后回头看她。
她站在那里看着我,江风把发丝吹起几缕,似乎在空中欢呼雀跃,略微发红的光线洒在脸上,与身上的红格子衣裙相映成趣,头上的发卡偶尔闪光,好像回到了太阳的怀抱。
她娇嗔的看着我,伸出手。
我走向前,伸出手。
一直拉着手走到岸边,才把手分开,江风清凉,手心里还是出了汗。我们回头看看走过的江桥,又一辆火车轰隆隆经过,冒着黑烟,直到很远,黑烟在空中渐渐变成轻烟。
大概两三百米就是一个不大的江湾,记得少年时爸爸时常带自己来这里钓鱼,如今鱼少了,钓鱼的人却多了,但风景未变。
远处有一两艘小船在江湾上划动,船桨出入水的声音似乎成了这里唯一的腔调。我们找到岸边的高处,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远处的江面,能听到江水滚滚流动的声音,而脚下的江水想熟睡的孩子,正做着甜甜的梦。
我们不愿打破这宁静,不愿打破这美,怕美中有了不足。
渐渐的——
夕阳挂在天边,似乎近距离俯瞰这人间,彩霞满天,染红了两岸景色,远处高低,都有欢喜的味道。她把身体靠过来,把头放在我的肩上,小声说道:“你写一首夕阳的诗好吗?”
我陷入了沉思,一会儿看着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开口念道:“漫天彩霞,太阳落下去的最后挣扎,夜幕伸出巨大的手,抚摸夕阳的眼眸,原来,这一种残酷的温柔”。我告诉她,题目叫《挽歌》吧。
真好!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不过太悲伤了,我想要一个欢心的。”
我有陷入沉思,搜肠孤独那些靓丽的词汇,最后开口念道:“夕阳是我的枕头,我打滚儿,伸腿,踢开彩色的被子,就是不睡”。
她听后咯咯咯笑着,说道:“你是不是怕尿炕啊?”
呵呵!诗意全没了。
我傻傻笑着,看到她开心真好。
黑夜终究是要来的,我们用天真化解了一刻,但无法不在黑夜中沉睡,日复一日,积蓄生活的能量。
回到南岸,坐车把她送回家,可却对她家的住址感到模糊,恋爱的感觉,也许就是模糊一切。我们的相识,是从一个巧合开始,然后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谁都没有主动的表明过什么,这是一见钟情吗?确切的说,第一次是个误会,第二次才算是钟情。
我们的性格相像,都有单纯、开朗的一面,二十四岁应该不单纯了,尤其是经过几年社会上摸爬滚打,再提单纯,别人会认为那是一种傻。但感情的事,不应该有杂质,如果真的爱了,那就去爱。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世俗能够所阻碍的,更不是偏见所能诋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