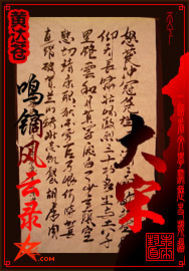雒阳城“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被民间俗称为九六城。它北依邙山,南近洛水,共开有十二个城门,亭台殿宇巍峨耸立,颇显帝王威仪。
相传,远在东周之时,瀍水源自梓泽往东汇入洛水,以其为界,西乃谓之王城,东乃称之为下都,是王城的郊外。及至西周,这里便是成周的一部分。
若是曾经,最热闹繁华的莫过于京师三市——城中金市、城东马市和城南南市。可如今,民生凋敝,百兴俱废,那种“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却是再难得见了。
七月已携卷着瑟瑟秋风袭来。此刻瘟疫虽未全退,但已如将欲冬眠的夏虫,露出了些许温和的苗头。而大街小巷,则无端出现了许多胁肩谄笑的官差,身后的跟着三两成对的属吏兵卫,叩响身居宅院的门环。
娄江月却仿佛丝毫没有注意这些。此刻,马车正辘辘行驶在铜驼街上。这里,因在南街四会道头筑有九尺来高的二铜驼,夹路东西相对,因此名谓铜驼街。
马车依旧是不变的高顶白盖,然而,车中却多了我,还有一名满面戾气的青年。
他便是娄江月近来的契约者,有个在当下似乎非比寻常的身份——曹节的养子。
然而这个青年却是名不经传,面色苍白,身子骨弱不禁风。那无处不彰显的孱弱,仿佛这秋风中抖动残喘在枝头的黄叶,只待一阵风过后飘零落下。几乎整日闭户不出的他,今天却似乎比较反常,与大街小巷弥漫的诡异气氛遥相呼应。
马车路过一家不起眼的宅门,院内似乎隐隐传来压抑的哭声。
“怎么——”这位曹公子皱了一下眉头,突然开了口。
我很不喜欢他说话的音调,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傲慢无比。可毕竟几个月来自己都是在他府上留宿的,也不好在抱怨什么。
娄江月懒洋洋半睁了眼,“哦?”
“这恼人的哭哭啼啼是怎么回事?适才出行,怎容得这般晦气!”
“此言差矣。”娄江月微微一挑眉,神容惫懒,却别有一番风情。
“怎么?”那人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就算阁下不信我,也不能否定当今圣上的鸿福是不是。今朝塞翁失马,他日焉知非福。别见眼下这般光景,说不定哪时便成了嫔妃省亲的豪门府邸。”
“你是说这些人家——”
“不错,时年八月初,京师民间算的可不仅仅是苛杂税赋,还要‘算人’。眼下这时日,朝廷派遣的中大夫、掖庭丞内廷官,当然还有那些精通相术的相士,可谓是无处不在啊。”
“术士?”那人微微眯起眼,露出不悦的神情,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令人反感的往事,“哼,巫蛊……”
“自然,阅视良家童女,择选家人子,不仅年岁要及豆蔻,不上桃李,姿容自是不得差的,面相还当符合相法‘吉利’,相士自然少不得了。”
却听那人兀自一声冷哼,“选中者当即载入后宫,择优后圣上便可登御么?却又是一番鹬蚌相争,入主北宫的岂有那么容易。”
娄江月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
“真不明白你既然拜访故人,这黄毛丫头,你也要带来?我看她被选去掖庭方才合适。”
我一愣,却见那曹节的养子正冷冷望着我,目光流泻着阴霾,让人浑身不舒服。
“她?”娄江月仿佛这时才注意我的存在,轻笑道,“若真选了去,我也算省心了。”
我狠狠的瞪他,却被他随意却警告的一瞥,于是不敢再造次。
“你瞧,这么蛮横的性子,谁敢要呢。”他斜在坐榻上懒洋洋的撑起手,似笑非笑的望着我,“不好好看管着,出去了净是丢我的脸面,我这心可当真是日日悬着呢。”
接着,他又仔细瞧了瞧我的脸色,佯装吃惊道:“看来还颇有几分念想,莫急,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到了年龄,就算选不上也定让你选上。”
我已习惯了他这种调侃,但还是控制不住气的脸都绿了。
“公子这倒不必担心。只要进了掖庭,再如何脱缰的野马,也有被驯服的那一天。”却听那曹公子发话,满面笑意眼底却暗藏狠戾,“女子万不可失了体统,必需严加管教,娄公子若是见了鄙人家中那些丫鬟侍妾,大可明了。”
不提倒好,一提记忆仿佛洪水猛兽陡然唤醒,那种熟悉的心悸让我僵直了身子,脑中浮现之前经历的一幕。
“姐姐,你这手……是怎么了?这般端茶打扫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不过是前些时日不小心的烫伤罢了。”
可那分明就是勒痕。
“上次和姐姐一起来的那个怎么不见了呢?”
“她……她害了病,回娘家了。”
府上的家奴侍婢乃是卖身侍奉,何来归家一说,这分明是撒谎。
如此情况时有发生,后来我才得知,那些所谓害病归家的,大多都是因乱嚼舌根或忤逆犯上乱棍打死的。至于那各式各样残酷的家刑,便是后来的听闻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微微发抖起来。
似乎是达到了某种效果,那人眼中闪现一抹得意之色。
“嗯,受教。”娄江月却仿佛兴趣寥寥,只略抬眼皮好笑的望了我一眼,便继续闭目养神了。
**************
马车一路畅通无阻,终出小苑门,临洛水之滨。
船行水上,烟波浩渺,浮光万顷。静静守望着夏都斟鄩、偃师商城、周王城到如今的京师……幽幽潺潺,流淌着磅礴气势,也氤氲着恬静婉约,诉说着无尽的风光旖旎,也承载着万千传奇与神话。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祥瑞迭兴,天授神物,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得之,以画八卦,谓之河图。黄帝贤明得鱼献洛书,唐尧沉璧知兴亡变数,虞舜祭典获黄龙负书,大禹治水现神龟箓图。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经尽录。
及至周公制礼作乐,功成后,便率群臣于洛水之滨赴曲水之宴。曲水流觞,停留之处便饮酒一杯。滥觞遂源于此。
而如今,绿波荡漾虽在,但那曾经的霞锦萦绕,帆樯林立已不再。空余这瑟瑟的江风与岸边无尽摇曳的荒草,仿佛在嘲笑着民间的灾祸与渺小无知。
这一支波光静然的曲水用它绵长的呼吸吹奏出青史沧桑的箫声,见证了数代王朝更替姓氏改写的战乱兴衰,映照了昙花凋谢、火光凄厉战旗撕裂的长街喋血,记载了黎民百姓朝不保夕的生离死别与动荡疫疠,轻叹着太久太遥远的阴晴圆缺与破晓黄泉。
桨声划破静默,几只沙鸥扑散而过,幽幽长鸣伴随着汩汩流水远去。娄江月不知从何处来了兴致,半眯了眼扣舷而歌,声音低沉舒缓,却似是蕴含着道不尽的纠葛与岁月。
“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祀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缀祷;色连三光……”
“这难道是始皇那时……”撑篙老人枯涩的声音在风中撕扯着,帽檐抖动,遥遥间只余残音。
“不错,正是那祭祀三山洛水时作的,祀洛水歌。”
“这转眼间,也快过了四百年了啊……”
“不错。”娄江月微微阖眸,“曾经那想与天同寿之人,留下的不过是那些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传说罢了。一世的荣与辱,誉与非,尽数如同这泱泱秋水,不舍昼夜,逝者如斯矣。”
“我祖上曾是韩国贵族,始皇横扫六国之时是如何的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以及那份绵延不绝的亡国之痛,都一代代口耳相传。而后兴亡交替,高祖开疆辟土逐鹿中原,救民于水火,围项王于垓下,九州乃定。及至更始篡权,世祖力敌众数,复兴汉室,一匡天下。这此间种种更替分合之道,又有谁能尽数参透!”蓑夫摇首长叹,长长的篙复撑起。
“更换的是帝君王者,黎民之疾苦却是如此相似的延续。”娄江月不知从哪搬出了两瓶好酒,因那曹公子实在病弱,便自斟自饮起来,“倒不知,这万里河山,与其说是千古帝王守护,倒不如说它是在守护万千生灵呢?”
“这般说法,老朽风风雨雨里这么多年,倒还是第一回听说。”
“呵呵,凡事有先,我便学那商鞅,来个斗胆的先例吧。”他又带了那七分癫狂,举樽对天,而后以酒泼地,“当世高人名流莫不图个自在,我便也逐个风流,胡言一通!”
“官人当真是豪爽性情。”那蓑夫胡须微颤,“历经种种天灾人祸,时人莫不三缄其口,像官人能这般不计较得失的,实为难得。”
娄江月却微沉了双眸,不再应声,只是出神的望向那滔滔流水。船依旧溯流而上,仿若缓缓漂浮在一个氤氲的梦境。在水天一色的浩渺中,驶向那茫茫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