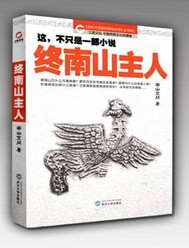白马寺,始建于明帝永平十一年。实仿天竺式样而筑,民间俗称金刚崖寺。其中,流传着甚为著名的永平求法之说。
昔日明帝刘庄于南宫梦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使臣于月氏遇游化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邀京师宣讲,并跋山涉水,白马驮经。为记此功,白马寺乃成。
然而,这个曾经沐浴皇恩、巍峨高阁、备受瞩目的宏伟建筑,如今因历尽人世磨难,终是变得衰颓而满目疮痍。静静伫立于长林古木,晨钟暮鼓、香火缭绕虽在,却已是人迹罕至。
大疫与饥荒迫使大批的僧侣外出化缘,寺内不见住持,院落长久无人打扫,积压了厚重的灰尘。
那一身黑色锦袍宽袖长衣之人,就这样行走于这乱世中的一隅寂寥中,步履忽紧忽慢,任扬起的尘屑数尺淹没了阳光。几处残桓断壁、破砖乱瓦映入眼底,却依旧怡然自得,仿若这世间最恣意散漫的狂傲高士。
他步履渐息,终是止于一株苍苍古柏之下。于是满院只余金桂沉静,时而有鸟鸣空谷,衬得一切愈发清幽。
寺中似是无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万物皆缄默。他没有入主殿,甚至投置一缕目光都是多余。就这样静静的,仿佛在等待着什么,阳光透过叶间细碎铺泻一身,眼底却是变幻莫测。
“既然来了,何不出面相见?”
终于,暗处传来一声叹息。
“我只道你许是念一点旧情,是为了夜郗那义女而来。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你真是毫无改变啊。”
“你不是也一样?”那人倏尔粲然一笑,万般阴郁一扫而光,只余无限惫懒,“忍了那么久,不觉得很辛苦么?”
“彼此彼此。”
慢慢,佛堂正殿走出了一名青年男子。素衣白袍,仙风道骨,发须飘逸,一双眼炯炯有神。
“说吧,一直找我,到底所为何事?……恩?我的百年之交……蓟子训蓟先生?”
“娄公子何时都是这般玩笑。”那名唤作蓟子训的不慌不忙,慢慢走近,“怎敢劳公子半分呢……只不过也想顺搭个马车罢了。”
“真是个好主意。”他说着,眼底却无半分笑意,“只不过,蓟达你何时……对宫中的事这么感兴趣了?”
蓟子训淡淡瞟了他一眼,嘲讽道,“娄公子不也一样?不过你说错了,我感兴趣的不是宫中的事,而是……你的事。”
“哦。”那人突然兴致寥寥,“想弄清楚我的来历,你再修行个千年罢。”
“好大的口气……也罢,就算要费些时日。不过,近些日子你也做不得安生。”
“这又……怎么说?”
“你清楚,我极不习惯你的作风……你要毁的,我必救之。”
“那可辛苦你了。随意。哦,也许应该这么说更能令你高兴……我拭目以待。”
风陡起,肆无忌惮的卷扫着尘埃吹过山门,吹散那如低语般百转的话音,静默再次袭来。
一抹云翳在艳阳面上拂过,那是细雨过后光明暗藏的阴影。拱影斑驳,如那洞券上深深浅浅的雕痕,那是百年前工匠血汗的铭刻。传说中的三解脱之门——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便如同水墨映在廊上明明灭灭,那是如今浮殍遍野之芸芸众生,在水深火热中无限憧憬的解脱与涅槃,明明近在眼前,却遥远飘渺如晨星。
不知何时,那驾豪华而尊贵的马车再次启程,载起再续调侃不止的二人。而寺中的某一隅,一名女子正幽幽转醒。
**********
一切仿佛,大梦三生。
我不知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街上的,如今又算不算是劫后余生,但我已能清楚的感受到轻柔的风夹杂着泥土的气息,空气中透着湿热。
此时的我虽勉强能站立,仍如行尸走肉。口中干渴,腹中饥饿难耐,冥冥中只有意识催促着我,向前,再向前,需要果腹的东西,哪怕一点点也好……
然而,入目皆是空荡,甚至不见杂草。大街小巷荒无人烟,只余几个叫花子有气无力的倒在街头,形容枯槁。
终于,我倒在一片墙根下。自己究竟是幸还是不幸?病死与饿死,不过是个选择的问题。
天空不知何时又朦胧的飘起了雨,那是久旱过后来之不易的水源。
我费力匍匐,颤抖着伸出手想要去接下一两滴甘露。
正在那时,远处传来辘辘的车轮声。
那是一辆我从未见过的华贵马车,无处不透露着拥有着的富足与雍容。精致的锦色华幔,金色的格纹,尊贵威严的白盖。一时间,我难以相信自己不在梦中。
然而,那车上的人飘来话语的话语却是那么清晰真实。
“夜家丫头,你怎么不在白马寺中好生休养,竟在这般地方乱跑。你可知花费了我多少精力?”
我吃惊的睁大眼睛,愣愣的望着那徐徐走来的,一身仙子傲骨的人。他貌似中年,发须随风而舞,双眼亮如辰星。
记忆明灭,那模糊的容颜似与数年前的景象渐渐重叠。原来时光的刻刀可以手下留情,在一些人身上柔软的拂过,不留丝毫印记。
“蓟……先生?”我不确定的望着他。童年的记忆被唤起,记忆中的那个人玄奇古怪,神出鬼没。但他却是郗夫子的不二至交,二人常常秉烛夜谈至深夜。
那人点点头,眸光闪动,目光锁定我,却仿佛透过在看向遥远的未知,然而其中涌动的沧桑感叹,却是可以轻易读出。
“先生如何知道……”我恍然,“我的病,是先生相救?”
果然,我病中所听的,都是幻象。可那人,就算是真正相求,也不会来吧。
他不置可否,只是幽幽长叹。
“没想到你还记得。上一次见你,怕也有四五年了吧,那时你不过是刚过灶台般高的黄毛丫头,抱起来轻的如同一片羽毛,如今竟是这般大了。老郗泉下有知,也该欣慰吧……”
“只可惜夜郗没有这个福分得知泉下了。”
高处突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应声,语调微冷。
吃惊抬眼,我怔愣的望向高处。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时隔三日未见的……娄隐。
他不知何时坐在了对面的数丈阁楼之上,那里本是几欲倾颓,渺无人烟。
五月雒阳的杏花雨飘飘摇摇,一时让人忘了这座城中千般的疾苦,眼中只有他那一身黑色锦装的雅致与不凡。
那如凤目般上挑的眸平添了几分妖冶,薄唇轻抿,一樽精致的天公爵擎在指尖,那姿势想必就算当朝的皇亲贵族,也无法做到他那般高贵从容,又有一份洒脱恣意掺杂其中,说不出的赏心悦目。
“娄江月。”蓟子训讶异一闪即逝,冷静的转过身去,“你还真是行事飘忽不定啊。”
“略胜阁下一筹而已。”
“娄……江月?”我喃喃。他本名不叫娄隐么?
“娄隐,表字江月。不过一切不过是自称,谁又肯定真假。夜弦,不要相信这个人。”蓟子训慢慢站在我身前,仿如一尊雕塑。
“不错,我不值得让谁花心思去相信。那样比这天下的太平来得更不切实际呢,蓟先生果真一张妙口,妙这个动人的名字还应该送给你为对,怎么偏偏就送给了这当今的可怜人,窦皇太后了呢。”
“你果真是去了见她?”
他轻笑,“你不信?不是特意跟去了么?我的督查使大人。没想到你耐心如此欠缺,比我这个逍遥散漫的回来的都早。”
“拜你所赐。”蓟子训轻蔑的看着他,再也不见之前的一丝怒意,有的只是讽刺与不屑,“是谁未到雍门便隐匿踪迹,不惜弃车还拐走把式,实非大丈夫所为,究竟谁更心虚,应有人心知肚明。”
“哦,怎么说呢。”他轻佻一笑,白皙玉指遥遥一指,“带个外人,总归不会方便。难道你觉得,把一个与自己时时作对的人放在身边,这个人嗯……还很可能丧失理性,这样的做法,算是明智之举么?”
“也罢,料你做不出什么好事,此次权且算我大意。只不过……” 蓟子训眼中明显含了一丝怒意,“你刚刚说夜郗什么?”
“怎么,我适才说的不对么?”那人微抬了音调,“触犯禁忌,背弃使命,有失身份。神魂俱灭不过自食其果罢了。他不也是得偿所愿?这万物,哪样又不是有得有失。他想要,便需付出代价。犯不着旁人耗费这精神力杞人忧天。你我这情景,又有谁来怜悯?”
“娄江月,需要怜悯的是你。曾经的睥睨六界不可一世,如今却困于红尘卑微到以契约来打发度日。而我,尽管修为未尽,但终是这天地间最自由的存在。”
“哦。虽是自由之身,但也有执著之物吧。单凭这一点,你就输定了。”他笑的愈发恣意,“这世间恐怕没有什么能令我执著的,契约也不过是契约。要比疏狂,你我不相上下;要谈比试,我虽然法力尽失,凭闪躲也尽可胜你数招。要论求索,那可要令你失望了。因为谁也别想觊觎我的东西,更别说——我的契约之物。”
“你说什么……?”蓟子训蓦然一惊,怒意再起,“难道你来这里的目的……”
“你说呢?你应该也冥冥中掐算到了吧,这几年你辗转各处甚至不惜翻山越岭到雒阳。这个女孩如今命理上突然与我的联系……”
“不错,她的母亲,便是平氏君。没有想到吧?曾经的你所认识的、让你找遍天下的那个人竟然就当今圣上乳母,那个勾结常侍谄媚太后的逢迎之人,就在刚才与我缔结了契约,让我来找到并护佑她与最心爱之人的……女儿。”
接着,他便微垂了目,笑意清浅,薄唇张合间吐出那低沉的几字,如同午夜来自地狱的诱惑。
“永——生——永——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