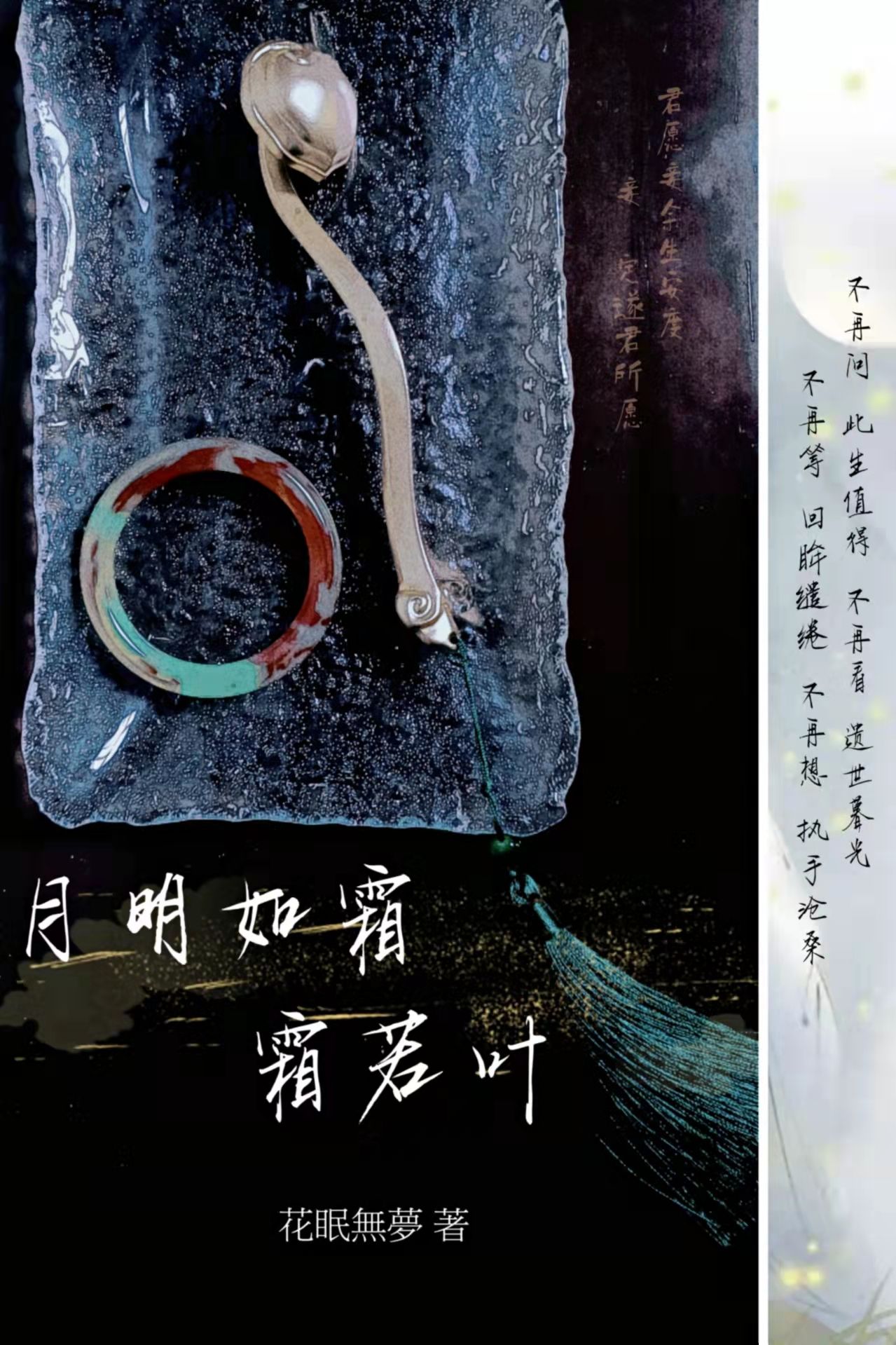行程的目的地是南阳,然而,却因为一场事故做了逗留。
那场事故便是,我害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这对于正在行程的辛绕和灵耀无异于是晴天霹雳,而且种种症状表明,我很可能是在途中染上了病疫,这顿时让灵耀愁眉苦脸。
辛绕一边在大街小巷兜绕着找医馆,一边兀自叹气。
“怎么把这事情给忘了,你自然比不上我们的体质……还让你跟出来,真是大意了……”
客栈都无法收留我们,一见情状,唯恐避之不及。而城中药铺多是人满为患,却不见郎中,只有几个伙计失魂落魄的忙着,原是如今大疫在前,郎中早已分身乏术,不知所踪。
而我的意识已愈发模糊,几次半睡半醒浑身如同炙烤,朦胧间恍知大限已至,不由得吃力劝说他们不要管我,自行赶去南阳。
每到这时,我就会隐约听到辛绕稍带怒意的呵斥声。几番昏迷,我似乎被安顿在一个寺庙里,四周尽是毛咋的杂草,钟鼓齐鸣,佛香缭绕。
很多次,我似乎都仿佛看见郗夫子在我身边往我口中灌入苦涩的草药,可稍加清醒后,却又发觉那是在满头大汗熬药的灵耀。
病中的我常说胡话,根本分不清昼夜,不知过了多少个时辰。晨晨昏昏,仿如百日。我总会混沌的奇怪,为何我还没有死去,为何身边仍旧有人。
他们……为何还不离开?他们……明明对疫情那么冷漠。
身子骨开始酸痛,我开始下意识不让自己转醒,否则便是钻心剜骨的疼痛。口中似乎有浓重的中药味,却每每咽下都能品尝到一丝血腥。我真的厌了,倦了,开始拒绝喝药。
辛绕似乎在我昏迷时说了好多话,但我一直不明白的听着,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无尽的黑暗中,我开始慢慢沉入。从头至脚。
却在这时,那熟悉的声音中,有些许对话竟然分外清晰起来。
“辛绕哥哥,姐姐已经吃不下去药了,灵耀也要无能为力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
“主人的三日之期未明,我们如若就此罢手,毫无请示。一旦出任何差池,追究下来,又当如何交待?”
“可明明就是不治之症……”
“主人吩咐过的人,就算是不治之症,也要守护到最后一时。只要有主人,便有我们的职责所在。只要我们想做,尽力去做,何曾有不能做之事?”
“可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不,我们还没有尽到全力。”那温和的声音顿了顿,“若说难题之广浩如浩瀚天地,那方法永远如天之星辰、地之碎石。我们还没有用到最后一个办法,小灵。那就是——”
“去找主人?”
终于,我陷入了一片沉寂。
****************************
育阳侯曹节府邸上,又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雒阳城内,也许从未有人会记得此人。然而,对于育阳侯、长乐卫尉曹节大人来说,也许并不尽然。
此时,他望着这个被府卫拦下的陌生人,面上仍旧是一副惯常的讥诮不屑、颐指气使的姿态。
“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擅闯本官的府邸啊,你命不想要了吗?”
那尖锐油滑的声音立刻让人立马泛起鸡皮疙瘩,想起了污泥里翻滚的泥鳅。
“大人……这么快便忘了我呢……”
仿佛耳边的轻言细语,周围人尽是一愣,目光聚焦在那人身上。只见他一身典雅的黑色锦袍,浑身上下散发着难以言说的雍容与贵气。那半垂的双目,随着微微扬起的缓慢声调,徐徐张开,幽深的黑瞳仿如带了一种催眠的迷幻,霎时间妖冶四溢。
众人皆不解。却见那位姓曹的大人在望见了他的目光时突然如钉子板站稳了脚尖,只是一个恍然,便露出无限惊异。
“你是……你是……”
这种感觉是什么?仿如来自最遥远的潮水,顷刻间无边蔓延。那是一段最重要的记忆,为什么……为什么会模糊,会有忘记很久的感觉了呢?
“是你么?好……立下契约,终生不得反悔。”
“你的愿望便是除掉窦氏外戚一族么?我便许尔如愿。”
“听好,事成与否,虽有天意,但在人为。建宁元年,事关你的生死。请使我入宫,入——长乐宫典中书。”
“这位就是——长乐五官史朱瑀朱大人?失敬失敬。不错,卑职就是尚书省曹大人的,不,应该说是所有中常侍的亲信……”
“收买?呵呵,这样传也不错。颇合我意。既然事已成,大人莫要忘了诺言……我么?自然是回到我应该回的地方去。”
……
“不错,就是我。记起来了么?”
那人慵懒的语调中带了一丝笑意,说不清是和蔼还是嘲讽。
“原来是你!那位高人!瞧我这脑袋,快!快请!”
“呵呵,果真是贵人多忘事……”
“怎么会忘呢!高人的恩情,可是时刻浸润着本官呐!本官的今日,也全都仰仗了高人你的指点啊!却不知本官何幸,竟劳高人尊驾?”
“哦,是大人的义子,一桩小事。”
“我义子当真眼光独到,竟能交到您这样的朋友,可谓三生有幸!”那人笑的愈发熨帖,“今日高人有幸临门,务必接受本官的重重答谢!”
“清除忤逆作乱者是你们的事,与我没有半分关系。”他懒洋洋的说,恣意取下指上的那抹碧玉,轻轻呵气,“不过是一句话,更何况,你也付出了契约的代价,再平等不过的交易,何来答谢之说?”
“这又是哪般话,高人平日行踪不定,万事点到为止,不一一言明,是您不屑与我等鼠辈为伍。任何差池也都是我这等凡人低贱之脑所犯下的。高人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岂能是我等能够比及的。尔等屈屈作为,让高人见笑了。”
“好吧。既然曹大人都这般发话了,我一介草民,又怎敢有丝毫不屈从之礼呢!”他笑了,仿佛三途河畔最妖冶的花,最美却最遥不可及。
伸手随意一指,便是府邸庭院里停靠的白盖马车。车夫还在车前打瞌睡,口水染湿了大半个衣襟。
“那就劳烦曹大人借马车一用了。”
“成成成!这算何劳烦!就算高人要了整个府邸,我都愿掏心交换!”那人笑的谄媚,口气却忠诚动听,亲切可人。
也许,这便是让当今小皇帝如此信赖喜爱的缘故吧。
“喂!你这个狗奴才!居然如此放肆,丢进我府上的颜面!是不是平日里过于怠慢你们了,皮痒的紧啊!”
“大人饶命!小的知错了,再也不敢了!”
马车慢慢驶入街巷中,后面跟着没精打采的牛车,上面载了两个一脸艳羡的人。
“好有气派啊!果真主人就适合坐这样的马车的!”灵耀激动的两眼放光。
“中常侍的完胜,换来了的是得寸进尺的奢靡、享乐和放纵。这样玩弄天下与鼓掌,民意饱胀的愤怒又会当何时得以弓满而发呢。”辛绕却在关心着另外一些事,嘴角仍含着不变的笑意,“那一定是摧枯拉朽的力量……不过,在如此狂风骤雨中要说不变的,果真还是主人。这种尊贵就是与生俱来。就算一文不名,两手空空,到了哪里仍能就地取材,构建他永恒的风流大厦。”
“辛绕,灵耀。”
前方的马车并没有快速行进的意思,显然是在等他们这辆别具一格的牛车。
那人就那样华丽丽的斜倚在温软的锦绸丝垫上,连车帘都懒得掀开,只是任风将其尽数抖动,让人隐约瞥见他那散漫的一角。
“说吧,什么事。值得你们兴师动众前来找我。”
“主人,是这样。”辛绕微微笑着,恭敬颔首,“那位与主人有三日之约的夜弦姑娘,眼下随行至雒阳,却不幸染上恶疾,我二人皆是回天乏术。我二人无主人命令,又不敢擅自妄为,遂前来请命。”
“夜弦?”马车帘幔后又飘出了漫不经心的声音,其中透露着三分诧异,兀自停顿了一会儿,似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郗夫子的徒弟么?”他轻笑一声,“没想到一时的疏忽竟然埋下诸多事情。”
接着,他便轻描淡写道,“好了,我知道了,你们去南阳吧。”
“那主人……?”
“我先去宫中会一会故人,随后就到。”
“是。”
二人皆是不再多言,面无表情。辛绕仿佛了然于胸,而灵耀更未有半分追问与纠缠。
牛车再次慢吞吞前行,眼瞧毫不协调的二车错身而过时,车内又轻飘飘的传来梦呓似的一句。
“敢情天下故人还真是多啊!”
仿佛一句暗语,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在那一瞬,辛绕转头淡淡回望了一眼,唇边绽开一抹微笑。接着,他便不顾灵耀眼巴巴的盼着主人接下来的发话,手下稍一运力,牛车便再次前行了。明明是慢吞吞的速度,却诡异的让想追的人永远也无法追上。
“高人,我们接下来是去……皇宫么?”车夫似乎察觉到气氛的不同寻常,说话小心翼翼。
这是什么人物!竟然曹节大人都如此敬重!
“唔。”那人阖上的眼眸在暗处悠然张开,幽深如暗夜却无端闪过一抹妖异的红,快的令人无法捕捉,“那是自然。不过……我看这之前是走……哪条路才好呢?”
修长的玉指向上缓缓伸出,他仿佛在虚无的空气中捕捉着什么,却又像是冥冥中漫不经心的掐算。
一切不过是瞬间完成。
“小哥,劳烦先去一趟城西白马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