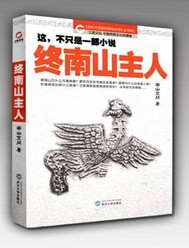清晨的天是浸染的绛蓝,带着万物复苏的前奏,那繁星愈来愈疏,隐没在熹微的浩渺之中。
街巷里分外的寂静,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透着寅卯交接之时特有的料峭寒意。娄江月停在一处幽深的巷子里,两面皆是榆槐光秃的枝桠。他踏上覆满青苔的石阶,轻轻叩响那紧密的院门。门廊上,桥府的悬灯还在幽幽的燃着。
“谁呀……”半晌,一个声音含糊应答。随着门板吱呀,有人小心翼翼的探出头来,睡眼惺忪。
“在下娄隐,冒昧叨扰司徒大人府上。”
“娄先生?”那人闻言突然抬头提起了精神,揉了揉眼,不可置信的说,“我是不是在做梦?”
说罢,他赶忙将门大大的敞开,露出一院的古树苍苍,简朴素洁。
“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小人这就去通报老爷……”
不料娄江月却突然拉住了那下人,微微一笑,神情中掺杂了一丝倦意。
“不必了。车马困顿,权且先睡一觉再说……”
那下人瞪大了眼睛,恐怕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等不重礼教之人。
“好……好,娄先生这边请……”
院子里静悄悄的,几株枯桠横斜,突兀的脚步声惊起沉睡的鸟儿,到处都是扑棱棱的慌然无措,让人也瞧着莫名起了一缕彷徨之意。
却见那小厮脸色突然不自在起来,仓促的瞄一眼娄江月,似是想到了什么事情。
“怎么?”娄江月虽总是半垂着眼慵懒的模样,却总有常人不及的敏锐察觉。
“啊……是这样,先生。都怪下人们粗心大意,您曾经养的那只鸟……唤作九儿的那个,不小心飞走了……”
“嗯。”
“还……请先生责罚!”
娄江月微微打了个哈欠,半晌有些困惑的抬头,“嗯?责罚什么?”
“责罚小人疏忽之过!累害先生失去心爱之物!”
娄江月闻此却突然莫名一笑,“心爱之物?”
接着他微微抚额,摆手笑道,“由愿好生不舍,由不舍生执念。一方的执念未尝不是另一方的羁绊。我娄某从未有执着之物,何来心爱之说?无妨,那鸟注定不是笼中之物,飞了也正合我意。”
那下人明显微微吃了一惊,“若如此,先生饲养它,却又是为何?”
“为何?”娄江月顿了顿,仰望苍穹继而悠然道,“以之为师。”
“以之为师?”
“人于尘世,往往因沾染各种欲望而渐渐迷失自我,偏离了自然赋予的本初之性。而动物身处困境的生存之道,顺乎天地自然,莫不有人值得借鉴之处。”
那小厮一时怔忪,晃了晃脑袋,似是颇为费解的望了娄江月一眼。
“先生博学。”
我却因短眠突然有种头痛欲裂之感,还好厢房已近在眼前。
*************
一觉过后,娄江月便携我前去堂屋。那里已坐了一位宽衣福巾、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衣着谦俭素雅,梳的一丝不苟的发偶有银丝闪过,以缣巾束于脑后。
仿佛一块上好的整玉完璧,经过时间的碾磨与零碎敲打,出现了条条细纹。他的神情无不带着点点沧桑的细屑。
堂上已置樽酒,只待主客对酌。
“世人都赞老夫为伯乐,不计前嫌荐能人,慧眼独具举才士。甚至堪比战国四君子之名。殊不知就算是这样的伯乐,也有难于求得的千里骏马。”老人目光和善却带着一抹难以察觉的凌厉,自娄江月行礼后便从未移开。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旷古难遇。”娄江月神色平静,儒雅欠身,“在下不过是个小隐隐于野的人,混迹于市井之中,游离于贩夫走卒之林,实在不值得司徒大人如此记挂。”
二人坐定,目中再无他人。我连忙卷袍上前,用斗小心将冽酒斟满羽觞。
“阁下之贤堪比子陵,如若此便是看不起老夫这双浑浊之目了。”
“岂敢,司徒大人谬赞。却不知大人近况可好?”
“你瞧我这昏黄老眼,稀疏落齿又觉如何?”
“大人忠心为国,老当益壮。”
“老当益壮?呵呵。那这双眉愁锁,忧思达旦,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又是如何?”
“大人为天下苍生殚精竭虑,实为在下所不能及。”
“年轻人倒是颇会逢迎。”
“诚为大人所迫,权以此安身立命。”
“哈哈,这倒终于流露出些许真性情来了,好!与君共饮,当真豪情自在,一时诸多忧思抛于脑后。”
老人将觞中之酒一饮而尽,之后慢慢放下杯盏。笑容如沉日般慢慢淡去,面色渐渐变得凝重。
“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曾经如此,当今亦然。男儿立世,既食汉禄,莫能驰骋杀场,建功立业,便要拼得满腹经纶,治国安邦,方可不负此生。我门下之客数百,都是志同道合之人,对先生无时不是虚席以待。”
说罢老人便起身深深一礼,无限的谦卑大度。他果真是求贤若渴,意欲招揽四方之士。
而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娄江月究竟哪点让这位司徒大人另眼相看,要知道,他可是刚刚从曹府混出来的人。
“殊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司徒大人认为当今之世,奔走仕宦会有何大的作为?”
老人微微一愣,竟一时无话。望着热酒那如丝如缕的白雾出神良久。
“想我桥某一生一腔报国壮志,斗梁冀,擒羊昌,忍河南尹之辱,受城旦之刑。杀皇甫,假黄钺,迫姜岐,荐陈球。焚膏继晷,凡事无不三思而后行,以大局为重。却无奈苍生疾苦,常侍乱权,汉室倾危!”
继而,他陡然抬头,目中露出悲愤,宛如决堤的洪流奔涌,“安能息心泉林,坐视祸乱于不顾,此等与生杀劫掠何异!
“如此,大人意欲何为?”
“我当直谏!贼党一日不除,天下便无安泰之日!”老人微微有些激动。
“这可当时大人三思的结果?”娄江月轻轻一笑,“仅凭一己之力,也许再无豫州刺史周景那般豪迈磊落之人。前车之鉴,大人莫要走那陈蕃、窦武将军的旧路。”
“圣上昏聩,乃是臣子无能。”
“与君共事,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娄江月淡淡道,“大人还是缓兵为上策。”
老人陡然沉默,过很久后方才叹道。
“非此不可了么……我现下时时回想,当初姜歧为何宁死不仕,甚至母之改嫁亦不为所动。难道摈弃这世间纷扰芜杂,如先生这般删繁就简,是安然于世的最佳之法?”
“人各有志,行径非同。若世上多是我等不求上进,游手好闲之辈,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大人不必如此介怀,以大人之性情,凡事当求无愧于心,不至孤绝悔恨终老便好。”
“果真如蚍蜉撼树,弄不好便是玉石俱焚么……”老人闭目锁眉,“如此又当何去何从……”
“本朝天子皆不永年:世祖光武年六十二,孝明年四十八,孝章年三十三,孝和年二十,殇年仅二岁,孝安年三十二,孝顺年三十,冲帝年仅三岁,质帝年仅九岁。”娄江月复饮一口冽酒,清晰吟道,“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是桓帝在位时民间流传讽刺跋扈将军梁冀的歌谣,那时,他刚刚毒杀质帝,桓帝刘志方才十五岁。
闻此,老人的面目似突然被往事撕裂,变得苦痛不堪,他以手掩面,悲泣不已。
“自孝和以来,这天下便已不完全在刘氏手中……”
“天子懦弱则好欺,天子精明则难奉,无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娄江月手指轻叩樽尾,淡然陈述。
“芸芸众生,这其中的故事,早已辨不清谁是真正的主角。一人的悲伤,或许成就另一人的喜悦。便如那一国的颠覆,或许成就着另一泱泱大国的崛起。天下大势分合交替,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却又不知乱于何时?繁华的背后,总会有人悄悄黯然收场。”
老人慢慢抬脸,似乎一时难以从沉浸的往事中回复过来。
“却又不知乱于何时?”他状似喃喃,“也许,老夫是该想想究竟能做些什么了。”
*************
【注】文中所提子陵,是东汉年间隐士。东汉隐士严光,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东汉建武元年(25),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刘秀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今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80岁卒于家。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