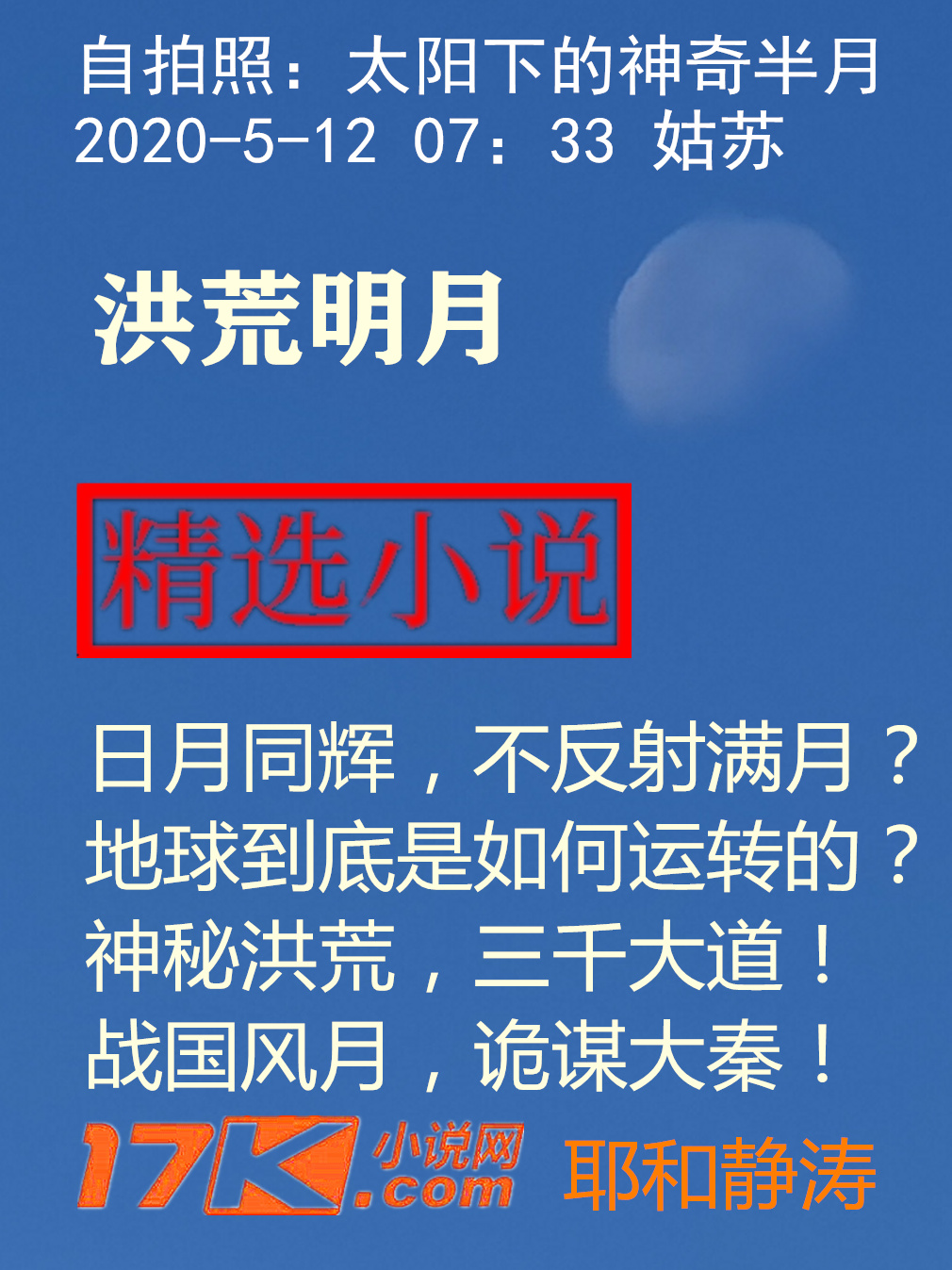那日他们又畅谈许久。
谈起桓帝之时的梁氏五侯,居功自傲作威作福,最终“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
谈起太学生及郡国生天下名士的清议,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时人称之“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
谈起外戚专权,飞扬跋扈横行朝野,一时“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谈起黄门常侍,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一时“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谈起质帝时官僚中的“前后李、杜”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桓帝时士人中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谈起延熹九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李膺、陈寔范滂等士子清流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谈起建宁二年第二次党锢之祸,陈蕃窦武兵败身亡,宗亲宾客姻属皆被灭族,囚禁流放、下狱处死的不计其数……
还有当今如履薄冰的五经博士,朝上痛心疾首的清廉忠臣,暗地为非作歹的朋党奸佞……
当初的血雨如柱与呐喊如雷,长街夜哭和纷繁诡计,再苦痛再心悸的灾难,如今只是字语中寥寥带过,只是瞬息之间,便已过千年烽烟,百年沧桑。
那是袒露出的一帙风干青史,转首回顾,任一翻阅,便有篇页在朔风中哗哗作响。
最后,话题回转,他们说起那宫门深锁,一夜白头的窦太后。
仿佛将欲油尽灯枯的幽幽烛火,明明灭灭悄无声息,只静静等待着幻灭的那一刻。
她的一生,论不及波澜壮阔,却也跌宕起伏,弥漫着道不尽的辛酸悲苦。富贵,她母仪天下,父兄手握兵权,无人能及。然而感情,她在享尽圣宠的采女田圣面前,却仿佛低微的一无所有。
她的姿容平庸注定她的情感,只能如同那月光透过花叶,筛下的黯淡疏影。那一份愈发醇浓苦涩的相思,随着光阴荏苒,渐渐酿成无限扭曲的苦闷怨愤,沉淀的愈发浓厚,便愈发有着令人心悸的力量。她在夜深人静之时,将其一次又一次寂寞的品尝。
延熹十一年,桓帝驾崩。满腔怒火终如洪水猛兽爆发。那一夜,先皇尸骨未寒,后宫血染长阶。黑色的夜刹那间绽开无数朵妖异的红色。
对待女人,她如同嗜血修罗,毫不留情。然而,在清剿常侍时,她却流露出犹豫未忍的慈悲神态。这一份看似柔弱的迟疑,注定了她悲剧的收场。
迁南宫云台幽禁,除母徙比景之地,九族尽诛。
“眼下黄门令董萌多次为太后诉怨,圣上似有同情之意,供养资俸便未断过。”老人说起近日情状,干枯的手微微紧了一紧。
“是么,那他近日可要多求自保了。”娄江月心不在焉的说着,眉眼间带了一丝薄醉,
“司徒大人曾经不阿权贵,以子奉法,也可谓对天下黎庶恩德并重,对朝野上下仁至义尽。如今大势使然,即便大人犹豫不决,常侍朋党定会迫使大人做此决意。”
说罢,他突然眼角一挑,斜睨到我,唇边绽开一抹不明的笑意。
“好了,能说尽此。如今,我倒有一事相求。”
**********
第二日天蒙蒙亮,桥玄便已衣着端庄的站在门前。他身着五时色的月白朝服,头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腰间佩有印绶,真可谓是广袖高髻、峨冠博带。
他在门前徘徊,手带着几分眷恋的抚平官服上的皱褶,仿佛要拂去最后一抹不舍与疲惫。良久方抬头揖礼,沙哑道。
“我将进宫面圣。只是……”
“大人但说无妨。”娄江月站在阶下,状似恭敬。
“老夫如今只有一事放心不下。鲜卑连年扰掠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杀略不可胜数,时至冬日怕又是蠢蠢欲动。”
“在下正欲前往并州一会故人,也许略能尽上微薄之力。”娄江月突然语出惊人。
我愕然,这可又是他的一次心血来潮。他难道把前去南阳的灵耀和辛绕忘了个一干二净么?
“如此甚好。”桥玄一声长叹,“对了,昨日你所求之事……不错,小女确是近日及笄之礼,让你身边这位幼|女前去学学寻常礼仪也未尝不可,二人年龄相仿,你我又非见外。深入蛮夷之地,的确莫要失了汉家仪礼。”
“如此便谢过司徒大人了。”
“莫要再唤我司徒,我如今已龙钟老态,缠绵病榻。即将是辞去官位之人,与草莽无异。”他轻咳了一下,苦笑道,“我已让下人打理行装,恭候圣旨。待万事安好,便启程返归故里睢阳……”
“公祖两袖清风,君心似水。归返故里乃是睢阳黎民的福气。”
桥玄轻叹一声,似是深锁了眉头。清晨的一缕光辉斜照,染亮了他花白的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惜老夫已近风蚀残烛之日……”
他转身愈走,突然庭院的回廊上传来纷繁的嘈杂与焦灼的脚步声。
“主公,万万不可啊!”
“主公一走,是将几十年的心血置于何地,将众宾客置于何地?”
“主公待我等不薄,若有何差池,我等自是不会逊于田横之门客,自当以死明志。”
待众人纷纷进言之后,突然从人群中传来惊呼。
“江月?你怎生在此?”
“不期而遇。”娄江月懒懒抬眼,顺势倚在门边石狮上,顿时有无数眼神如钝刀直扫而来。
这一随便的举动,众宾客顿时窃窃私语。
“那便是主公一心要找的贤人娄隐?”
“虽是仪表堂堂,但言行竟是这等散漫,难保不是放浪之辈。”
桥玄慢慢回身,将来之众人的愤懑与不甘一一看在眼底,最后终是一声长叹,弯腰长揖至地。
众人皆大惊。
“主公为何行此大礼?我等尽是受惠于公,怎生承受得起?”
“众位先生尽是志士仁人,桥某得遇众君,实乃毕生大幸。昔日邀众饮于堂上,本以图报家国,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为所共求。”桥玄抬头,言辞恳切,目中却似燃起幽幽之火。
“然纵使拳拳之心,不抵当世浊浊之风,权门请托,贿赂公行。国力衰微、民不聊生。此皆莫不有桥某之过。眼下我当告罪于圣上,辞去官职以惩我之不济。”
似乎有人面露异色,张口欲言。
“桥某非能士,实是有负诸位,万死不能以求谅之。” 桥玄再次谦卑作礼,接着他下面的一句话,让众人皆是沉默。
“合则留,不合则去。”
************
那天众门客自是不能以此寥寥数语平心静气,还是娄江月最后出言一句,让众位皆再无话。
他说。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离。诸位之所为,可是促使常侍以利而合,为何不能韬光养蓄,以使其以利而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人如此只是暂避风头,难保还有出仕之日,圣上最器重的人莫过于桥爱卿。”娄江月负手于后,一副闲情逸致的模样。
众儒士也不再露出之前的鄙夷神情,大多数人尽是决心追随桥玄前往睢阳。
**************
感冒了。。。好难受,打着喷嚏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