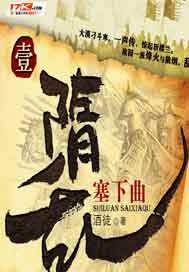“非伤天害理,乃是前辈力所能及之事。”娄江月淡淡的笑道,已然起身一礼。
老者慢慢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沉默了一会儿方才道,“那人平日里行恶多端,染此顽疾可谓报应,姑且不论因果天命,这其中又不知有多少大快人心。”
“谢元谢前辈。”娄江月突然正色,又恢复了那副慵懒随意的模样,“当今世上,大量饱学之士流落民间,刚正不阿者冤死道旁,心术不正者升官封侯、比比皆是。与其谈论这因果报应的麻痹,倒不如积压怒火弓满而发,如此才能改天动地,迎来真正的大快人心。若非如此,壶公所谓的恶人,单凭这正义,岂能是杀便杀的完的?”
那老者身子微微一顿,沙哑着嗓子又一次叹道。
“年轻人,你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何深陷这一潭污泥乱藻之中?”
“前辈却又是为何隐于这洛水之上做一个耄耋蓑夫?”
直至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位老人,便是后来汝南市肆口耳相传悬壶卖药的壶公。
后世传说他倾囊授妙练就长生之药,碧海寻奇制得不老之丹,鹤发童颜,身披鹑衣,足踏草履,妙手回春,其丹药能治百病。天黑市罢便纵身跳入壶中,次晨复出。时人逐利而效仿悬壶惑众。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刻的他,仍未肆头宿壶,接济黎庶,似乎求他便有这六段关卡的规矩,这其中便是茶道。
叶、具、水、火、味、心,六样俱全。
而娄江月所求之事,便是医治那曹节养子的顽症。
**************
月朗星稀之时,娄江月却已携我舍了船,告别壶公和那尚在梦中的曹公子,缓缓步入那荒茫的夜色中。
壶公不知怎的没有挽留,只是眼中闪烁着不明的光亮,令人并不是十分舒服。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特别注意我这个黄毛丫头,只当是个家奴仆从。
然而,就在我跃入岸边时他突然开口道。
“年轻人你和这个丫头,怎么……”
我心一惊,以为他要说出什么讽刺伤风败俗的话来,却听他继续道。
“怎么都让老朽探不出命数……”
我大呼一口气,精神松弛下来后很快便困得东倒西歪。
娄江月微微一笑,我隐隐瞧见他眼底缓然流动的一抹沉寂。
“前辈且不需再劳神费心……我与前辈一样,都是戴罪之身……”
说罢,他便利落起身,顺手揪起还在微微瞌睡的我,眨眼间便已经离开堤岸数步之遥。
“放……放我下来!”我两脚悬空,双手像溺水般在空气中拼命划着。
这种没着落的感觉,当真,很不喜欢。
“哦,抱歉。只当清晨打水提那水排习惯了,一时忘了手上是你。”
我幽怨的盯着他,却见他好整以暇的放下我,又是神速前行。一时我真不知让他放下到底是对是错,因为劳累的追击之旅再次开始。
行至二三里,我似乎都能感觉到壶公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终于再一次被枯枝碎石绊倒后,疲困加疼痛,我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要回城么?”我喃喃道。
他慢下步速,回首行至我身旁,趁着那清凉弯月,我望见他眼中含着似睡非睡的惺忪神色,唇边一抹浅笑。
却不料他开口,突然给我讲起了故事。
“昔日世祖(光武帝)出猎,夜归上东门,城门侯郅恽以夜黑难辨为由禁许帝入城,帝无策方改中东门进城。结果郅恽赏布百匹,因忠擢位;而中东门侯却遭贬罚。至此之后,十二门守备莫不效前朝,及至党锢之祸,守备尤甚。”
“我听不懂……”娄江月此时已然是梦中之人了,那话就像飘渺的云烟,愈发遥远。
“简单来说,就是眼下正值深夜,我们离了曹公子,我又非达官显贵,暂入不了城。”
“啊?”我哀嚎了一声,声音却因困顿跟细哼没太大区别,“我们不会就这样露宿荒野吧?更深露重,野兽潜伏,可谓危机四伏啊!公子你又为何非要弃船独行?那位老爷爷不是和你畅谈的很好?”
“很好?”他突然短笑一声,说不清是恼怒还是讽刺,低头拂了拂衣袖,接着忽而微微揪了揪前襟,抻了个懒腰,轻松道。
“事情完成了,便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和那种人在一起,礼尚往来,繁文缛节,都是拘束。为了让他满意,我身子骨端正的都酸痛了。哼,若不是为了契约……”
“公子……你又为何立这契约……”我含糊不清道,“有……什么用?”
他斜睨了趴在地上的我一眼,很鄙夷的摆手。
“做事只为求个有用?我一介凡夫俗子,只图个自在罢了。既然世上求我之人甚多,我又何有不应的道理?”
“唔,唔……”我身子躺在砂石乱草里铬的不行,睡意却再也阻挡不了,任凭脸贴着冰凉的地面,眼皮沉下来。
“夜弦,先别急着瞌睡,我问你。”他就那样居高临下的望着我,月色倾泻洒满他一身的凉意,但他却没有一丝的冷厉与乖张,“雒阳城墙有多少里?城门多少道?”
“不知道……”
“三十一里,十二道城门,东西南面各开三门,北开二门。东面上东门、中东门、望京门由北向南;南面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由东向西;西面广阳门、雍门、上西门由南向北;北面夏门、谷门由西向东。十二门统由城门校尉督察,每门设侯一人。十二门中,唯雍门、津门护卫略松,可稍施恩惠于此。但这些都不足挂齿,其实在广阳门处有一密道可通至城内……”
真是好的催眠曲,我保持着最后一丝意识,以示尊敬。
“我记不住……”
“眼下记不住不要紧,某一天逃生时记住就可以了。”
“啊?”我一下子清醒,“公子,我们又遇到麻烦了吗?”
他手指一拨鬓角扬起的乱发,微扬了脸轻笑道。
“祸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万事难保长久,无人万能且与你同行一路。就算是必定之物亦有变数。这便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
话音未落,便听远处的四周丛林中似有嘈杂声起,而借着那惨淡的月光,我似乎窥见了利刃泛白的雪亮。
“也许,最可怕的永远不是野兽……”娄江月缓缓转过身,仍旧是一脸惬意。不过那神色在月光下有种别样的诡异,“我们被包围了。”
我哆嗦着爬起来,还未有更多动作,便听到一个粗哑狠戾的声音阴森响起。
“这位公子,你刚才所说的密道,可是算数?”
我心陡然一沉,四周黑影如压顶般靠拢,一人倏尔点亮火把,我看清为首的是名脸带刀疤、贼眉鼠眼的中年男子。
可是,怎么……
娄江月突然目光定定的望向那贼首,那人吃惊得睁大眼睛。
“怎么又是你们!?”
***********
之后回京师的路,自然就是这伙夜里企图混进城内的劫匪送下来的。他们的确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曾经落入其手中一次,但最后还是娄江月略施小计侥幸逃脱。
这回,自然不是例外。
哪有什么密道,在城门卫队与劫匪混战之迹,我们安然入城。若不是娄江月早些察觉增添了我们的利用价值,此刻我们早就成刀下亡魂了。
“信不信由你,我的命我自己可珍惜着呢。”娄江月神态自若的这句话屡试屡灵,百试不厌。
当然,还要怪这些土匪出身草莽,太傻太单纯。怎么看来都是娄江月扯了谎,但就他自己来说,“我从来都不说谎话,谎话是你们理解出来的,不是我的问题。”
在他看来,那条“密道”便是这样的混入之道,不存在或真或假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