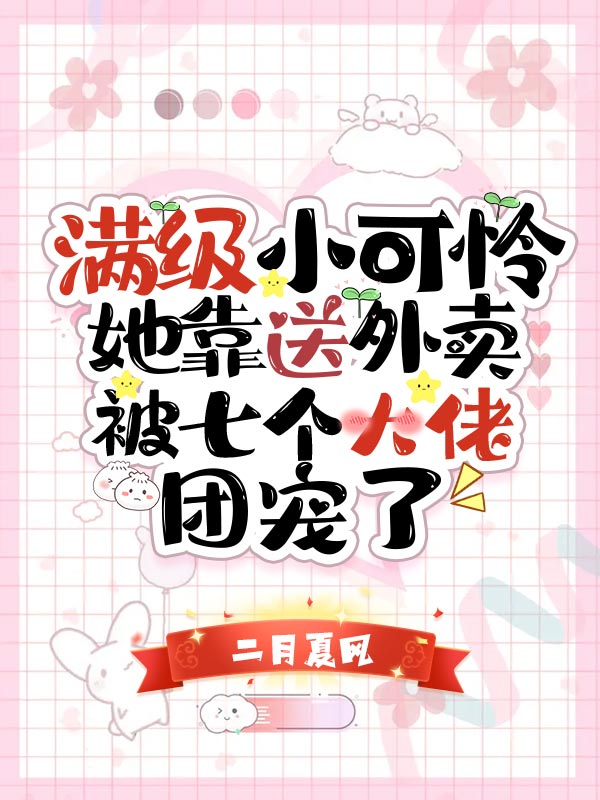在我的少年时代,有个算命先生来到慕容家,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姑娘也许活不到15岁,自那以后,我就对算命先生这种职业抱持起了一种敬畏之心。
在我看来,命运这种东西的玄妙就在于不能把握,所谓命数,也自非凡夫之心可以揣度,这些算命先生却敢于直面未知,敢于揭露隐在命运转轮下的某些可能,并将它出示给世人看,不可不谓之勇士。
虽然事实早就证明,那个算命先生的话只是一派胡言,可我觉得,那个关于我会在15岁时死去的预言,一定也是司管命运的神明于冥冥之中的安排,在某年某日,它发生了,它总会与日后的什么时候相连。
于是那日,我在朔州的街头,遇到了另外一个算命先生。
他告诉我,从我的命格来看,我本应该在15岁死去。
听完他的话之后,我颇为费解地望着他,他于是指着我手上一条隐蔽的线告诉我:“你看,你的生命线,在这里断掉了。”似乎怕我看不清楚,还特意拿手指沿着那条线画给我看,说,“或者说,它本该在这里断掉。”
于是我更加确信,命运这物件果然是玄妙的,事实上我并没有死,当然,也不排除掉我已经死了的可能,或者,其实我已经死了,我只是在假装自己还活着,或者我还活在我活着的时间里——我自以为这件事实践起来有那么一些困难,我有呼吸有脉搏,就连个子都还在长。
将我的疑惑告诉先生之后,他极为高深地说了一句:“不可说。”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招摇撞骗,于是便想拿回我的银子,却听到他说:“小姑娘,你的命运很奇特,可终会归于平凡,你生了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可这却未必是好事。浮生千头万绪,世人也都活在尘埃之中,又怎会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我的手因这话僵在了半空。
又听到他说:“……浮生长恨欢处少,劝君莫作独醒人。”
我将手收回去,放到自己的腿上,因为他的这句话而有些哀思,我垂目低语:“先生,我也许醒了太久,太久,都快要不知道做梦的滋味……”
可是因为一个人,我开始做梦了。你说,这会是一件好事吗?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我终究没有拿回我的银子,天色将晚,飞鸟声在头顶凄凄切切,路边树木上聚了许多乌鸦,一走近,它们就仓惶地飞。脚下的那一条路很宽,比刚刚进入朔州城时不知道宽了多少倍,我心想不愧是主干道,就算是骑马也完全没问题——于是我开始庆幸没有将马扔在驿站里,当然,马一直不归我管。
那条路不光宽,还有些漫长,好似永远也走不到尽头,我想,也许南云和枢棉早牵着马儿在尽头等我,于是渐渐加快了脚步。
也许是越心急越易出状况吧,走了不到一半路程,脚就很奇特地扭到了,道路很平坦,按理说不会有什么机会扭到脚,我却偏偏就是出了这样的状况,甚感无奈,只好挪到街边坐下身子,将白色绣鞋脱下,发现关节的部位果然肿的很高。
“这可如何是好啊……”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
然后在那个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乱糟糟的马蹄声,街上很空旷,四面的店铺大都打了佯,那大队人马逼近的声音便格外清晰,我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朔州又是个类似枢纽一般的城市,有什么队伍借道而行也算正常,于是仍旧一心一意地盯着扭到的脚叹气加惆怅。
直到那乱糟糟的马蹄声,在我面前戛然而止。
来者有七八个人,为首的人率先自马上下来,在我面前站定,我垂着眼,看到一袭白色锦袍,和隐在锦袍下的黑色软靴,顺着那个修长的身子往上望,某张记忆里也存在过的寂静清冷的容颜,使我不由的一愣,然后我听到空气中似乎有人发出轻微的叹声,还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些人都是我。
那是我时隔一年多,再一次见到白梓轩。他的眼睛似乎已经好了,眼眸细致而狭长,目光锐利寒冷,似是一种叶边锋利的芒草,不小心触到之后便是尖利的疼。我只觉得眼睛有些发酸,唇角动了动,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他是如何找到我的?
哦,我在不久之前当了他送我的簪子,有个词叫做顺藤摸瓜。
那他又为何会出现在朔州?
朔州是他治下的土地,他会出现在这里也在情理之中。
有没有可能,他早就知道我会来?
兴许,没准儿。
我就这样在心间自问自答了几个问题之后,总算没有在第一个问题上显得很傻。我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是来找我的吗?”
也许是他站的地方刚好生了一棵很大的街树的缘故,树杈斑驳的影子落到他面上,摇曳生姿,将他冷淡的容颜衬得有些柔和。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带着久违的冷寂温度,却是动听的:“慕容雪时,你让本王好找。”
“……为什么找我?”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有些搭错神经,他为何找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回京之后以为会在倚梅阁见到我,可是她的那个浓妆艳抹的王妃却告诉她,他养的那个小妖精早在几年前就被明察秋毫的她撞破“意欲行刺王爷”的不良居心,而她出于爱夫之情,便将那个小妖精除之而后快,为他排了忧解了难,只等他回来与她夫妻情深共度余生……
不对呀,既然华妃已经告诉他我已经死了,他就没有理由到处找一个已经死了的姑娘,除非他想被人认为是神经病,或者,他真的是个神经病。
“本王真的是疯了……”他的声音包裹着寒气。一只手如同冬日树木的枝干,苍白而有力,忽然握上我的手臂,将我毫不费力地从地上拉起来,拉到他面前,我光着一只不能沾地的脚,觉得那样一个姿势很不舒服,便微微皱了眉,可他似乎不打算放过我,我只觉得身子一轻,就被他扔上了马,他也随后跨上来,我闻到他身上的那股很好闻的香,微微失神。
“慕容雪时,本王真的是疯了,才会在知道你已死之后,仍然日夜不停地找你!疯了才会下定决心就算找不到你,也要找到你的尸体!本王疯了,才相信慕容雪时会那么轻易就死掉!”他的声音在风中被扯的粉碎,落在我心上如同仓促的雨点。
“本王真的是疯了,明明被你耍的那么惨,竟然还觉得高兴……”他最后这样说,“我真的高兴,慕容雪时还活着……我的雪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