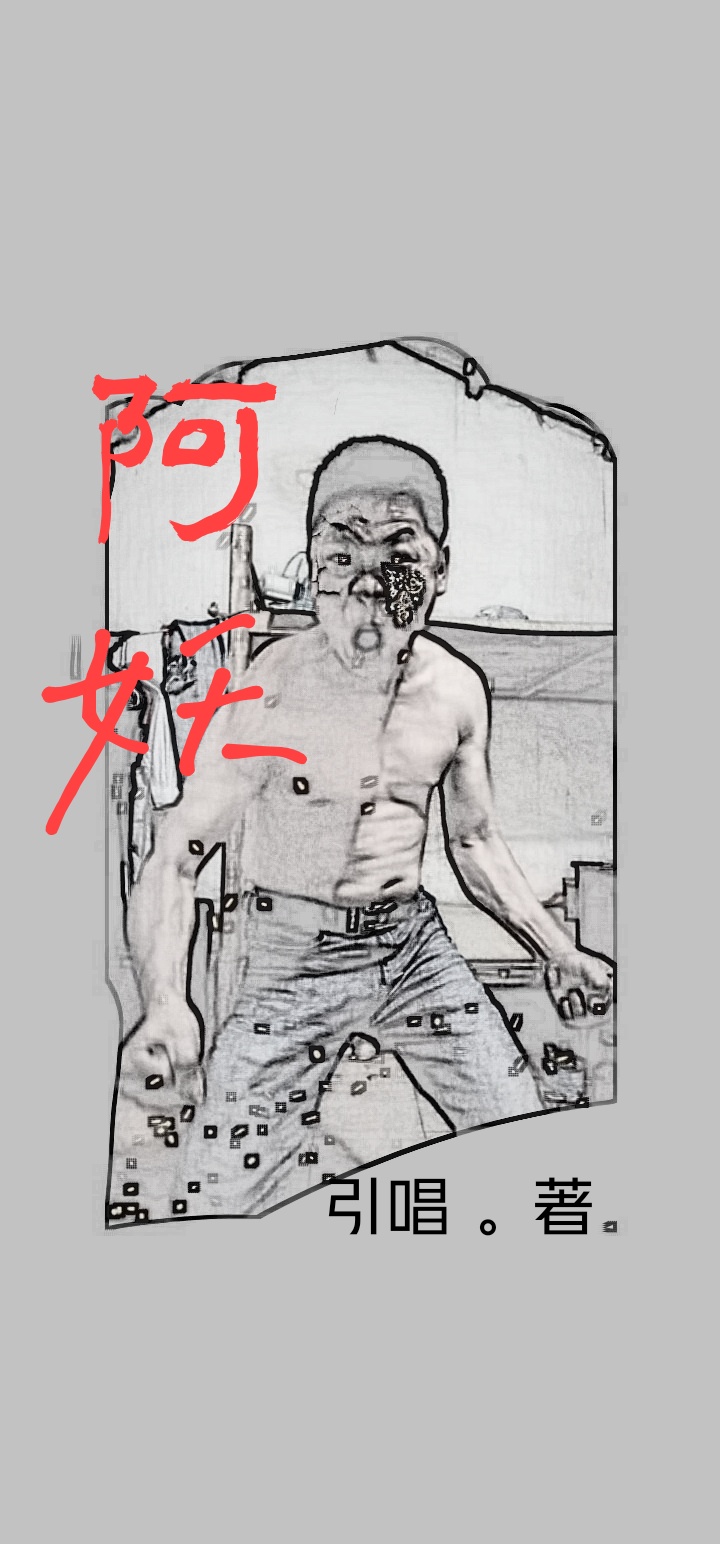我的这双眼睛,常常看到污秽之物——那些即使存在于此,也无存在意义之物。
对于那些不知痛苦为何,不幸为何,生存为何,死亡为何,而仅仅抱存着虚无的意识,在这个世界的缝隙彷徨而生的生物,不知是谁,从何时开始,规定了它们与人类之间,存在有模糊却清晰的界域。
因为有这个界域的存在,这个世界便也被强迫性的一分为二,人们把普通之眼所观之世,称为“合理之世”,即“常世”,而拥有我这样眼睛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则不能以寻常之理性来衡量,于是便生出了“离常之世”,世人口中所说的“妖鬼神魔”,便是这个世界的衍生物,然而世人不解“离常之世”的理性,一直以来对它的称呼,从“地狱”到“彼岸”甚而“妖界”和“魔道”,莫衷一是,其实这些叫法并没有还原这个世界本来的模样,而仅仅表现出了人类所认识的一个侧面,直到后来有人称之为“恒世”,它才以这个名字固定下来。
而你若问我为何物。
那可能,会是个很长的故事。
“我看到风,看到树木,看到大地,看到翻涌的云。
“我看到少年的眼光,如刻在沙石上等待被冲走的文字。
“啊,风自森林而来,你自海而来。
“踏着白色的浪朵,带来海的腥气,像一尾鱼……
“而我,坐在苍茫的时间里,等一朵花开。
“周围繁花似锦。”
“雪时!”一个声音打断我低声的吟唱,刚刚形成的印象顷刻如同溃散的沙堤,我立即从意识中抽身。
“姐姐?”就着夕阳昏黄的光,我看到了轻脚走到我身边的女子的脸。
“你又在没事制造一些乏味的印象了,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语言过于温和,即使创造出来,也只能留下寂寞而已。”姐姐在我旁边的秋千上坐下来,伸手挥散了因我的声音而聚集起来的“鱼”——当然不是指水里的鱼,而是对一些力量微弱,随季节迁徙的一些小型生物的称呼。
“嗯,也是呢。”我默默低下头去,看着被夕阳拉长的影子。
我常常像这样,一个人坐在庭院里的秋千,从早上一直做到暮色四沉,飞鸟从远方而来,停在对面的屋顶上,呆呆看着某一个点,偶尔歪起头,发出咕咕的闷沉叫声。不像这些每天固定会来的鸟,空气中的某些生物总是匆匆而去。
它们满载“污秽”,可是我却希望它们能停下来。
声音里,宿有某种力量。
古人信仰言灵魔法,认为说出来的事都能成真,因此而生祭辞,我觉得那向神明吟诵美好愿望的场景异常美好,单纯怀抱信仰,将希望寄托言语,而那些朴素渺小的愿景通过诗人之口流传,并在时光中被精心打磨。
那是语言和声音原本的意义。可是是从何时开始呢,人们驾驭语言,因为它有时候可以变得像凌厉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