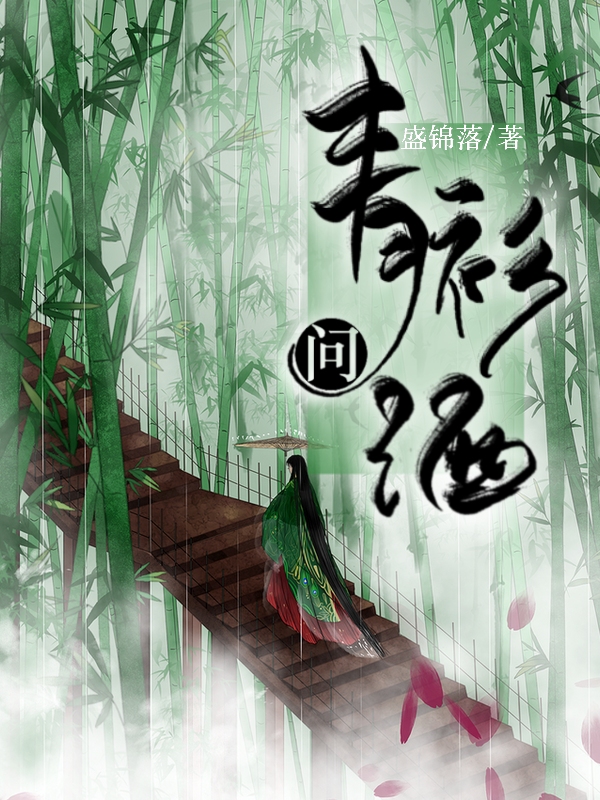陆女士恶狠狠地转过头,发现是谭瑾玙,士气顿时减掉大半。她一米六的个头,穿二十厘米的高跟鞋才能赶上谭瑾玙,现在比谭瑾玙矮不少,气势上毫无优势。她在琢磨着怎么怼回去。
谭瑾玙先发话了,“孟理是你姐姐家的孩子?他的父母都去世了?”
“是又怎样?”
“他的父母把他托付给你了?”
“对啊,所以他就是我的孩子,我想怎样就怎样,你管得着么?”
“您的孩子我管不着,但孟理来我这里,我就要对他负责。”
陆女士白了她一眼,没说话。谭瑾玙把手机放在陆女士眼前,问:“这是你们打的?也下得去手?”那是她刚刚拍的,画面是孟理发青发紫的手腕和小臂。
“打他怎么了吗?”
“我在这里警告您和您的丈夫,下次孟理再来我这里的时候,但凡他有一个新的伤痕,我就会让你们夫妻两个没有好下场。”
陆女士难以置信地看着谭瑾玙,“着你还管的宽呢!”说罢,冲到活动室里,一把抓起孟理的手腕,拖着他就走。“啊!”孟理痛的大叫一声。陆女士似乎抓得更紧了,她知道手腕是孟理的弱点,孟理的五官拧到了一起。
“您在干嘛?”谭瑾玙赶了过来,卡住陆女士,把她的手从孟理的手腕上拔了下来,捧着孟理的手腕看了好久,确定没有大碍之后,盯着陆女士看。陆女士像疯子一样扑向了谭瑾玙,元宝冲她大叫一声。
陆女士停下来,大口喘着气,她害怕并且讨厌狗这种所谓的宠物。孟理缩在谭瑾玙身后,躲着他的姨妈。“今天您要是想带他走,那您必须在这里向孟理保证,不毒打他,也不无缘无故的打他。”
陆女士气鼓鼓地看着谭瑾玙,看了好一会儿她才没好气地答应。孟理不情愿地和陆女士走了,回头看了谭瑾玙一眼,眼神又恢复了麻木和冷漠。
谭瑾玙看着两个身影离去,街道两侧是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知了在树枝上嘶鸣,一声声,像是孟理最后的挣扎。没办法啊,小家伙,时间不够,我也不好救你。她摇摇头,回到了办公室。小马正在接电话,是下一位预约的,谭瑾玙没有管,坐在椅子上,拉开抽屉,拿出上官笙给她的本子。
本子很厚,A4大小,是上官笙从七岁开始用的日记本。谭瑾玙从第一篇开始翻阅,她想再来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看抑郁症的模样。
从七岁的一页纸写六篇日记,到二十二岁的一篇日记写三四页,这个本子都没有被上官笙抛弃。他用了十六年,上学上了多长久,他就写了多久,每天的痛苦和绝望,开心和希望,他都一笔一划地记录下来。
谭瑾玙慢慢地看,孟理和上官笙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孟理说他是在四岁的时候父母出了车祸,爸爸抢救无效,妈妈则又撑过了一周,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把孟理托付给了她的妹妹。
而上官笙的父母学识渊博,也很爱他们的孩子,就是常年在外工作无法照顾上官笙,所以他是由爷爷带大的。七岁时爷爷去世,上官笙才开始有抑郁的表现,而且不稳定,时轻时重。
最关键的是上官笙周围的人大多是充满善意的,而孟理习惯了被排挤,有心理扭曲的可能。
谭瑾玙揉揉太阳穴,她感觉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但又没有证据,只好嘲笑自己空想。她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写了一个地址。
上官笙只留了这个地址,其他的信息没有留下一个。尽管谭瑾玙很熟悉这个地方,她还是又轻轻念了一遍地址的名字。那是她的初中,也是上官笙的初中,是他们两个人时空的交汇点。
地址下面有两个字:写信。
没有其他的联系,来来回回,只有几封信,谭瑾玙多看了几眼,收起了本子,她又开小差了。
突然想起来孟理沙盘才弄了一点点,还没收拾。谭瑾玙大步跨进活动室,看见了令她后怕的一幕。
孟理将一对夫妻、一个小男孩、一位年轻女性和一只狗的模型放在一个高高的沙丘上面,沙丘之下,不仔细看根本观察不到有几个模型被埋在里面。
被埋的模型有另一对夫妻、一个婴儿和几名学生。谭瑾玙倒吸一口冷气,这情况,不加强引导,孟理不得上天?
她收拾好沙盘,又准备了一会儿资料,结束上午的工作。中午带着元宝离开咨询室时,感觉背后一冷。谭瑾玙转身看了看,但好像是没什么会发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