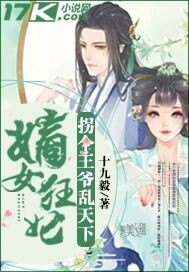霍东篱略微疲惫的回到家,请辞信还放在家中,可他已经跟刘澈说了,这个地方他是真的不想在待下去了。尤其下午见了花爻那样的状态,他更是恨不得马上带她离开这个地方。
刘澈没有直接表态,只是看着他,然后冷笑着走出了大殿。
或许自己辜负的人中也包括了他,可到底是谁辜负了谁,又怎么说得清。是他带他走入了这朝堂,树立了正义之心,可也是这人将曾经教会他的所有给颠覆得彻彻底底。
他抬头,看了眼灯笼高照的门匾,缓缓笑了笑,这个霍家,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呵。他走了,又会怎样呢?一代家族的没落?还是某些家族的幸灾乐祸?
可是这些,说到底,于他又有何干。顶着一个孝意的名头遵从着一层又一层的束缚,最后苦苦挣扎的自己却还落得个千夫所指。
呵,这世道真是好笑呢。
他推门进入了府中,吱呀的门声显得清净的府中更加清冷。这家不似家的地方不过是供他一个避雨遮风之所,可这心中所吹打的风雨他们又怎会怜悯的施舍出手替自己遮挡?
“霍祛。”他抬头看向仍在替他守门的人,微微笑了笑,问道:“她怎么样了?”
“花爻小姐中途醒来之后便,便走了……”
“为何没告诉我?整整几个时辰,为什么没人进宫告诉我!”霍东篱冲他吼道。又是不辞而别,又是不辞而别!这个女人是真当他的心是随时敞开的么!霍东篱有些气愤的攥紧了拳头。
“老,老夫人不让告诉少爷你。”霍祛有些胆怯的说道,他家少爷为什么每次情绪失常都跟那个女人有关啊!那个花爻可不可以就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了啊!
“她不让告诉,你就不告诉了?!”他冲霍祛吼道,怒目瞪着他。
身后却传来一威严的女声,“放肆!东篱,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声木拐杖杵地的声音赫然震慑了情绪有些激动的霍东篱。“你再说一次。”
霍东篱紧攥的拳头更是紧紧的攥着,迸射的青筋直如雨前蚯蚓般躺在皮肤上,他缓缓转身,看向那有些古稀之色的妇人依旧威严许许的矗立在那儿。他缓缓开口道:“母亲,您还要怎样?”
“我想怎样?哈,这话该是我问你!东篱,你也不小了,学学你舅舅吧!别再做些愚不可及的蠢事了!”
“蠢事?什么是蠢事,什么又是聪明的事?学舅舅?母亲,你是真的不知道么?你真的愿意我那样做么?”
“他能做的你凭什么不能?你是霍家长子,这点责任感你应该有!”
“呵呵呵呵,”霍东篱看着那位妇人竟笑了出声,这笑却苍凉得让人心寒,“原来,所有的你都只是顾全霍家,呵!那你当初为什么连那个男人是谁都不敢说出来!为什么让我苟延活了那么多年!现在你却用长子的身份来告诉我那些,所有的那些我必须去做!”
“你……”霍老夫人颤抖着手指着他,竟不相信他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你这逆子!”
“逆子?呵,你到底是为了霍家的颜面还是你的颜面啊。若不是舅舅带我进入那个社会你肯回来找我?若不是我建功立业,小有所成,你肯告诉我我那不知姓名的爹是何人?霍夫人,你首先是那人的情妇,其次才是我的娘吧!”
“啪!”霍老夫人颤抖着手打向霍东篱的脸颊,本是毫无破绽全副威严的脸庞也因为愤怒显得有些扭曲。“你,你给我滚!”她扶着拐杖身形仍然有些不稳。
霍东篱看了眼她,眼神中的悲伤一闪而逝。这个女人从小就抛弃了他,上次受伤归来见她那样为自己悲伤他是真的差点就心软的了,看她那么喜欢敏敏也以为她不再逼着自己追逐权势了。可是,呵,若不是她的刻意接近敏敏,又怎会知晓她是乌智人,又怎会告诉张青,他又怎会忍心将那个无家可归的女子撵走?!
他吸了口气,依旧平淡的说道:“霍平性情敦厚,且信服于我。武艺也算脱群,又从小耳濡目染官场规则,不出两年他也能独当一面。至于你自己,霍楠他即使对你没感情,好歹也会看着舅舅的面子不会为难于你……”
“你说这些干什么?”霍老夫人将拐杖杵在地上,发出闷闷的声响,“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
霍东篱抬抬头看向她,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呵,本该是他最亲近的人可为何却从来不曾将他当成亲人来看待?他笑了笑,说:“从小到大,我好像没一件事能趁你的心呢。”说完他转身。
“站住!你给我站住!”霍老夫人在身后大声的叫唤,可那人勾着嘴角却一言不发头也不回的往外走了。
“少,少爷!”霍祛尴尬的站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决,他上前两步挡在了霍东篱跟前,伸出双手将他拦住。“少爷。”
霍东篱看了看他,微微笑了笑,“霍祛,你也要挡我么?”
霍祛咬着唇,只是看着他,脑袋中却不停的转换这人平时的一言一行。他是那样的青春飞扬,却被困于这权势囹圄之中,如今,如今好不容易拜那人所赐愿意挣脱出去,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拦着他。
他鼓得大大的眼珠子直愣愣的盯着他,缓缓他让开身,低声说道:“少爷,保重。”
霍东篱看了眼那低垂着头的人,笑了笑,一脸轻松的走了出去。
屋外春寒料峭,漆黑一片,他虽不知现在去往何方,可心却坚毅无比,轻松无比。
进入皇宫,进入官场这七八年来,他似乎一直都以执拗之姿傲视群雄,似乎都以为只要问心无愧,其他都无所谓。可这些年度过的时光,风光过,畅快过,大笑过,也大悲过。
那些经历了生死之后换回的荣耀曾经无比享受的刺激着他的神经,可渐渐的,看着那些越来越残忍的画面,那些从白骨堆中走出的男儿,笑不似笑,哭不似哭,茫然于尸山血海中,竟感觉找不到了回家的路。
他才知道,活下来真的是一件好幸运好幸运的事,而那些轻易用他人生死来成就自己威名,将他人生死儿戏,当成自己谋划的一步棋的人,他真的无法苟同。
茫茫大街上,已然宵禁。
“又是闯了宵禁呵。”霍东篱失神的笑了一下,那个女子总是可以那样轻松随意的拨乱他的心弦,总是可以那样自以为是的做着最不利己的举措,总是让他想忘却忘不了呵……
霍东篱叹息一声,抬头看去,再次望了望这繁华落下的长安,向城外走去。
一路上他微微忐忑,如果可以,请让她在那里,他曾在那里错过了她,如今可不可以再挽留住她?
灵隐坡上冷风希希,霍东篱看了看那泛着微微黄光的木房子,心中又悲又喜。漆黑的夜,是谁的灯照亮着自己的整个世界,暗淡的人生,又是谁照亮了她冰封的心灵。
推门而入,霍东篱恍惚又似见着了那年冬季的景象般,她畏畏缩缩的蜷在那一次,眼神中的流光异彩在看清是自己之后的暗淡无光。
霍东篱心中一痛,向屋内看去,那女子好好的坐在桌旁,双手却在细细的雕刻着什么东西。
霍东篱无意识的松了一口气,他和上门,走上前去,看着女子略微生涩的手似在削一柄小木剑。他看了看那女子投入的眼神,满脸平静又祥和,他坐在她旁边,一言不发。
花爻却微微笑了笑,“你来干什么?怕我又跑了?”
霍东篱被她逗笑了,弯了弯嘴角,看着她,反问道:“不是么?你不预备跑?”
花爻剜了他一眼,手中的活计却也不停歇,她故意叹息一声,“是啊,谁让某头犟牛不肯包庇我这个逃犯呢?”
霍东篱笑着指着她,笑容缓缓却凝固了下来。“我辞官了。”
花爻手上的动作一顿,又接着笑着继续雕琢,说道:“好啊,霍大头找到什么前途好的事了?也带上我啊。”
“我,跟家里也决裂了。”他又自嘲的笑了笑,“如果那算家。”
花爻放下手中的活,转头,第一次正眼看向那人。
“我,我想带你走,阿爻,我们一起走吧。”
花爻抿着唇不说话,微微低下头,似在思索。
霍东篱有些紧张又有些焦急,“你可以不喜欢我,甚至讨厌我,可是,阿爻,这里真的不适合你。如今都这样了,你还回到这里干嘛?你上次劝我之后便不辞而别,我想你走了也好,至少为了家族我还是可以在那官场好死不死的呆着也不用顾忌什么。可是,你又回来了,你白天那样真的吓坏我了。阿爻,我们走吧,就当结伴同游,看遍这为之疯狂,为之奋斗过的山河,好么?”
花爻抬头看向他,这个男子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下了那一身的骄傲如此平和的同自己讲话?是不是大家都要痛过之后才知晓,原来能在一起真的好不容易。
霍东篱忐忑的看着她,注视着她的每一个表情。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霍东篱依旧执着的看着她。缓缓花爻,开口说道:“好。”她笑了笑,“后天,我们就跟欧阳叔叔一起走,离开这,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笑容真的是有感染力,可以传播的呢。
霍东篱跟着傻笑起来,花爻继续雕琢着手中的木头,屋内,昏黄的灯光不甚明亮,可是真的照亮了这二人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