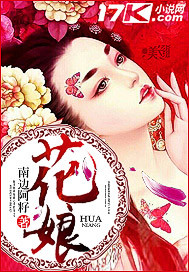主账中,苏广守在塌边,几服药下去,张青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奔劳担忧了两日的众将领,军医也终于可以踏实的休息一会。大战在即,谁也不敢托大。
苏广一手撑头枕在桌上,上下眼皮早已打起了架,连续的睡着了倒,倒了迷迷糊糊的看了看见没甚异状又继续睡。
榻上之人,面目平静,的确已无大碍,他强自挣脱捆锁,意图打开那被深深尘封的记忆,意图颠覆那人告知他的曾经过往,意图重温同那女子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可一波又一波的困惑,执迷如同滔天巨浪般猛然拍向他,他终究无可奈何。
“以我之名,告你实情。澹台花爻,敌国妖女,善攻人心,潜心隐匿;白面修罗,杀人如履,投毒无形;毁你功绩,殁你威名,乱我朝纲,损我国运,以汝之姓,歃下重誓,他日遇见,亲手刃之!”
睡梦中那阴桀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牵着命运,带着诅咒般的设定着这人的宿命。
张青身处一团混沌中,四周黑暗至极,他瞧不见那说话人的面容,却条件性的辩驳道:“不,不是的……”他微微蹙眉,呢喃道:“她,不是这样的……”
似没料到他会有如此抵抗般,那声音顿了一顿,继而更加桀然的说道:“敌国妖女,善攻人心,又惑你志,鼓吹谋逆!战场对阵,血溅当场!”
张青苦痛的抱着头蹲在地上,却仍是不愿妥协般的呢喃道:“不,不要……不可以。”
那声音这次却骤然加快语速道:“那个孩子,是个孽种,孽种!杀了他,杀了他!”它似意识到那人已经对澹台花爻有了抵抗力般,竟换了个方式。
果然张青脸色一松,也没了那般大的阻力去抗衡,他萎顿的抬抬头,重复了一下,“杀了他?”
“对,那个孩子,必须死。”
张青缓缓起身,颀长的身姿连半分影子都没有,只让人觉得孤清清。
“杀了他……杀了他。”他低低的呢喃着犹如无知孩童学着说话般这样不停的重复,那人阴桀的声音也带着诡秘的笑意渐渐消散。
睡梦中的的张青缓缓睁开眼,平静的起身,坐了起来。他看了看四周的陈设,目光定在瞌睡中的苏广身上,死灰色的眸子渐渐有了生机,染上层层亮色,他就这样静静的坐在床上定定的望着那人。
“砰!”
苏广皱眉揉揉撞上了桌面的额头,又习惯性的抬头向那床上看去,迷糊糊的点了点头,又继续闭上了眼。
张青好笑的看着他,下床站起身。
苏广猛然抬头,又向床边看去,顿了一顿,突然立起身,朝张青那儿走去。
“大,大将军,您,您醒啦!”
张青淡然的伸手,欲倒茶,苏广立马接过,傻兮兮的只是望着张青笑。
张青微微笑道:“苏广,怎么了?”
苏广看了看帐外的天色,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该大亮了,他抓抓脑袋,摇摇头,“将军还要再睡会么?”
张青也朝外看了看,淡淡的说道:“昨晚辛苦你了。”
苏广笑了笑,道:“将军你这一睡可就睡了两晚呀,不单我,连诸位军医,有军衔的将领都担心得不得了。”他瞧了瞧张青的神色,又解释道:“没办法,将军在那儿晕倒,这进进出出总会给人瞧去,不过好歹还是将消息控制在了可控制的范围内。”
一听他提及,张青微微思索,却不是很清楚自己昏倒的原因,他又睁了睁眼,却未果,想起自己身体本就有恙,便问道:“军医可有说我晕倒的原因?”
苏广摇了摇头,“军医都束手无策,不过,幸好临走时,爹爹给了我薛神医的方子,好歹还算是派上用场了。将军,你可觉得好些了?”
张青点了点头,“没什么大碍了,东篱可找到了?”
苏广闻言脸色一变,张青敏锐的捕捉到了异样,“还不知所踪?”
苏广摇摇头,“踪迹是算有了,只是,只是,霍将军被他们擒去了。他们放言,人质对换。”
张青握着茶杯的手停在空中,天未大亮,苏广有些看不清他的神情,半晌张青开口道:“天明,拔营宣战。”
……
外面的拔营动静让昏昏沉睡的花爻不安的睁开眼,帐帘被掀开,透出一丝白光花爻皱皱眉,迷糊的看向外面。
长恭也迷迷糊糊的揉揉眼睛,抬头问道:“阿娘,外面怎么了?”
花爻站起身,因为有些头晕的缘故她起身之后稳了稳,站在牢笼边努力想向外看,已经过了两天了,可却没有他的一点消息。那些送饭之人她也不敢唐突的问,如此心中忐忑的过了这两天,而今日外面那样大的动静,是不是他醒了?
正在她踌躇揣测之际,外面已经走了一人进来,花爻眼神一亮,立即唤道:“左将军,左将军!”
左康冷眼看了看她,他身后跟着一小队人,纷纷全副武装立矛而立。
“姑娘有何事?”左康冷冷的问道。
“左将军,他,他好了么?”
左康扫了一眼她,冷笑了一下,“姑娘可是问谁?”
花爻被这冷嘲热讽的一问,更是脸色惨白,她抿了抿嘴唇,“张,张大将军,身子可,可……”
左康冷然一笑,轻蔑的看了眼她,“好一个乌智王妃呵!马上要同你夫婿见面,你竟只关心别的男子?”
花爻一听,只反问道:“他醒过来了?”
左康瞥了一眼她,冷笑涟涟,负手对着身后之人吩咐道:“将他们带出去。”
“诺!”
长恭见那十多个彪形大汉向自己走来,停在地上的牢笼也随着那些人的抬举而晃动起来。他惊恐的抓住花爻的小腿,瞪大了眼珠子,花爻将他护住,冲左康叫道:“左康!你胆敢趁张青病危之时妄动权职!我要见他,放我出去,我要见他!”
“澹台花爻,你好大的口气!”左康沉声怒吼道,大掌一挥,那十几位停下动作的侍卫也又继续抬着往外走。
刺目的光亮突然射来,花爻反射性的将长恭的眼睛用手捂住,自己也闭上了眼。
待适应了那样的光亮花爻睁开眼,便见四周旌旗凛凛,士兵铠甲瑟瑟,戟盾威武,人人整装待发,战马昂扬,号角沉闷呜咽的响起,带着冷凛的战争气息传遍了整个平原。
花爻心中一紧,左康见他模样,冷言道:“张青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哼,这两国因你而开战,你竟还记挂着另一个男人。哼哼,这妖女的称号可真担当得上呢!”
花爻不发一言的看向他,也不想去管他的冷言冷语。
左康又仔细打量了一番花爻的神情,转身便头也不回的翻身上马往前走去。
军旗猎猎,带着大国无与伦比的气势朝着那前方行去,犹如一柄即将出鞘的宝剑,随时等着向敌人挥下致命的一击!
天狼河,一如既往的缓缓流淌,而此刻河的两岸林林站立的军队赫然对峙,两两相望,一触即发。
两军之前,帅旗随风而鼓,发出猎猎的声响,一黑一棕两匹高头大马之上,两军首脑威严的坐于其上,沉稳如山,内敛如火。
日上中天,万里平原之上,一水相隔,秋季,北雁南归,莺莺长鸣,猎猎的风声之下更显得天空的寥寂。
彩旗一招,两军首领都微微颔首,双方阵营中,分别拉出一囚车。囚车滚滚驶出,压着布满小石子的道路步入双方的视线。
张青一见坍圮在囚车里的霍东篱满身血污,一身伤痕,放松的面部也紧紧的绷了起来。昭伊琛郓一见那囚车中立于囚车一角的妻儿,本是平静的面容上勃然作怒,身形也止不住的欲往前倾。
孟获大刀阔斧的往阵前一站,大嗓门吼道:“朝音土狗,速速归还我朝太子,王妃!惹毛了你孟爷爷这铁头锤可不是说着完的!”
他一相叫骂一相舞动铁锤便向那牢笼砸去,“碰碰!”作响。
朝音这边见了霍东篱被拷打得那般模样本就心中怒火腾腾,又见那人如此野蛮粗鄙,那百千斤重的铁锤砸向霍东篱更是惊得人心惊胆颤。
前锋赵又行打马出列,横槊于马前,怒道:“蛮野匹夫!卑劣无耻!我朝音泱泱大国岂容你如此儿戏!”
孟获大笑连连,那刺破耳膜的笑声震得河对面的长恭也止不住的捂住了耳朵。
昭伊琛郓眼尖的看着那女子不舒服的蜷缩着身子,打马往前了一步,止住了孟获的继续叫阵。
“张大将军!朝音素来有仁义礼仪之称,用妇孺孩童来作人质实在有失国本!如今霍将军我们归还,也请归还朕的王妃,君子之战,该当顶天立地!这万里山河,若是朕实力不济,何当双手奉上,若是朝音兵力不及,也实属天意!”
花爻看着那人站于阵前,威风凛凛,英气逼勃,心中满是酸楚。
他还是要这样为她,这一仗,他即便倾尽所有又如何能抵挡这虎狼之师?而好不容易握有的砝码他也要如此轻易丢弃么?
花爻想得难受,那活生生立于河对岸的人虽是隔得那般远,可却仍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暖暖情意。
他告诉她,阿爻,我来接你回家……
张青冷眼看着这二人的眉目传情,心中莫名的就腾升出一股怒火。
他翻手从近旁手下的腰间取过短剑,拍马而起,凌厉的剑势在空中挽起一个剑花,便直直的向那囚车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