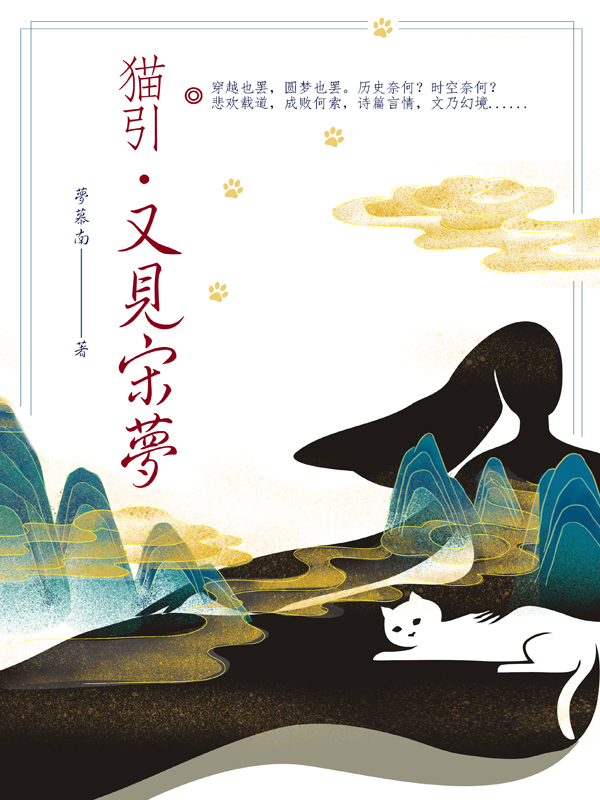乌智地牢,阴湿潮冷。
夜间,一袭王袍终于进入此处,守卫恭敬的立定问候,那人却如一堵厚重的墙般,脸上的神情阴沉怖戾,直让人觉得比这阴寒之地还要冷上更多。
甫一进入地牢,昭伊琛郓双肩向后微微用力,披在身上的貂皮大衣便随之滑下,身后阿顿都适时的接住,并没发出一声声响。
深幽的地道里,厚重的皮靴踩在地板上发生阴森的声音,一如那人此刻的心情一般。
“大汗!”
琛郓仍是面无表情,不发一言。
阿顿都从身后微微示意让他开门,那名侍卫立即躬身将地下室的牢门打开。甫一打开,一股湿臭夹杂着霉腥味扑面而来,琛郓皱皱眉,吓得那侍卫脸色白了白。阿顿都微微目视他,那人才稳了稳心神,将琛郓请了进去。
牢房内更加的阴沉昏暗,里面的空气较之外面更加不流通,隐隐的房内一角蜷缩着一人,头发披散于身上,混着血水黏在了那人的满身。
琛郓微微皱眉,却仍是又向前走了几步,阿顿都想起昭伊敏敏的嘱托,心中颇觉忐忑,亦是跟随着向前。
琛郓却在那人跟前几丈处站定,阴鹜的看着那不知是睡了,还是昏了过去的人。
“弄醒他。”
阿顿都领命将刑具旁的冷水舀了一大瓢。
“哗!”冰冷刺骨的寒水夹着盐深深的刺激了那人的感官,“嘶!”,那人痛苦的发出让人浑身起疙瘩的声音。他缓缓的动了动,长而粘稠的黑发之后那双眸子却亮如明月。他看见来人,轻轻的嗤笑了一声。
“好!”琛郓见他如此无礼,不怒反笑。走上前去,俯视着如困兽一般颓废的人,“霍东篱,我敬重你。”
“嗤!”霍东篱动了动腰身,身子略微松懈,惬意的躺在身后的石壁上,“承蒙夸奖。”
昭伊琛郓凛了凛神色,严肃道:“花爻曾经救过你性命,你难道要眼看着她去死?!”
霍东篱讽刺的抬眼看了一下他,一手放在蜷起的膝盖上,微微抬头,“你认输,她便无碍。”
琛郓寒着脸走上前,阿顿都心下骇然,这家伙不是找死么!若大汗真对他动了杀心,那,那公主那方又该如何交代!
却不料琛郓只是紧了紧拳头,缓了缓神色道:“霍东篱,你是聪明人,既然甘愿被抓至这,又何苦做这些徒劳之举呢?白白受些伤,”他笑着看向那人,淡淡的反问道:“何必?”
霍东篱却不以为然,依旧道:“这与你又有何干?”他微微笑着摇了摇头,“一个男人的天下却要用自己的女人来换取,乌智大汗也不过如此么。”
琛郓怒意横扫向他,可那人却仍似不知死活般笑看着他。琛郓蹲下身,伸出手捏住他的脖颈,恶狠狠的说道:“你这话该同你那伟大的舅舅讲!同你那伟大的君王说!”
他使劲的捏住他的脖颈,霍东篱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却仍是怜悯的看着怒气冲冲的人。
阿顿都连忙出声唤道:“大,大汗,大局为重。”
琛郓似也听了阿顿都之言醒转过来般,他甩开他的身子,如同丢弃一件物事般的不屑,他站起身,继续道:“有本事,战场上明刀明枪的同我争这天下。你若不耻,该不耻的人是他张青!”昭伊琛郓眸子中迸射出冷然的光芒如同沙漠中圆月时分占领最高高地却被其他狼群围剿的独狼一般。那样的不屑,漠视,却又带着深深的恨意。
霍东篱嗤笑一番,低低的说道:“你就不可耻?”
昭伊琛郓回头瞪着他,霍东篱却不予理睬,“不是你骗她说月华沙死了,她会对舅舅绝望?”
昭伊琛郓一震,微微眯了眯眼,霍东篱见他神色一变,更是鄙夷的看着他,“你连时间和空间都不敢给她,就这样独断的告诉她,要带她走,你敢说你不可耻?乌智大汗,你可真是高明呵。”
昭伊琛郓深深的凝视着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霍东篱被这充满真力的笑声震得五脏中的气血又乱窜而翻滚,他却生生的咽下了那浓厚的血腥气。
琛郓笑够了,猛然停下,眼光却嗖然的射向那人,“霍东篱,难怪,难怪呵……”他又微微摇头笑了笑,“你这样文武双全,又故作糊涂之人确实是他的大敌呵!”说完他又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诡谲的笑道:“霍东篱,你自己甘愿送上门来,是笃定他一定会救你么?”
昭伊琛郓的笑声以及那莫名其妙的话对霍东篱的心神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他沉着脸,“什么意思?”
昭伊琛郓复又看了看他,转过身,似轻松的说道:“罢了罢了,你愿意用你的所有来赌明天,我又何惧?即使没有你,我也会救下她!”
霍东篱突然叫道:“你说清楚,什么意思!”
琛郓不予理会,突然,他低低的笑了起来,转身惬意的看向那几欲咆哮的人,他再次勾了勾唇角,“对了,她应该没告诉你们,他要杀的是谁吧。”见霍东篱仍是一副怒气勃勃的样子,他突觉得一股复仇的快感从心底蔓延开,“长恭啊,呵呵,长恭,不就是张么?”
他看着那人猛然一震,那丝淡淡的快感更加肆虐的在全身每个细胞内乱窜,可心底却滋生出一丝疼痛的悲哀。他姓张,呵呵,她连儿子的名字也要唤成这样,这样念想着那人。
他再也不看身后之人,迈开大步便朝外离开。阿顿都看了看牢房内仍未反应过神来的人,他淡淡的叹了口气。
这般孽缘如何得解,那人又有几分胜算能在他心中留下一席之地?阿顿都苦笑着摇了摇头,五十步笑一百步,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他稳了稳心神,开口道:“敏敏公主让你珍重。”
话已带到,他便再也不想多呆上一分了。可霍东篱却猛然扑了过来,好在他的锁骨早已被钢构给勾住,才让阿顿都躲过一劫。
“呲!”
“咚!”
阿顿都回头看了看那因为疼痛而倒退,却因受刑而身型不稳导致全身栽倒在地的人,那人却不顾疼痛,龇牙咧嘴的冲他问道:“他说什么!他胡说些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阿顿都淡淡的叹了口气,这些不归他管,他只管那人安心快乐。
牢门重又关上,隔绝了一切,霍东篱却歇斯底里的吼叫道:“胡说,胡说,昭伊琛郓,你胡说!!!”
可这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语除了愈发显示出内心的惶恐不安之外,还能说服谁?
那一模一样的眼睛,那二人相处的和谐画面,花爻每每奇怪而故意扭转的视线。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霍东篱颓然的锤着地板,深恨自己的反应迟钝!乌青的地面淡淡的晕上一层红,一声一声砸地的声音犹如一声一声的扣心自问!“不可能,不可能,舅舅……舅舅,长,长恭是,是你的孩子啊。”
昭伊琛郓出了大牢,怔怔的立在院中,阿顿都稍晚了一会,出来见他似在等着自己,心下歉然,“大汗。”,他上前,垂首唤道,替那人披上了外套。
昭伊琛郓面色不变的任由他,伸手也拢了拢貂皮。似方才在天牢中耗费了他过多的精力般,他淡淡的开口问道:“敏敏,她还好吧。”
阿顿都缓了缓,仍是恭谨的道:“霍东篱对公主有救命之恩,放不开也是理当的,只是大局为重,公主会理解的。”
“是么?”琛郓苦涩的笑了笑,望了望如水的月光,微微闭上了眼睛,“我们果然是亲兄妹呵,这脾气,又会差到哪儿去。”
阿顿都垂首不语,他跟了琛郓十数年,从孩童时期便跟着他了,对于那刁蛮任性却又心思单纯,面冷心热的小公主自然也是熟悉万分。
昭伊琛郓禁锢着她是对的。
琛郓叹了口气,睁开眼,只是盯着那月亮出神,“那女人一直不信任我,阿顿都,你说,我若为她舍了这天下,她可会跟我走?可会依赖我?信任我?”
阿顿都知晓这只是他的自问,却不需要别人回答的,他亦只是安安本本的做个倾听者,不多言,不多语,只为让那人吐掉心中烦闷。亦如那人一样,想起那梨花带雨的小脸,曾经笑容灿烂的面容自从回来之后便再无笑颜。
“她为何就不愿跟我走呢?什么叫利用完了,我们,也完了?呵呵,她只当我从头至尾都在利用她么?”他头痛的皱皱眉,抚抚额角,“她怎会这样想呵。”
琛郓连日来已被这战役忙得焦头烂额,朝中以诺顿王为首的王公大臣趁此机会竟竭力求和不愿开战,至于王妃被掳有伤国体这样的举动也自然被其忽略,甚至以花爻入宫四载挑拨是非这些缘由为理奏请革除花爻妃位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号。可他却一力扛下,打出了迎战的旗号,朝中那些贵族见势干脆告病不朝。琛郓心中虽然盛怒却发作不得,一面一一击破,劝服,一面暗中联络那夜那黑衣女子筹谋军饷一事。
他早已身心俱疲,他自己也怀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可是,他还是做了,义无反顾的想要向天下人宣誓:
他,昭伊琛郓的女人,是他最珍视的世间珍宝!谁动,必诛!
可这些,那人可会懂?
“若这是利用,花爻,那也是你利用我呵……”月色中,那人迷蒙的神情看向那漆黑如墨的夜空,淡淡的月光下,似又见着了那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