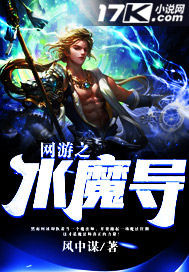仙童惭愧归惭愧。
此时此刻,人精和妮可降服了牛王,一把大火烧了牛王洞,夫妻俩迎着一轮喷礴而出的红日,双双走在回家的路上。大雾还没散去,天地间一片空濛。露水十分新鲜,淋淋漓漓溅在裤子上,连脚上的鞋也浇得湿漉漉的,滑不留足。
妮可笑了笑,干脆脱下鞋子拿在手上,一路山下进发。衙役们都很开心,缴获的战利品也不少,最多的是金元宝和百花醪。大家都没有想到:原来洞中的喽罗和仆役,都是金元宝变的,牛王一走,法力失效,他们自然而然都显了原形。
至于百花醪,那可十分珍贵,小小一滴,贵逾黄金。打开瓶盖,就有一股大自然的清新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浅浅地喝上一口,那份香,那份甜,那份没掺任何杂质的醇厚,让人沉醉。能喝上一口,大家也算是开了眼界,韵足了洋味。
妮可脸色红润,兴高采烈。夫妻俩能够齐心协力,联手制服作恶多端的牛王,而自己能毫发无伤,全身而退,她已经感到很开心,很满足。能够跟自己的爱人厮守在一起,同荣辱,共进退,哪怕再苦再累?她也愿意,甘之如饴。
人精骑在马上,不由得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妮可叽叽呱呱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清。假冒进士朱平之名,来福来郡平德做这个知府,毕竟是假的,冒名顶替,名不正来言不顺,人精时时刻刻都担心冒险,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惧当中,谎言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永远也见不了阳光。
露馅还在其次。
其实,人精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妮可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一旦败露,自己岂不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妮可会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爱情?两人之间一旦有了裂痕,就不可能再有纯粹。裂痕它永远都是裂痕,就是弥合了,也还存在。一想到这里,人精有些后怕,也有些担心。
可命运就是这样,你越是迴避,越是害怕,它偏偏要对着你来,对着你上,哪壶不开?偏提哪壶。让人精迴避不了,也哭笑不得。真应了那句古话:该来的总会来,要来的躲不了。让人精连假冒的知府也做不了,难道这是他的宿命吗?
人精不信命,可他也不得不服。
恍惚之中,人精坠蹬下马,上了白玉台阶,府衙里吵吵嚷嚷的,乱成了一锅粥。见到他,师爷何平带着大愣和二愣,眉开眼笑地迎上了上来,拱了拱手,结结巴巴地说:“老爷,不好了,明天你的同年、福来郡的推官崔福生要来,要来给您送匾,老爷,这可如何是好啊!”
何师爷的一张苦瓜脸拉得很长、很长,愁眉不展的样子。关键时刻,他根本不像个师爷,倒成了一个习惯于吐糟的怨妇。大愣和二愣也吓得不轻。一个袖着双手,不停地用脚尖,在地上划着圆圈;一个像拉碾子的驴一样,围着人精机械地转来转去,转得人精心跳加快,头昏脑胀。
“二愣,你能不能停下来,再转,我都快崩溃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这个知府老子不当了,老子还真不稀罕?”人精狠狠地白了大愣和二愣一眼,接着又说:“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先乱了阵脚,给对手以可乘之机,镇定,何师爷你懂吗?”
“老爷,我倒是想镇定,可怎么个镇定法?一想起这事,我的栾心就蹦起老高。”何师爷一脸苦笑。
“是啊,是啊!冒名顶替那可是欺君之罪,发现了要砍头的,小命不保。”大愣和二愣也大声附和。
“胆小鬼,脑袋掉下来碗大一个疤,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杀人只当风吹帽,怕、怕个屁!”人精一拍胸脯,豪气顿生,接着又说:“别他妈叽叽歪歪了,让人看见反而不好。何师爷、大愣和二愣,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还叫尿给憋死吗?”
“老爷,你想到办法了?”何师爷有些紧张。
“还没有。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人精四顾无人,压低了声音,接着又说:“等会儿吃了晚饭,我就不回仙谷村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咱们关上门,开一个短会,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
“老爷,就我们四个?”大愣指了指自己,又看看人精、何师爷和二愣一眼。
“我的个小祖宗,你声音轻一点。不就我们四个?你还想找谁?你还想敲锣打鼓?”师爷警惕地看了四周一眼,十分紧张地捂住了大愣的嘴。
“大愣,你别妄自菲薄,相信老爷,也相信你自己,知道吗?办法一定比困难多?”人精友好地在大愣的肩上拍了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先忙去吧!记住哟,晚上九点,在老爷我的书房,不见不散。”
推官崔福生是第二天九点多钟到的。
到的时候,人精在大愣和二愣的陪同下,正躺在府衙隔壁的元珍药铺里看病,打点滴。人精得的是病毒性感冒,浑身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疹,超级传染,且咳嗽不止。府衙上下、里外都弄得神秘兮兮的,高度紧张。
没办法,人精只得头上缠上绷带,脸上捂着个口罩,连走个路也需两个人搀扶,一左一右,嘴里哼哼唧唧,眉头紧攒,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大愣和二愣都生怕被传染,一个个都苦哈哈的,甚至不怕对着人精讲话,仿佛连空气也可以传染。
可郡里来了同僚,而且还是同榜进士,人精更不敢怠慢,也没有半点可以怠慢的理由。他强撑着,强打起精神,在书房里接见了这位同年,热情,客气,周到,一样都不缺。至少看上去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让推官挣足了面子。
其实,按照傲来国的官制,郡里的推官就相当于现在州人民法院的院长,掌管刑名、狱讼,赞计典,类似于古代的判官,是郡守佐贰官,官阶为从四品,比人精冒名的那个正四品知府朱平,还低了一个档次。
可人精并不这么看,同年之间是没有高低上下的。他处处礼让着崔福生,言必称您,您先请、您先用、您先来之类的客套话,更是经常挂在嘴上,让推官十分受用。崔福生自然也意气风发,红光满面,就像弥勒佛再生。
久而久之,崔推官也疑窦丛生。在他记忆里,同年朱平可不是这个样子。朱平心胸狭隘,死要面子,尤其喜欢争强好胜,为了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可以死蛤蟆争出尿来。他怎么一下子变了呢?变得礼貌,大方,不拘小节,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崔推官有些匪夷所思。
带着疑惑,崔推官又回忆他们之间的一些往事,一些场景,一些典故,一些出现的人物,讲过的一些话,可人精说得一丝不差。站在他面前的,分明就是踌躇满志,刚愎自用的朱平。活灵活现,如假包换。
其实,说到底,崔推官和朱平仅仅是个同年,见过有限的几次面,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什么友谊和交情。他对朱平的大致印象,和现实中的朱平,有些对不上号。不知是自己的记忆偏颇,还是朱平脱胎换骨,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崔推官不得而知,也不想陷在里面。
虽说病得不轻,可人精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给崔推官和几个随员,在平德府订了最贵、最豪华的酒店,摆了最丰盛、最美味的宴席,用公款大大的奢侈、腐败了一回。人精想:幸亏自己在福来郡只有这一个同年,再多几个,自己就要破产了。不吓个半死,也会被老百姓赶下台。
在人精看来,崔推官其名是来给自己送匾,表彰自己智擒鬼盗、火烧牛王洞的功绩,其实却有趁机打秋风、敲诈勒索的成份。听话听音,人精是个聪明人,脑子不笨,他早就听出了崔推官的弦外之音。换一句话说,或者也叫暗示。
崔推官吹开杯子里的浮沫,浅浅地喝了口茶,笑着说:“朱知府,你是我的同年,全郡十二个府三个州,我为什么要给你请功送匾?不仅是你智擒鬼盗、火烧牛王洞深得民心,功勋卓著,还因为你是我崔福生的同年,你我交情不浅。”
“那是,那是!我们这些在下面主政的,仰赖推官大人的美言和提携。我朱平以茶代酒,敬推官大人一杯,千言万语,尽在香茗之中。”人精哈哈大笑,不停地打着马虎眼,不失一个官僚政客的世故和客套,圆滑、练达兼而有之,暗藏机锋。
“朱同年,还是下面好哇!至少不会缚手缚脚,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有一句古话叫什么来着:宁当鸡头,莫作凤尾。鸡头再丑再陋,也是自己;凤尾就是再美再漂亮,也是别人的尾巴,身不由己啊!”崔推官像个怨妇,牢骚满腹。
“要不,我们换换。你来平德府当知府,我去福来郡做推官。”人精的话既有几分调侃,又有一点挖苦。笑了笑,他接着又说:“老崔呀,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知府风是风光,出门前呼后拥,可几十万人都指着你穿衣吃饭哪!稍一不慎,就是失察。你呀!你是只惦记着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知府也不好当哪!也是驴糞蛋蛋外面光。”
“不好当?但至少比做一个推官强。我不说别的,一府的钱粮你可以做主吧!钱财过手,总有些油水可以捞一捞,总有些好处可以沾一沾。”崔福生期期艾艾,一脸羡慕,接着又说:“朱知府,你不要说你是包公、海瑞,两袖清风,我不听!”
“老崔,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人精听出了崔推官的弦外之意,揣摩出了他的暗示。他四顾无人,客气地拱了拱手,压低了声音说:“老崔,你放心,我早就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程仪,四个随员,一人一份,些须薄礼,不成敬意,还请笑纳。”
“朱知府,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老朋友的。有酒大家喝,有财大家发,同喜,同喜!”崔推官喜笑颜开,十分友好地擂了人精一拳,神神秘秘地说:“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吧!一定会在郡守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升官发财,指日可待!”
“老崔,那我是不是给郡守大人也备一份薄礼?”人精憨憨地搔了搔后脑勺,还是有些犹豫。
“那敢情好,礼多人不怪。聪明!”崔推官十分激动地一拍大腿,大拇指高高地竖了竖,翘了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