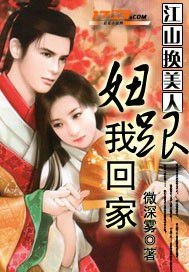蓦地,溶洞深处传来了杂杂沓沓的脚步声,杂之以鬼盗们说话的声音,在洞窟里嗡嗡回响。看样子,鬼盗们都喝大了,喝高了,脚步有些踉跄,声音呑吞吐吐,一个个都红头涨脸,面目狰狞。黑暗中,一双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就像传说中的鬼火,熠熠闪烁,让人恐怖而又惊悚。
鬼盗们一来,掳来的女人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见到了在天空中盘旋的老鹰,一个个都惊恐万状,莫名地紧张了起来。出于人求生的本能,她们不由自主地团成了一堆,挤在一起,潮水似地推来攘去。束手无策,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看得出,妮可也十分紧张,紧紧地握住了人精的手。鬼盗猪脸的本事,她早已见识过了,对于人精,她却没有十足的把握。隐隐的,她既有几分期待,又有一些担忧。人精打得过鬼盗猪脸吗?会不会因此而丢了性命?
女人们就像一锅烧开了的水,骚动、沸腾了起来,一个个都大呼小叫,嚎啕痛哭。哭得人精血脉愤张,激情澎湃,真想就这么冲出去,跟鬼盗们拚一个你死我活。
可人精不能冲动,只能忍,冲动是魔鬼。可有的时候,忍耐比冲动还要可怕。人精的拳头几乎攥出了水,牙齿咬得格格响,嘴唇也快要咬出血来。他知道:自己一旦冲动,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
接二连三,有女人被强行拖走,鬼盗们一个个酒气薰天,眉开眼笑。当然,为了某个长得好看一点的女人,鬼盗们也有打斗,也有争吵,也有相互挖苦和嘲讽。但他们很快就妥协了下来,各退了一步。在某些方面,鬼比人还要团结。
有些人,甚至有些伟人,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去决斗,不惜打得头破血流。放弃是一种美德。可在某些人眼里,放弃的反而成了懦夫。打得头破血流的,反倒可以名垂青史。可不管怎么说,为了妮可,人精就可以不顾一切,可以去和任何人决斗。
骚动之中,人精死死地拽住了妮可的手,十指紧紧相扣,不容任何人把她从自己手里夺走。妮可也真是幸运,被几个鬼盗们轮流抢夺了一阵子,可她有人精死死攥着,磁力太重,不得不放手。鬼盗们都喝高了,醉得一塌糊塗,也没有过多的讲究。在人堆里胡乱拉了一个人,欢天喜地地走了。
猪脸陈旦终于出现了,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他的内心里有些纠结。喝醉了酒丢了工卡和腰牌,猪脸陈旦就回不了地狱,一直在人间里东游西荡。后来,他还听说,四大鬼使中又出现了新的猪脸陈旦,自己的未婚妻桑吉也跟他好上了。
除了痛苦和绝望,猪脸陈旦还积压了满腔的怒火。他恨人间,他恨这个卑鄙的世界,他恨冒名顶替他的这个猪脸陈旦。这么多日子了,他求爹爹告奶奶,不惜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可仍然回不了阴间。他有冤无处诉,有国不能报,有家不能回。他活得实在是太憋屈了,要多冤就有多冤。
一直以来,猪脸陈旦除了爱点酒,没有其他别的嗜好,和未婚妻桑吉也处得好好的,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可一杯酒毁了他的未来,给了那个冒名者以可乘之机。他恨那个假猪脸陈旦,冒名顶替之仇,夺妻之恨,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这样一来,猪脸陈旦就开始了疯狂地报复,既然回不了地狱,他就把他的怒火都撒在人间,逮着谁就该谁倒霉。他纠集了一帮孤魂野鬼,占住了这座溶洞,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专门跟官府作对,把美好的人间弄成了地狱。
除了喝酒,猪脸陈旦最大的兴趣就是施虐。他喜欢女人哭哭啼啼、破口大骂的样子。连自己最心爱的未婚妻都被别人霸占了,在他猪脸陈旦的词典里,再也没有爱或怜惜。有的只有痛苦和无休无止的愤怒。
站在女人堆旁,猪脸陈旦踌躇了一阵子。在这么多的女人当中,他一眼就看中了妮可,前些天他从鱼市码头掳来的那一个。女孩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要霸占她,要施暴,就像那个冒名顶替的猪脸陈旦,霸占他的未婚妻桑吉、征服他的未婚妻桑吉一样。
接连几天,猪脸陈旦在那个女孩身上说尽了好话,下足了功夫,甚至不惜撕破了脸,开始霸王硬上弓。女孩子不仅不从,还乱撕乱咬,把他的脸也挠破了,至今还隐隐作痛。鼻子呢?也被她咬坏了,鼻翼上面还留下了两颗很深很深的牙印,可以说是伤痕累累。
可不管怎么样,猪脸陈旦还是喜欢这种刚烈、叛逆的女孩子。他多么希望他的未婚妻桑吉,能像这个誓死不从的女孩子一样,用指甲,用牙齿,用一腔热血,殊死抵抗那个冒名者的大胆入侵,捍卫她脚下那块最神圣的土地。
猪脸陈旦深深地吸了口气,终于理清了自己纷乱的思绪。他绕着乱成一堆的女人,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管结果如何,他还是想去试一试。至于能不能得逞?可不可以征服?他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可是,你不去努力,你不去尝试,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结果如何?你的人生就永远只会留下遗憾。
想也没想,猪脸陈旦就把手伸进了女人堆里,伸向了那条他十分熟悉的花裙子,拽了又拽。
可就在这个当口,一只手猛地往上一翻,快逾闪电,紧紧地扣住猪脸陈旦的脉搏。猪脸陈旦挣了挣,可那只手骨节粗大,坚逾铁石,像一道刚刚焊上去的铁箍。猪脸陈旦的身体立刻麻了半边,动弹不得。
见人精得手,妮可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伸手,就摘去了猪脸陈旦腰上的刀和刀鞘。没了刀和刀鞘,猪脸陈旦的手再快,也成了没了牙齿的老虎,不足为患。妮可咬牙切齿,顺手一个大耳光子抽了过去,啪地一声脆响,猪脸陈旦的脸立刻肿了半边,像一只发了酵的黑麦馒头。
遭过害的女人们一拥而上,撕的撕,咬的咬,尽往猪脸陈旦最敏感、最痛疼的地方招呼,把他身上的衣服撕得赤条条的,身体抓得百孔千疮,血流不止。猪脸陈旦双手被控,动弹不了,哭爹喊娘地喊叫了起来。
听到猪脸陈旦又喊又叫,妮可急中生智,扯下了一只臭袜子塞进他的嘴里。人精也用一只手,抽出腰里的一小根裤带,打了个活扣,套在猪脸陈旦的脖子上,把他反背在肩膀上。猪脸陈旦越是挣扎,脖子上的活扣就锁得越紧。
诸位,需要交代一下的就是:长期以来,人精一直用龙须藤上的龙须作裤带。不是一根,而是一束。龙须不仅坚韧,牢靠,还非常耐用,结实,水火不侵,别说是捆一个小鬼,就是捆一条张牙舞爪的恶龙,也够用了,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人精和妮可虽然小心了又小心,谨慎了又谨慎,可还是让声音惊动了在溶洞深处,寻欢作乐的鬼盗们。他们放下女人,挺刀执杖地赶了出来,团团地把人精困在核心。刀光闪闪,作势欲扑。妮可亮出了手上的匕首,一颗心也紧张到了极点。
满不在乎的是人精,他一只手勒紧龙须,就像《搜神记》里背鬼卖的定伯一样,把猪脸陈旦反背在肩膀上。他脚尖一点,踩飞了放在地上的杄担,一根七十二斤的镔铁棍,就轻轻松松地握在手里了。他脚踏罡步,边抡边舞,手上的镔铁棍呼呼作响,幻出了一个漩涡,激起了一个大大的光圈。
让妮可大跌眼镜的是,人精居然武功精进,今非昔比。妮可的紧张显然有些多余。人精一根七十二斤的镔铁棍,指东打西,横扫千军,虎虎生威。镔铁棍搅起了一阵阵的旋风,天昏地暗,飞砂走石,吹得妮可几乎睁不开眼睛。
别看鬼盗们平时叫嚣得很厉害,咋咋呼呼,祸害起老百姓来也毫不含糊。可一遇到人精这么硬扎的对手,就认了栽。棍风所及,一个个倒在地上,死的死,伤的伤,跪在地上哼哼唧唧,哭爹喊娘,早就失去了鬼盗的威风。
人精也累得够呛,脸因缺氧而涨得通红。他拄着镔铁棍,粗粗地喘定了一口气,大声吩咐:“快,妮可,点火,放烟!”妮可踌躇再三,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好不容易才擦着了火镰。妮可确实有些紧张,手也不听使唤。
火焰低滞了一阵子,终于熊熊地燃烧了起来,浓烟滚滚。埋伏在竹林里的衙役、捕快们,见知府老爷得了手,一个个摇旗呐喊,奋勇争先地抢进洞来,捆的捆,抓的抓,把鬼盗们一个个押出洞来。一时里,塘坝镇人山人海,哭声震天。
全民公审、处决鬼盗的那一天,是一个大晴天。天高云淡,万里无云,空气里飘满了茉莉花的香味。广平府衙门前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乌泱乌泱地挤满了来看斩鬼的老百姓。老百姓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一个个扬眉吐气,喜笑颜开。
人精乌纱朝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案前,接受着万民的瞻仰和膜拜。从古至今,知府老爷下马管民,上马拿贼,勤政爱民。可真正敢与恶鬼为敌,深入匪窟,勇擒鬼盗的,人精还算是第一个。可以说,开了人定胜鬼的先河。
捕快、衙役们也心诚悦服。他们一个个都对自己的老爷,佩服得五体投地。能够孤身一人,独闯溶洞,就足以说明知府老爷的责任和担当。他们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早早地赶到衙门前,为知府老爷大壮声威,维护治安。
赤金县塘坝镇的百姓们都来了。他们一个个敲锣打鼓,牵牛赶羊,箪食壶浆,来给知府老爷挂红,献礼,送锦旗和彩幛。多好,多质朴的百姓哪!来了一批又一批,送走一拨又一拨。还有的,正走在来的路上。
猪狗失而复得,牛羊失而复得,妻女失而复得,百姓们要求的并不多,有什么比血脉亲情、比亲人团聚还重要?铲除了鬼盗,恢复了太平,百姓们又可以安居乐业了。他们不停地唱啊,跳啊,额手相庆,载歌载舞,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幸福的泪水怎么擦也擦不完。
杂在一群普通的百姓们中间,妮可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为自己的男人而骄傲,而自豪。作为一个被鬼盗掳去了的年轻女孩,她也真正见证自己爱人的机智,神勇,感受了鬼盗们的猖狂和可恶。她就像一个深受其害的老百姓一样,把鬼盗们看一遍,唾一遍,骂一遍,恨得咬牙切齿。
大快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鬼盗们被一个个押上台来,五花大绑,面如土色,一长溜地跪在地上,高高矮矮十八个。人精从签筒里抽出一支竹签,恨恨地扔在地上,厉声大喊:“午时三刻已到,郐子手,鬼头刀伺候,斩!”
鬼头刀依次挥起,寒光一闪,一颗颗鬼头乒乒乓乓地掉在地上,滚出老远,被早在候在一旁的一群饿狗叼起,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得无影无踪。尸体失去了头颅,脖腔里冒出了丝丝缕缕的白气,一时里阴风怒号,大雾弥天。
怪的是:猪脸陈旦的尸体失去了头颅,却又缓缓地长出一颗新的,须发皆张,圆睁怒目,高声大喊:“老子冤枉,老子不服,老子是阎罗国堂堂的鬼使陈旦,你他妈的一个小小的知府,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处决老子?哼,我呸!”
人精火了,亲自操刀上阵,兜头往猪脸陈旦身上泼了一盆狗血,缓缓地举起了鬼头刀,厉声大骂:“我不管你什么鬼使不鬼使?你祸害人间,作恶多端,就该杀,就该死!你有什么冤屈,就找阎罗王去申诉吧!”
说罢,人精手上的鬼头刀猛地一挥,刀光一闪。一颗头颅噗地一声掉在地上,骨骨碌碌地滚出了几丈远,溅起了一蓬白血。人精伸出手,遥遥一招,一只禿鹫盘旋着飞了下来,呱地一声,叼起了地上的头颅,扑腾起翅膀越飞越远,一眨眼就消失在缥缥渺渺的苍穹。
大家再看时,猪脸陈旦的四肢抽搐了一阵子,应声倒在地上,眼看着是活不成了,一缕阴魂归了地府,找阎罗王讨说法去了。
一时里,百姓们都凝神屏息,惊得目瞪口呆。沉默了一阵子,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衙门前欢声雷动,喝采声如潮,百姓们又载歌载舞,开水一样地沸腾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