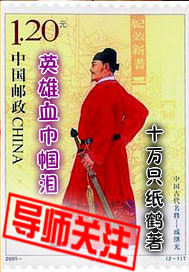妮可在赶赴首都益稼郡的途中,被空空门知著堂的堂主巢天虎救走,连夜用舱门抬至一个老郎中的家中。帮中弟子不敢怠慢,锦衣男子亲奉汤药,把妮可像菩萨一样供了起来,一日三餐,非鱼即肉,时令果蔬、糕点茶果堆了满满一屋。
老郎中望闻问切,连开了几剂中药,早、中、晚连服三次。妮可原来没什么大病,只是偶感风寒。不几日,身体就调养好了,手脚利索,红脸也红润起来。偶尔,还可以帮老郎中的儿媳妇烹茶煮饭,做做家务,打发那一段寂寞无聊的日子。
老郎中的儿媳妇,也不知道妮可什么身份,看到这么多男人,这么多扒手,围着她兜兜转转,谀词令色,知道妮可一定不简单,至少不是个普通人。可她又不敢问,更不好意思问,只好一直憋在心里,对妮可也爱搭不理。
不仅老郎中的儿媳妇猜不透,老郎中也猜不透妮可的身份。见妮可的病已完全好转,无甚大碍,可还有这么多的男人,这么多的扒手,在店子里出出进进,吆五喝六,左邻右舍也难免说闲话,嚼舌头,指指点点。老郎中为避免嫌疑,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自然希望妮可早一点离开。
有一天,吃完晚饭,妮可收拾完碗筷,帮老郎中的儿媳妇纳鞋底。小媳妇四顾无人,压低了声音说:“你知道吗?丐帮的老帮主白眉中了剧毒,两只眼睛全瞎了,前些天晚上用轿子把我公公抬了去,看了一晚上的病。作孽啊!”
“为什么要弄瞎白眉的眼睛?”妮可有些漫不经心。
“夺权争位呗!”小媳妇只顾低头纳鞋。
“哪是什么人呢?”妮可拽起了鞋底上的索子。
“帮中的两个护法。一个叫郑通,一个叫宋见。”
“呸,利欲薰心。”妮可呲了一嘴。
“可不是吗?都跳了崖,都死得很惨。活该!”小媳妇咬断索子,也恨恨地骂了一句。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不知谁当上了这个帮主?”妮可若有所思,长长地叹了口气。
“听说是一个叫人精的俊俏后生,江湖人称偷天神猿,使一根七十二斤的镔铁棍,武功十分了得,人也长得威风凛凛。”小媳妇絮絮叨叨,看了妮可一眼,接着又说:“听说这个人精还是个读书人,单身贵族,不是帮中弟子,还当上了丐帮的老大。要不,我找人给你介绍、介绍。”
听到人精两个字,妮可本能地全身一震,泪流满面,颊上飞起了两朵红晕。可妮可暗暗地擦了把泪,不动声色地说:“大姐,你真灵通?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又不是丐帮里的人?这些都是帮中的不传之秘?”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知道吗?我的亲舅舅就是丐帮松鹤堂的堂主张楚凤。现在丐帮的九袋弟子、护法长老。他的一条命,就是现任帮主人精,从仁川郡的大牢里救出来的,神得很嘞!江湖上都传疯了!”小媳妇在头发上润了润针,有些洋洋得意。
“真有这等事,真是太巧了。”妮可口不应心,一个疏忽,针尖刺穿了手指,沁出了一点点的鲜血。她把指头含在嘴里,吮了吮,吮出一口鲜血吐在地上,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大姐,你丐帮长,丐帮短的。丐帮究竟在哪里?远不远?”
小媳妇四顾无人,竖起一根指头,轻嘘了一声,压低了声音说:“不远,就在湾子村,翻过后面那架大山就是。我听说,湾子村就是丐帮的密营,里面有私塾,有武馆,有年轻人演武练兵的山洞,神秘得很嘞!”
“哪里的湾子村?”妮可故意装傻。
“仁川郡苍南县的湾子村呗?你没去过?座落在大山里面,山青水秀。美得很嘞!”小媳妇十分向往。
妮可想了想,有一点她始终也想不明白。按理说,人精潜入仁川郡的大牢里去救人。那么,总捕头乃至郡守都是他的对手,敌人。为什么七月十五那天晚上?他会和总捕头、郡守同时出现在游船上,把酒言欢。看样子,交情还不错。小偷和捕头好上了?鸡和黄鼠狼居然成了朋友?真是怪哉!
一连几天,妮可早出晚归,把龟山港的水陆地形,都摸得清清楚楚,烂熟于胸。到苍南县走哪条路?从哪里分岔?到湾子村又有多少路程?要经过哪些地方?妮可都做足了功课,在一个小本子上标注得清清楚楚。甚至在哪里打尖?在哪里歇宿?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哪怕再苦再累,只要能找到人精,找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也值。
写到这里,读者朋友或许会有些疑惑,出云号在仁川河里航行了四、五天,怎么还没跑出仁川郡的地界。列位不知,仁川河是一条之字形的河流,蛇绕蛇弯,回还曲折。通常从本郡出发,在别的郡航行了几天,又会进入本郡的水域,只是河道不同而已,船夫、水手们早已见惯不惊。
其实,根据妮可的了解和观察,去苍南县,到湾子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要绕着大青山,七弯八拐,大约一千多公里的路程,需四、五天的时间。另一条路要翻越大青山,从一座匪寨中穿过,只需一天的时间,不过路近,风险也大。
本来,巢堂主和锦衣男子,要给妮可搞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以示对老帮主的尊重,也被妮可婉言拒绝了。自己一个落难之人,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既与自己的身份不符,又是浪费资源。人活到这个份上,仪式已是多余,她只想谨慎一点,低调一点,争取早一天出发。
妮可思来想去,决定还是闯匪寨,抄近路,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约三、四天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连沧海都可以变桑田,世界又该发生了多少变化?她只想早日见到人精,她一刻也等不及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大青山海拔并不高,却十分陡峭,满山苍翠随着山势起伏,蜿蜒,又曲曲折折地伸向远方,给莽莽苍苍的地平线,作了最美、最美的镶嵌。仁川河萦回如带,像一根明晃晃的索子,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远远望去,龟山港就像索子旁的一粒弹丸,笼罩在灰朴朴的阳光里。
妮可在脸上涂了一层锅底灰,穿一套补丁摞补丁的烂衣服,头发也弄得乱七八糟。她挽着一只破竹篮,装了二十几颗鸡蛋,背着一只蓝士布的包袱,混迹在一群贫民、乞丐堆里,战战兢兢地向岭上爬去。风很大,吹得她脖子上的花布围巾呼呼作响,人也有些踉跄。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家里死了人,出了大事、急事,大家是不会闯匪寨,抄近路的。路虽说近了一点,毕竟要担风险,要提心吊胆,看人脸色,仰人鼻息。人们宁愿多走几步路,多耗一点时间,多费一些金钱,也求个心安理得。
贫民中,老人居多,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衫,端的是破碗,拄的是拐棍,个个都是一步三喘,老态龙钟。年轻人是不敢混在里面的,一是怕土匪掳去入伙,坏了性命;二是怕被土匪拉伕,抓去脱坯种地,修房做屋。
尤其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更不敢了。妮可听人说,大青山寨子里的土匪大头目,叫彭俊青,是个采花大盗,嗜好淫人妻女,江湖绰号蝴蝶草上飞。被他糟蹋过的黄花闺女,没有一千,也有数百。二头目入伙前是个木匠,叫邬顺,江湖人称开山斧鲁班,会一些拳脚功夫,人还比较仗义。
早些年,朝庭也出过缉捕文书,悬赏黄金万两,捉拿过这个采花大盗。无奈此贼武艺高强,轻功了得,再加上他诡计多端,多次从官兵和捕头手里逃脱,继续在大青山一带占山为王,鱼肉百姓,辣手摧花。
妮可为了抄近路,赶时间,扮成了一个老太婆,混在一群贫民、乞丐堆里。其实,她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和绝对的把握。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步步为营。
一路上,妮可装聋扮哑,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一切都咿咿哑哑,用手势表达。她时刻牢记着言多必失这个词。万一被人从声音里识破了她的年龄,了解了她的身份,她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甚至,大难临头。
当然,妮可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她在她的烂靴套里,藏了一把匕首。万一被土匪识破,她首先是自卫,先拉一个垫背的再说。然后,再是自尽。面对着人精居住的湾子村,用一把锋利的匕首结束自己,了断残生,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越往上爬,空气就变得越稀薄,山路也陡了不少。大爷、大妈们都爬得气喘嘘嘘。妮可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毕竟是刚生过一场大病,体质有些虚弱。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人精在湾子村的消息激励着她,她早就已经躺下。
妮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手搭凉蓬,远远望去,离土匪的寨子越来越近了,悬在竹竿上的义字旗迎风飘扬。夕阳挂在陡峭的山崖上,红光四射,远远近近的林子里,浮满了淡紫色的轻烟。一群黑褐色的归鸦,翅膀掠着阳光,零零星星,隐隐约约,暮雨似地在天空中飞翔。
不知怎的,越往前走,越靠近土匪的寨子,妮可的心就越紧张。不用凝神屏息,她也可以听得见自己剧烈的心跳。看得出,大爷、大妈们也比她好不了多少,一个个都如履薄冰,汗出如浆。要想全身通过土匪的老巢,毕竟不是儿戏。
土匪的寨子前,排着一列由乞丐和贫民组成的队伍,两边的山坡上,站满了荷枪执戟的喽罗。喽罗们一个个都耀武扬威,面无表情,凶神恶煞般的样子。
寨门前有人值守,验明一个,放行一人,交五十文铜钱。买路钱不贵,盘查却格外仔细。有点像法官审犯人,捕头查户口。妮可看见,有人被当众扣了下来,被一群喽罗推推搡搡地押了进去,一声爹一声娘地叫起屈来,凶多吉少。
妮可挽了挽胳膊上的竹篮,躬着腰,装着老态龙钟的样子,一步一捱地往前走去。她的心有些高度紧张,冷汗源源不绝地冒了出来,她用手擦了擦,弄得手心手背都是汗。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双手不停地搓来搓去,搓出了两颗黑黑的汗泥,心也悬到嗓子眼。
终于轮到妮可了,值守的喽罗一抡枪杆,枪上的红缨闪了闪。妮可点头哈腰,赶紧走了过去,满脸堆笑,递上早已准备好的五十文铜钱。铜钱己用红头绳穿好,长长的一串。
不知是紧张,还是疏忽。妮可在递铜钱的时候,两手前伸,裸露出白皙的腕部。虽然手指手掌化了妆,弄得乌漆麻黑,可手腕却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她的手指手掌黑得像炭,手腕却白得像藕,时间不长,却足以暴露她女孩子的身份。
完了,完了!妮可的脸一下子烧得通红,本能地抱紧了双臂,身体也筛糠似地抖个不停。值守的头目腰插双斧,虬髯虎目,可能是寨子里的二头目邬顺。邬顺上上下下,十分凌厉地看了妮可一眼,愣了愣,挥了挥手,照例放行。
谢天谢地!妮可心中暗喜,三步并做两步跨了出去。篮子里的鸡蛋哐地一响,一下子碎了几个。蛋清和蛋白顺着篾片的缝隙流下来,淋淋漓漓掉在烂靴子上,把鞋帮子都弄得湿漉漉的,惨不忍睹,像鬼画的桃符。